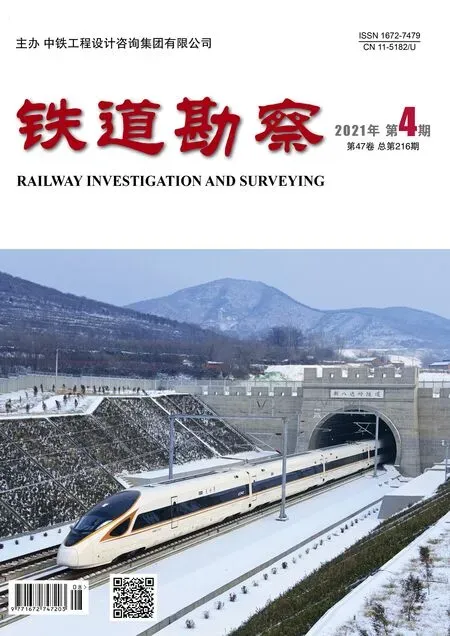川西某引水隧洞工程多尺度地質環境特征分析
戚紹禮 魏星燦 鐘志彬 劉宇罡 鄧榮貴
(1.中國水利水電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成都 610213; 2.中國電建集團成都勘測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 610072; 3.成都理工大學環境與土木工程學院,成都 610059; 4.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成都 610031)
我國西部山區地形地質環境條件極其惡劣,新構造運動活躍,尤其是四川盆地西部,歷經印支、燕山和喜馬拉雅多期次構造運[1],地形起伏劇烈,受多條活動斷裂構造影響,區域構造應力較高,地震頻發,巖體結構類型眾多,在該區開展隧道類工程建設面臨的巖體工程問題復雜[2-6]。而工程區工程地質及水文地質環境特征的正確分析是后期制定有效工程對策的基礎,徐健楠等[7]通過對普陀山長大深埋鐵路隧道區域水文資料及現場勘查,針對隧道不同段落的巖層與結構特征,采用不同的方法組合進行涌水量預測,并提出施工措施建議。同時,川西地區又是我國水電資源的重要基地,是國家“西電東送”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8]。
川西地區水電站多為引水式發電,長大引水隧洞群成為水電站建設的關鍵,如錦屏二級水電站布置7條穿越錦屏山的隧洞群總長達120km,建設過程中易遭遇高地應力、巖爆、高壓大流量突涌水等復雜工程難題[9],宋威等對其工程地質環境特征進行了分析[10]。因此,開展此類引水隧洞工程前期工程地質環境特征分析,是保證工程安全、高效建設的關鍵[10-11]。
以涼山州某在建水電站引水隧洞工程為背景,從不同尺度視角詳細分析隧址區域地質環境特征,進而綜合分析區域構造過程,揭示造成工程區復雜地質環境的內在因素,以期為川西地區大量隧道類工程建設提供經驗借鑒和技術參考。
1 工程概況
某水電站位于四川省木里縣境內,為低閘引水式發電站,主要由首部樞紐工程、引水及輸水工程、發電工程和施工臨時性工程組成。其中,首部樞紐工程包括擋水閘壩、引水閘首、泄洪孔門及排沙孔門等構筑物與結構物;引水及輸水工程包括輸水隧洞、調壓井、分水閘室及壓力鋼管隧洞和相應的結構物;發電工程包括地面式發電廠房、尾調閘門、尾水渠道及防護構筑物和相應的構筑物與結構物。水庫正常蓄水位為2215m,相應庫容48.4萬m3,調節庫容12萬m3,引水隧洞長約11.15km,利用落差129m,裝機容量172MW。
2 各尺度區域宏觀地質環境特征與分析
主要從不同尺度視角,遵循從宏觀到局部的原則,分析各尺度地質環境特征及其造成隧址區復雜地質環境現象的相關性,從而為針對性地開展圍巖支護設計和施工方案提供依據。尺度區域是指從全球板塊構造的視角出發,就隧址區周圍數千公里大尺度區域范圍、數百公里中尺度區域范圍和數十公里小尺度區域范圍的地質構造特征,系統分析工程區不同尺度層次下的地質構造動力來源,地質構造特征及其締造的隧址區復雜的工程地質巖體力學環境和工程巖體結構類型。
2.1 大尺度區域宏觀地質環境特征與分析
數千公里尺度下,區域的宏觀地質環境包括板塊構造及其形成機理、過程,決定引水隧洞工程區地質環境的總體格局。該引水隧洞位于四川西部橫斷山脈核心部位,平均海拔高程4000m以上的第一階梯青藏高原至平均海拔高程約1500m的第二階梯四川盆地過渡帶(實際上,四川盆地核心地區的平均海拔高程不足500m,屬于第三階梯的高程)。為從更廣域的角度來觀察水電站所在的地質環境,根據地殼板塊構造學原理,隧洞位于歐亞板塊東南凸起端根部西側,南亞印度地殼板塊、青藏高原與準揚子地臺之間的三角地帶。
水電站位于青藏高原凸起體的東南邊緣地帶。根據地殼板塊學說的觀點[12-13],青藏高原不屬于一個獨立的地殼板塊,而是在南亞印度板塊的強力推擠作用,太平洋板塊主動頂推作用(通過揚子地臺傳遞作用)和歐亞板塊的“剛性”約束作用下的受擠“上凸變形體”。青藏高原形成之初,主要產生褶曲變形,印度大陸板塊持續向歐亞大陸板塊之下俯沖和楔入,強烈的持續擠壓構造作用,使該地區地層新生代以來產生多期強烈構造變形,以早期深層次的韌性剪切構造和晚期的脆性斷裂構造為特征。隧址區位于歐亞大陸板塊的前緣,印度大陸于新生代初期主動與歐亞大陸擠壓碰撞,初期擠壓作用的整體方向為N5°~10°E,隨著地層變形破裂和接觸邊界的變化,后期擠壓的總體方向變為N25°~35°E。印度大陸與歐亞大陸從初期碰撞至今的持續作用,宏觀上經過了以下過程(見圖1)。

圖1 南北向兩大板塊及青藏高原地塊間相互關系示意
(1)歐亞大陸板塊南部邊緣附近產生褶曲變形,形成近EW向的背斜褶曲,同時產生北東及南西向的剪切節理,沿背斜核部發育彎張性裂隙和近南北向壓張性裂隙。
(2)隨著印度大陸持續強烈的擠壓,因受歐亞大陸主體和揚子板塊主體的強力約束,特別是鄰近呈NEE向展布的塔里木盆地和呈NNE向展布的四川盆地基底的強力約束,上述歐亞大陸南緣近東西向的褶曲強烈隆起,并開始朝近南倒轉,超覆于印度大陸北部邊緣之上。
(3)印度大陸繼續強烈擠壓歐亞大陸,向歐亞大陸南緣背斜倒轉翼部產生俯沖和形成韌性剪切(剪切塑性大變形)構造斷裂(縫合帶或結合帶)。此時除東端(緊鄰橫斷山區)和西端(緊鄰克什米爾高原)外,歐亞大陸南緣與印度大陸北緣之間,在空間上的上、下關系基本形成。
(4)印度大陸持續北移,進一步向歐亞大陸之下俯沖和楔入,歐亞大陸南緣開始抬升,拉開了青藏高原形成與演化之旅。
(5)印度大陸長時間持續向歐亞大陸之下俯沖和楔入,歐亞大陸的抬升從其南緣逐漸向北部發展,至塔里木盆地東南緣、柴達木盆地西南緣和四川盆地西北邊緣。受三大盆地地殼基底特別是塔里木盆地地殼基底的強力阻擋,歐亞大陸南緣開始的抬升,印度大陸逐漸向東北方向發展,同時垂直向也不斷抬升,青藏高原的雛形逐漸顯現。
(6)青藏高原繼續抬升的同時,因受其強烈的“楔-頂-擠-壓”作用,以及在東、東北和西北側三大盆地的強力約束性阻擋作用下,其地殼物質向四周產生“超覆”或“滿溢”,形成地形階梯,其中就包括大規模的龍門山超覆型孕震構造帶。
雅魯藏布大峽谷區域的擠壓構造更為強烈和復雜。該區域構造分為兩個部分,其一是橫斷山區域,受印度大陸北緣“拱橋”推擠在東西向派生的強烈擠壓作用,形成了眾多近SN偏NW向的構造山脊,在近SW向不到70km的距離內,出現了“三江并流”的奇觀;其二是雅魯藏布大峽谷區域,受印度大陸北緣“拱橋”推擠的強烈擠壓,產生北東向的強烈俯沖與楔入作用,使該區域出現了局部隆升式褶皺和彎張斷裂與剪切斷裂疊合現象,使該區域的構造極為復雜。這就是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南部青藏高原南緣碰撞東構造結區域的地質環境,引水隧洞位于該東構造結的東側約505km,可見隧洞所處宏觀區域構造地質環境極其復雜。
2.2 中尺度區域宏觀地質環境特征與分析
工程所處的數百公里的中尺度區域大地構造部位上,工程區位于“川滇菱形”斷塊的北西部,為次級斷塊“稻城斷塊”的東緣,該次級斷塊由理塘—德巫斷裂帶、麗江斷裂帶和金沙江斷裂帶所圍限。東鄰理塘—德巫斷裂帶的南延段(德巫—麥地龍)、八窩龍斷裂帶SW端,南鄰木里弧形斷裂帶西翼。區內受次級斷塊“稻城斷塊”邊界斷裂帶的影響和控制,地質構造較復雜,斷層、褶皺發育。
該引水隧洞位于橫斷山脈核心的最窄部位(見圖2),起點在大渡河谷石棉縣約850m高程,沿243.63°方向至緬甸河谷高程約780m的剖面通過水電站工程區,橫斷山的寬度約460km(剖面長度),承受了前述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喜馬拉雅山楔入構造的東構造結的“犁入式”擠壓作用,以及揚子地臺西緣四川盆地地塊的強烈頂推約束作用,歷次強烈的構造作用,形成了現今近南北向的構造形跡,河流的急劇下切,塑造了當今近南北向的河流和山脈,在直線距離約64km范圍內出現了所謂“三江并流”奇觀,這點與大尺度宏觀構造環境對應。

圖2 隧址區中尺度橫斷山中部構造概要平面
根據橫斷山區平面構造特征勾畫的剖面構造示意(見圖3),該引水隧洞工程位于四川省的西部,木里藏族自治縣境內,地處青藏高原橫斷山脈的東南部,地勢由北向南傾斜,為高山深切割區,河流強烈侵蝕下切,屬高山峽谷地貌。山頂高程一般3500~4500m,相對高差達1500~2500m。表明引水隧洞在中尺度區域范圍內構造環境的復雜性。

圖3 隧址區橫斷山中部構造概要剖面(A-A’)
2.3 小尺度區域地質環境特征與分析
從該引水隧洞工程所處的數十公里小尺度區域來看,木里河由北向南流經工程區,河谷多呈不對稱“V”形,莫嘎拉吉溝—曼念吉岡溝約6km河段,右岸坡度較緩,左岸陡峭。可見有三級階地,其中Ⅰ、Ⅱ級階地較為發育,為堆積階地,Ⅲ級階地分布零星,為基座階地,僅局部地段殘留其部分,各階地撥河高度分別為2~5m、15~20m、60~80m。
工程區地層以區域性淺變質地槽型沉積建造為主,巖漿活動微弱。地層區屬巴顏喀拉-秦嶺地層區中甸分區的木里小區,區內古生界、中生界除缺失侏羅系和白堊系外,其余各系均有沉積,但各系發育程度及其分布不一,以奧陶系、三疊系較發育,分布較廣。工程區地層巖性主要為奧陶系下統的變質石英砂巖、板巖夾千板巖,志留系板巖、千板巖夾硅質板巖、灰巖,三疊系的上統曲嘎寺組中—厚層夾薄層狀灰巖,少量石炭系灰巖夾板巖[14]。地層間多以斷層和角度不整合接觸,少數為假整合接觸。區內第四系地層分布較廣泛,主要分布于右岸緩坡地帶及河床、溝床,成因類型較復雜,厚度和結構變化較大。工程區主要發育一系列NW向、NE向斷層,組成“棋盤格式”,NW向發育為主,NE向次之(見圖4)。

圖4 工程小尺度區域構造
場區位于先鋒斷層(F1,NE向)、赤土斷層(F9,NW向)和機落斷層(F2,NW向)所組成的“小斷塊”內,發育有北西向的茸德斷層(F3)、基洼斷層(F4)、撒洼斷層(F5)、索根斷層(F6)及北東向的曼念吉岡斷層(F7)、布讓滿耶斷層(F8)等,其中F4、F5、 F6、 F7橫(斜)切引水隧洞,典型斷層出露見圖5(a)。
工程區內山高坡陡,物理地質作用較為強烈,受地形地貌,地層巖性,地質構造控制,不同規模褶皺、揉皺現象明顯,造成巖體結構破碎、產狀雜亂,見圖5(b),為風化、卸荷與崩塌災害發育。右岸以坡、殘積堆積和滑坡堆積為主,左岸以崩、坡積堆積為主,兩岸沖溝未見泥石流堆積。

圖5 隧址區典型構造發育特征
水文地質方面,區內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層孔隙水、基巖裂隙水和基巖局部褶皺構造虛脫空腔河岸陡峭山體強卸荷松弛“貫通性裂隙水”3種地下水類型。松散層孔隙水主要集中分布于河谷地帶,含水層為第四系堆積物,主要賦存于砂礫卵石層中,地下水的補給以大氣降雨和地表水為主,運移和排泄條件主要受地形地貌及河谷第四系的沉積特征控制,具有較大的差異性,一般為潛水。
受巖性及構造控制,基巖裂隙水埋藏及補給、運移、排泄條件復雜,因節理卸荷作用松弛張開,以及軟弱巖體受擠壓揉皺強烈變形作用,含水裂隙(帶)之間水力聯系有的較差,而有的較好。“貫通性裂隙水”主要賦存于小型揉皺型褶皺構造形成的虛脫空腔和沿陡傾構造節理或小斷層卸荷松弛或張開的裂縫中,該類地下水補給受地形降雨匯集、巖性帶狀分布和空腔發育程度的影響。
小尺度區域工程地質及水文地質環境特征分析表明,場區受多條斷層切割控制,可見大量小規模揉皺現象,地質構造和地層巖性復雜多變,隧洞開挖過程中將不可避免穿越斷層破碎帶、卸荷松弛帶等,易引發局部塌方、涌水等工程災害。
3 工程場址區區域構造過程初步分析
由圖4可知,工程區的褶皺構造和斷裂構造跡線主要是NW向和NE向,其中NW向褶皺較NE向褶皺發育,斷裂構造兩個方向發育程度相當。
根據場址區斷層及節理走向及傾角統計,場址區發育4組優勢斷裂,分別為:①N55°W向、②N25°W向、③N5°E向和④N55°E向,傾角大于60°的陡傾斷裂占70.2%。場址區中等堅硬和堅硬巖體的綜合內摩擦角(φ)應為20°~50°,平均值為33°。根據巖石力學中的摩爾-庫倫強度理論,夾角在(90°-φ)的范圍內可以配套構成同一期形成的共軛“X”剪節理。這樣夾角在40°~70°的2組節理組合可能構成同一期形成的剪節理,其中①組與③組,③組與④組,①組與④組之間的夾角在40°~70°之間,此可以構成3套“X”剪節理,對應的最大主應力方向分別為N25°W、N25°E和EW。
綜合上述場址區不同尺度區域地質環境特征分析,以及微小褶皺和節理調查資料的整理及分析,對場址區構造過程進行如下推測性分析。
(1)最初場址區受到來自東西向(約N25°E)的擠壓構造作用,地層初步形成了NW向展布的一系列褶皺形態和③組與第④組剪節理或斷層。該期的構造活動應該是在印支期的構造活動形成。根據我國大地構造分析[15],可以推測該方向的最大構造主應力為印支期構造所致,并且最大主應力方向與場址區內主要褶皺構造呈大角度關系。
(2)場區受到北西向(約N25°W)的構造作用,形成了①組和③組優勢節理,該期構造與燕山期構造方向(NWW)有一定關系,推測為燕山期產物。
4 結論
以川西地區典型水電工程引水隧洞為依托,從場區數千公里至數十公里的不同尺度視角,綜合分析了隧址區工程地質及水文地質環境特征,獲得以下結論。
(1)宏觀大尺度上,受印度—歐亞大陸版塊“楔-頂-擠-壓”強烈作用,工程恰好位于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南部青藏高原南緣碰撞東構造結區域東側,造成隧洞所處宏觀區域構造地質環境極其復雜。
(2)中尺度上,引水隧洞位于“川滇菱形”斷塊的北西部,為次級斷塊“稻城斷塊”的東緣、橫斷山脈核心的最窄部位,承受前述印度洋板塊與歐亞板塊楔入構造的東構造結的“犁入式”擠壓作用,以及揚子地臺西緣四川盆地地塊的強烈頂推約束作用,歷次強烈的構造作用,造成引水隧洞工程在中尺度范圍內復雜的構造環境。
(3)小尺度上,木里河由北向南流經工程區,河谷多呈不對稱“V”形,發育一系列NW向、NE向斷層,組成“棋盤格式”,不同規模褶皺、揉皺現象明顯,造成巖體結構破碎、產狀雜亂,隧洞開挖過程中易出現局部塌方、涌水等工程災害。
在工程建設初期,受工程規模、勘察手段等限制,很難對超過10km長度的隧洞工程地質環境作出準確判斷。因此,針對川西地區復雜的地質環境條件,應從不同尺度對工程區構造環境進行分析,揭示區域地質環境形成條件及機理,再結合工程勘察及地面調查結果,綜合分析并對隧址區可能的地質環境特征進行合理的推測,將有利于更加準確地判斷開挖圍巖條件,指導實際工程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