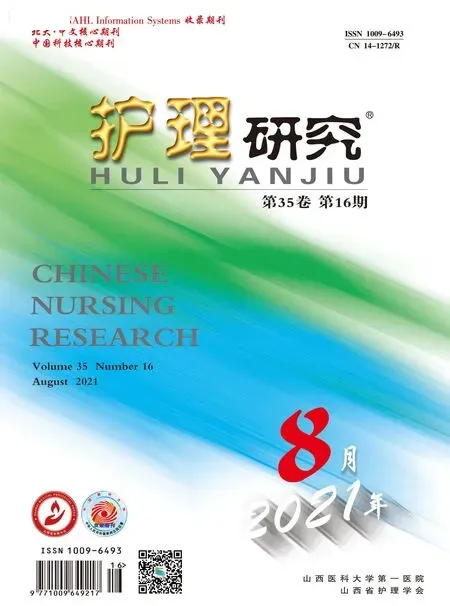認知行為療法結合普拉提運動在腰椎間盤突出癥術后病人護理中的應用
左青青,曹亞琴,何守玉,閔繼康
1.湖州師范學院,浙江 313000;2.湖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腰椎間盤突出癥(lumbar disc herniation,LDH)是指由于腰椎間盤退行性改變、超重負荷、外界力量等多種因素長期作用下導致纖維環部分或全部破裂,髓核組織從破裂處向外膨出或突出,壓迫神經根發生的急性損傷性炎癥反應。病人主要臨床表現為腰痛、下肢放射性疼痛、肢體麻木、間歇性跛行[1]。劇烈疼痛使病人產生非理性恐懼心理、逃避運動,最終導致失用綜合征[2]。研究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恐動癥”[3]。相關研究發現,LDH 病人術后恐動癥的發生率為45%~60%[4],高于術前,可能與疼痛時間較長、開放性手術、術后遺留疼痛等因素有關[4]。國內關于LDH 術后恐動癥相關研究較少。已有研究顯示,通過術前相關知識宣教、術后多學科協作治療、個性化鎮痛治療等,可以降低恐動癥的發生率[5‐7]。本研究旨在觀察認知行為療法結合普拉提運動對LDH 術病人恐動癥及康復依從性的影響,現報告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方便抽樣方法,選取2019年6月—2020 年7 月湖州市某三級醫院骨科住院病人作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經臨床醫師確診為LDH 病人,需擇期行腰椎手術;②年齡18~80 歲;③恐動癥量表(Tampa Scale for Kinesiophobia,TSK)評分>37 分;④有正常的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具有簡單數字、文字書寫能力;⑤自愿加入本研究,并取得知情同意權。本研究經過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排除標準:①病人存在其他脊柱疾病;②除LDH 外已有其他慢性疾病的病人,且慢性疾病存在長期疼痛;③腰椎曾有手術史;④參與其他研究;⑤腰椎手術期間需進行其他手術;⑥合并嚴重器質性疾病。脫落標準:①術后病人由于病情變化轉入他科;②研究期間不愿繼續參與,自行退出者。樣本量計算:參考文獻[8],使用梅斯醫學APP 樣本量計算,最終確定所需樣本量為68 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34 例。兩組病人一般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續表)
1.2 研究方法
1.2.1 對照組 采用常規護理、認知行為療法。①常規護理:術后注意觀察病人生命體征及病情變化,及時詢問病人雙下肢感覺變化情況。術后24 h 內病人需保持平臥位,禁止翻身;24 h后協助病人軸線翻身,2 h 1次,預防壓瘡;注意切口敷料情況,發現異常情況及時報告醫生;注意觀察是否有腦脊液漏發生。病人病情穩定后,囑其行踝關節背伸、跖屈,防止下肢靜脈血栓。術后4~6 h 以流質飲食為主,避免食用牛奶等產氣食物,以高蛋白、高纖維素食物為主,具體飲食需考慮病人是否存在其他疾病。記錄每日病人大便情況,必要時使用開塞露等通便措施。術后48~72 h 拔除引流管后,病人無明顯不適情況,指導病人正確佩戴腰圍,行站立、行走訓練、直腿抬高鍛煉、腰背肌肉鍛煉、正確坐姿訓練,具體運動根據病人疼痛情況合理安排。②出院指導:囑病人術后3 個月佩戴腰圍,3 個月后可以解除腰圍,6 個月后開始慢慢彎腰。彎腰時拿物品重量不能超過5 kg,左右手同時使用。術后3 個月、半年、1 年預約復查。③認知行為療法:術后加強與病人交流,建立相互信任的護患關系。了解病人對LDH 術后康復鍛煉的認知水平,耐心講解術后康復鍛煉的重要性。術后2 d 至出院前1 d 講解LDH 術后康復方法、目的、注意事項,及時糾正病人錯誤認知。建立康復計劃,指導病人每日進行肌肉放松、深呼吸訓練,每次20~30 min。出院日至術后第6 周,評估病人康復計劃實際完成情況,對康復結果給予肯定,進一步強化病人對康復鍛煉的認知。建立微信群,定期發送相關康復鍛煉視頻、日常注意事項,及時通知病人進行復查。
1.2.2 觀察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進行普拉提運動。運動形式以平躺抬膝、伸頸卷骨盆、仰臥脊椎旋轉、背部伸展、伸展脊椎、貓伸展式等運動形式為主。①平躺抬膝:病人平躺在瑜伽墊上,雙膝彎曲,雙腿分開與肩同寬,雙手平放于身體兩側。將右腿慢慢伸直、抬離地面。右膝緩緩向胸口處靠近。動作保持穩定,膝蓋不能轉動。保持5 s 后還原,更換另一側腿。②伸頸卷骨盆:取去枕仰臥位,骨盆位于正中,雙膝彎曲,腳掌平放,雙腳與肩同寬,雙手平放在兩側,下頜內收。呼氣收腹,緩慢卷曲骨盆。下部、中部、上部依次離開地面。吸氣時緩慢抬高身體的上部,保持肩、骨盆和膝關節位于一條水平線。呼氣時身體、椎骨依次降低,回到原始位置。③仰臥脊椎旋轉:取去枕仰臥位,雙手伸直盡量與肩部保持在同一高度,手背朝下。身體伸直,兩腿合攏、膝蓋彎曲90°,緩慢抬高雙下肢,與地面成90°。吸氣時讓大腿沿著地平面慢慢下滑。當對側肩部即將離開地面時,肩部下沉,放松頸部。呼氣收腹,集中核心力量將腿部還原至中間位置。重復上述動作進行對側運動。④背部伸展:病人坐立于地面,雙腿伸直,雙腳微微分開,雙臂平舉至肩部高度,雙眼平視前方。呼氣收腹,雙臂前伸,收下頜與鎖骨觸碰,椎骨緩慢向前彎曲。保持向前卷的姿態,過程中避免背部挺直,到脊椎形成一條“C”形曲線。吸氣,保持姿勢。呼氣還原,從下至上緩慢伸展。⑤伸展脊椎:與背部伸展取同一坐位,雙臂向前伸直。吸氣時收緊盆底肌,呼氣收下頜至鎖骨。慢慢向前彎曲脊椎,收縮腹部肌肉,雙臂保持前伸,腰部前彎,腹部緩慢上抬。吸氣保持姿勢不動。呼氣由下往上伸展脊椎,還原至最初狀態。⑥貓式伸展:俯撐在瑜伽墊上,雙手雙膝著地,身體正中位,雙手與肩同寬,呼氣收腹,收下頜至鎖骨,慢慢拱起脊柱。下沉至最低點,保持身體穩定。吸氣還原。呼氣仰頭,眼睛看向天花板,全身放松,吸氣還原。從病人拔除引流管開始鍛煉至術后第6 周,每次30 min,每日2 次。
1.3 評價指標
1.3.1 TSK 該量表是判定恐動癥的主要工具之一,共17 個條目,每個條目均采用Likert 4 級評分法,1 分為強烈不同意,4 分為強烈同意,條目4、條目8、條目12、條目16 反向計分,總分17~68 分,>37 分提示病人存在恐動癥,分數越高表示恐動癥越嚴重[9]。
1.3.2 ODI 評價病人術后腰椎功能恢復情況,從疼痛程度、生活能力、日常活動、睡眠、社會活動5 個方面評分,總分為50 分[10]。
1.3.3 骨科病人功能鍛煉依從性量表 該量表從與身體方面相關鍛煉依從性、與心理方面相關鍛煉依從性、與主動學習相關鍛煉依從性3 個維度進行評定,共15 個 條 目。采 用5 級 評 分 法,1 分 為 根 本 做 不 到,5 分為完全做得到,分值越高說明功能鍛煉依從性越高[11]。1.4 資料收集方法 資料收集前對調查員進行統一的培訓,資料收集時采用統一的指導語指導病人填寫,填寫完畢后當場收回,并進行雙人核對,以保證問卷、量表的有效性。本次調查問卷有效回收率為100%。比較兩組病人術后1 周、4 周、6 周TSK、ODI 評分及骨科病人功能鍛煉依從性水平。
1.5 統計學方法 所有資料檢查、核對后雙人錄入計算機,采用SPSS 23.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描述,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定性資料進行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病人術后TSK 評分比較(見表2)
表2 兩組病人術后TSK 評分比較(±s) 單位:分

表2 兩組病人術后TSK 評分比較(±s) 單位:分
注:F 組間=12.788,P<0.001;F 時間=743.330,P<0.001;F 時間×組間=12.672,P<0.001。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 值P術后6 周22.00±2.65 25.18±3.07?4.566<0.001例數34 34術后1 周34.56±2.34 37.47±2.34?5.134<0.001術后4 周27.35±3.47 30.97±3.47?4.298<0.001
2.2 兩組病人術后ODI 評分比較(見表3)
表3 兩組病人術后ODI 評分比較(±s) 單位:分

表3 兩組病人術后ODI 評分比較(±s) 單位:分
注:F 組間=44.539,P<0.001;F 時間=316.440,P<0.001;F 時間×組間=18.871,P<0.001。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 值P術后6 周23.29±3.15 30.18±3.24?8.880<0.001例數34 34術后1 周33.21±3.42 37.88±3.02?5.976<0.001術后4 周27.97±3.71 33.82±3.26?6.915<0.001
2.3 兩組病人功能鍛煉依從性量表評分比較(見表4)
表4 兩組病人功能鍛煉依從性評分比較(±s) 單位:分

表4 兩組病人功能鍛煉依從性評分比較(±s) 單位:分
注:F 組間=95.106,P<0.001;F 時間=1 065.388,P<0.001;F 時間×組間=15.476,P<0.001。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 值P術后6 周57.21±2.91 49.06±4.55 8.801<0.001例數34 34術后1 周39.00±2.23 33.94±2.30 9.219<0.001術后4 周46.56±2.63 41.12±3.04 7.888<0.001
3 討論
隨著人們生活節奏不斷加快,LDH 發病人群呈現年輕化趨勢,持續腰痛嚴重影響病人的生活質量。腰痛時間超過3 個月稱為慢性下腰痛(chronic low back pain,CLBP)[12]。中國約20%CLBP 是由LDH 所致[13]。手術治療已成為LDH 后期主要治療方式之一。手術治療雖然可以有效改善臨床癥狀,但術后病人臥床休息時間超過2 周,肌蛋白合成將會減少50%[14]。如何實現病人術后早期康復鍛煉一直是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研究發現,LDH 術后病人康復效果不僅與脊柱退行性病變程度有關,還受心理、行為及信念等因素影響,其中恐動癥已經被認為是影響LDH 術后病人疼痛持續時間、功能減退、喪失功能的獨立危險因素之一[15‐16]。相關數據顯示,LDH 術后45%~60%的病人會出現恐動癥。患有CLBP 并伴有較高程度恐動癥的病人,其身體殘疾的風險增加41%[14]。故對LDH 術后病人進行干預可降低運動恐懼水平、提高康復依從性,促進術后早期康復。
1983 年,Lethem 等[17]首次提出了恐懼回避模型。主要由受傷經歷、疼痛刺激、與疼痛相關的高度恐懼(疼痛災難化&對運動極度恐懼)、低功能的自我效能感、逃避/回避行為、棄用綜合征等因素構成。疼痛災難性解釋會導致病人對與疼痛相關的情境和運動產生心理恐懼。此外,通過增加對身體感覺的注意力和難以從這種刺激中解脫而產生高度警惕。這種回避行為會導致身體功能障礙和殘疾增加,從而導致抑郁,增加痛苦感知水平。1990 年Kori 等[18]將這種回避行為定義為“恐動癥”。蔡立柏等[5]對108 例全膝關節置換術后恐動癥病人進行認知行為干預,結果顯示,認知行為療法可以明顯降低全膝關節置換術后病人的運動恐懼程度,同時促進膝關節功能的快速恢復。認知行為療法是以問題為指導的短時間治療模式,包括心理教育、放松訓練、認知療法、問題解決和行為活化等方面組成。其主要優點在于幫助病人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觀點并加以改正,消除不良情緒、調整不正確的行為。認知行為療法已成為目前使用較為廣泛的心理干預方法之一,在治療抑郁、焦慮、強迫癥等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19‐21]。Archer 等[22]對86 例腰椎手術后存在恐動癥病人進行持續6 周的認知行為治療,結果顯示干預組病人疼痛、TSK 及ODI 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脊柱功能恢復率、病人生活質量有所提高。但相關研究顯示,術前對病人進行恐動癥相關知識宣教及減輕恐動癥的相關訓練,LDH 病人術后恐動癥發生率仍高達45%左右[23]。
普拉提主要訓練核心肌群,提高病人肌肉力量及協調性。訓練過程中結合普拉提式呼吸功能鍛煉,能夠有效減輕脊柱及背部疼痛[24]。隨著醫療及康復技術的進步,普拉提運動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25‐28]。羅明輝[29]對64 例慢性非特異性下腰痛病人進行普拉提運動結果顯示,普拉提運動在減輕下腰疼痛感、改善腰椎功能等方面取得較為滿意的效果。楊敏麗等[30]對60 例非急性期LDH 病人進行了8 周的普拉提運動,結果發現,實驗組腰椎關節活動度明顯優于對照組,疼痛程度有所降低。Cruz‐Díaz 等[31]對64 例慢性非特異性下腰痛病人進行12 周普拉提練習,結果顯示,普拉提運動干預對慢性非特異性下腰痛病人殘疾、疼痛和恐動癥管理有效。慢性非特異性下腰痛病人發生恐動癥的危險因素主要是疼痛年限、經濟負擔。LDH 病人術后恐動癥與慢性非特異性腰痛存在一定的差異。LDH 術后病人發生恐動癥主要由于術前急性期嚴重的疼痛感、手術創傷、疾病預后等影響因素造成,發病率較慢性期更為嚴重[32]。單純的普拉提運動并未改變病人原始的錯誤認知,只是單純從運動角度減少疼痛刺激,從而進一步降低運動恐懼水平[33]。故本研究根據LDH 術后病人實際情況,讓病人在提高認知并糾正自己錯誤觀點的情況下結合普拉提運動,根據逐漸暴露的原則,調整練習,逐步使病人適應新的運動模式,從而達到降低術后恐動癥的水平,促進腰椎功能的早期恢復。
本研究結果顯示,普拉提運動與認知行為療法相對于單純認知行為療法能夠有效改善LDH 術病人恐動癥水平,提高康復依從性。由于本研究只選取1 所醫院病人作為研究對象,可能會產生選擇偏倚。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需要將LDH 術后病人康復運動方式進一步規范化、多樣化,納入更多樣本量、多個單元合作、更為深入的研究,為臨床工作者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