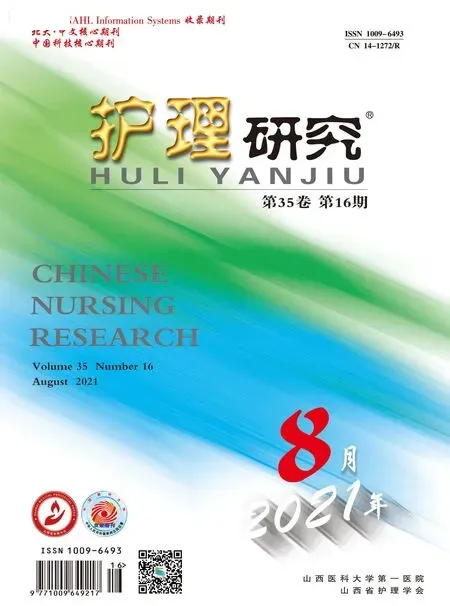移動醫療在預立醫療照護計劃中的應用研究進展
楊妍婷,王永麗,索婷婷,孫佳忱,沈永青
河北中醫學院護理學院,河北 050000
2000 年,中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截至2018 年底,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已達到11.9%[1],慢性病人口數量呈增長趨勢[2]。2015 年經濟學人智庫調查顯示,我國公民的死亡質量位居全世界第71 位,死亡質量較差[3]。 預 立 醫 療 照 護 計 劃(advance care planning,ACP)是指人們憑借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經驗,在意識清楚并具有決策能力時,表達個人臨終照護意愿的過程,力求使醫療服務與人們價值觀和偏好保持一致[1],適用于生命的任何階段,當人的健康狀況惡化或年齡增加時,ACP 會變得更有針對性[1]。有研究表明,ACP 往往能帶來更好的生命結局[4‐5]。我國ACP 尚處于概念推廣階段,面臨文化差異、制度缺乏等阻礙[6]。移動醫療作為一種新興的干預方式,賦予了人們資源自主權,可通過相關設備緩解人們情感上的不適[7],并能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覆蓋更多人群,提高人們接受度。本研究通過梳理國內外文獻,總結目前移動醫療在ACP 中的相關理論模型、應用現狀、可用性評價現狀,以期為后續移動醫療在我國ACP 中的推廣提供借鑒和參考。
1 移動醫療在ACP 中的應用現狀
世界衛生組織將移動醫療定義為通過各種移動和智能移動設備,如手機、掌上電腦,為醫療衛生實踐提供支持,已在慢性病管理方面得到廣泛應用[8]。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大量研究表明,移動醫療ACP 具有較多潛在益處,能在臨床會診中提高溝通質量,改善生活質量,減少不必要的住院治療,增加姑息治療的使用等[9‐10],還能緩解人們面對死亡話題產生的不良情緒,及時更新人們對ACP 的掌握情況并推送相應信息[11]。目前,國外主要以病人電子信息記錄系統、網頁、APP的形式呈現,我國ACP 目前處于起步階段,多以微信、公眾號的形式進行推廣,信息傳遞缺乏連續性、規范化、系統化。
2 相關模型
2.1 多屬性效用理論模型 該模型是一種量化決策分析方法,能夠將眾多評價指標納入分析模型中,分別對指標賦予適當權重并相加算出方案總得分,各個方案的總體效果最終以量化結果顯示,具有適用廣泛、評價完整、操作簡便、結果明確等優點。Making Your Wishes 是基于多屬性效用理論模型,由醫學、護理、生物倫理學、老年醫學、決策分析、法律、圖形藝術、教學設計和教育等領域的專家共同參與的在線網頁程序,程序以音頻、視頻、互動等形式為病人量身定制了ACP 教育、價值澄清練習,將個人的目標和偏好轉化為可由醫療團隊實施的特定醫療計劃[12]。
2.2 跨理論模型 該模型將個體的行為轉變過程劃分為5 個不同的階段,包括無意向期、意向期、準備期、行動期和維持期[13]。在特定階段應該采用適當的改變策略,使行為改變的效能最大化。該理論將行為變化看作一段跨越時間的過程,但不一定以線性方式進行。Prepare For Your Care 基于跨理論模型隨時間演變和病人觀念、行為的變化提供不同的內容,使用視頻故事、行為建模等5 個步驟,打造適合病人不同階段的教育措施。
2.3 生命終止概念模型 生命終止決策可以被概念化為醫護人員、病人及其家人之間的重復反饋的動態過程,最終決定采用或放棄維持生命的治療。該模型重點關注參與決策的參與者(病人、醫護人員和病人代理人),并定義了生命終止決策過程的3 個截然不同的組成部分(信息交流、治療方案的討論、治療方案的決定)。My ICU Guide 是基于生命終止概念模型,通過19 次質性訪談為重癥監護室(ICU)病人家屬開發的關于嚴重疾病患病期間對治療偏好的思考、相關信息、參與共同決策、考慮并代表病人的價值觀和偏好、自我管理和情緒健康技能、提出問題以及與醫療團隊進行溝通及其他關鍵技能的在線平臺,幫助病人及其家屬參與ACP 的過程,做出更加符合病人意愿的決定[14]。
3 移動醫療在ICP 中的應用形式及內容
3.1 病人電子健康記錄(electronic health record,EHR)在ACP 中的應用 EHR 是以病人ID 為標識按時間縱向地集成全部醫療相關數據的官方健康檔案記錄,每個人與EHR 綁定生成個人健康記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s,PHR)。在不同的組織和單位之間實現數據信息共享和交流[15]。EHR 在醫療機構廣泛應用。Bose‐Brill 等[16]基 于PHR 創 造 了ACP 通 信 框 架,進 行了小型隨機試驗,其特點為個性化、結構化、高效,可以自動與病人的病歷同步,并且為病人與醫護人員提供了交流平臺。結果顯示:與常規護理相比,PHR 與ACP 相結合,能提高門診ACP 記錄率和質量。此框架適用于ACP 的初始階段,在ACP 后期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研究。安全醫療電子消息傳遞(patient electronic messaging,PEM)是EHR 的一項功能。2009 年美國《經濟和臨床健康信息技術法案》的頒布,促進了PEM和EHR 的使 用[17]。Tieu 等[11]通過PEM 將適當ACP 資源鏈接的非侵入性激勵電子消息定時發送給注冊的參與者,進行了隨機對照干預,干預組接受個性化的PEM,發出初始消息8 周后,向尚未上傳ACP 計劃的個人發出提醒消息,12 周時收集最終數據結果。預先醫療指令(advance directives,ADs)是ACP 計劃的一種形式,使用個性化PEM 干預組的參與者,AD 完成率比對照組顯著提高。EHR 與ACP 相結合的其他研究[18‐21]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ACP 的記錄率和AD 的簽署率。
3.2 網頁程序在ACP 中應用 基于網頁的ACP 程序,可以在任何首選時間在網頁上對其進行訪問,它們更易吸引受眾,相對容易實現,并且具有可伸縮性[22]。Making Your Wishes Known(MYWK)是遵循循證指南由多學科團隊開發的,針對可能導致決定性喪失工作能力的常見醫療狀況以及在生死攸關的情況下采用的治療方法,提供有針對性的教育在線網頁平臺,不同人 群 應 用 的 研 究[12,23‐25]已 證 明MYWK 易 于 使 用[25],能改善病人臨終醫療決定[26],準確代表病人的意愿[27],對臨床醫生也有幫助[28]。有研究表明,潛在的病人代理人不適合此種在線干預,會使病人代理人自我效能下降。Prepare For Your Care 采用視頻故事、行為建模等5 步流程,部分研究將PREPARE 與簡易閱讀的預先指令聯合在一起進行干預[29]。定量研究[30‐34]和定性研究[35]均顯示,此項目促進了ACP 對話的開展和ACP行為的參與。搜集到的其他有關ACP 信息的10 個網頁程序[14,36‐41]包括了對ACP 的準備或ACP 適當時機的關注,對治療和護理偏好的選擇以及可能任命的醫療代理人,幾乎對參與者沒有產生負擔,易于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參與者對ACP 知識、技能的掌握,提高了ACP 的記錄率和AD 的簽署率。基于網頁的ACP 程序雖不能取代與病人及醫護人員進行ACP 的討論,但可以為病人準備這些討論提供支持,并在自己的時間和環境中考慮其價值觀、信念和護理偏好等問題。
3.3 移動健康應用程序在ACP 中的應用 移動應用程序(application,APP)是支持病人進行ACP 過程的另一種方法,可緩解談論死亡帶來的不適感[7]和對跨醫療機構決策的可及性的擔憂[42],提高ACP 的完成率[43]。涉 及ACP 的 相 關APP 見 表1[44],點 擊APP 后 直接鏈接網站的未被納入表中。共納入6 款APP,語言均為英語,大部分可實現免費下載,均可提供個性化文件,但只有兩項會跟蹤報告用戶進度,不利于監測用戶狀態,提供適時信息。只有兩款APP 提供了關于ACP知識方面的內容,目前針對ACP 的APP 更適用于準備完成階段的人員,而不是希望了解ACP 流程的人員。目前,國內主要通過微信群、公眾號、QQ 群、論壇等方式加強生命末期病人、照顧者及醫護人員之間的交流,網頁、APP 面向的人群也多為臨終、腫瘤等人群[45]。而國外相關APP 由于網絡的限制,語言和文化的差異,大部分程序很難在國內應用推廣。我國可借鑒國外的經驗、理論模型、結構,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ACP 移動程序。

表1 移動健康應用程序(APP)一覽表[44]
4 移動醫療在ACP 中應用的可用性評價
可用性是指特定用戶在特定環境下使用某個產品,高效、滿意地達到特定目標的程度。Sarah 等基于具有共同電子病歷的區域衛生保健系統,招募了46 例病人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探求病人使用基于EHR 系統的ACP 相關工具的原因以及程序該如何適合ACP的認知[46]。通過詮釋學編輯方法對數據進行歸納分析,大多數病人表示通過該工具傳達他們的偏好變得更加方便和高效。Van Der Smissen 等[22]認為基于網頁的交互式ACP 程序是可行的。研究以Arksey 和O'Malley 方法框架進行范圍界定[47]納入27 項研究進行可行性和有效性評價,研究顯示,程序易于使用,對基于網頁版的ACP 項目感到滿意。Mcdarby 等[44]對現有的預先護理計劃移動APP 內容的功能,設計質量和局限性進行評價,結果顯示,針對ACP 的APP 在iOS平臺和Android 平臺已經有一些可以免費下載,但當前可用的ACP 移動應用程序具有不完整的ACP 內容,并且缺乏增強用戶友好型的基本設計功能。
5 移動醫療在ACP 中應用存在的不足及建議
我國對移動醫療技術在ACP 中應用的相關研究較少,雖然移動醫療在ACP 國外研究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①病人電子病歷系統與ACP 相結合的高質量研究較少,可能存在偏倚,可增加隨機對照試驗,擴大樣本量,進一步考證。②APP涉及ACP 質量參差不齊,存在外觀和內容不匹配的現象[44],一些ACP 移動應用程序只是帶有相關ACP 網站鏈接的平臺,不能離線使用的功能缺陷帶來不便,未來的ACP 應用程序開發中必須優先考慮可用性以及提供更大的可訪問性。③國外移動醫療ACP 均為英語,具有文化局限性,未來可先對我國醫護人員進行移動醫療網頁評價、需求的調查,為未來我國移動醫療ACP 的開發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做好前期準備。我國ACP 的發展處于起步階段,移動醫療ACP 的開發包括的基本信息有生死教育、行為改變過程、ACP 流程,一些重要醫療選擇的區別,如何與家屬、醫護人員表達自己真正的意愿、如何選擇代理人,以及醫護人員ACP 的教育培訓內容。④老年人群對移動設備的使用素養水平不高,可為其設計簡單可操作個性化版本。
6 移動醫療在ACP 中應用的發展前景
移動醫療作為21 世紀醫療領域最具潛力的創新技術之一[48‐49],能彌補ACP 干預措施的資金、時間和空間缺陷[50‐51],以經濟、高效的方式接觸更廣泛的用戶群體,使用戶能夠在自己方便的情況下以電子方式編輯和表達個人意愿,減緩面對死亡話題的不舒適感[7]。研究顯示,病人和照顧者從網絡獲取醫療信息的人數越來越多[52‐53]。“4G”“5G”網絡的覆蓋、智能手機、掌上電腦等硬件裝備的普及、醫共體的發展,推動了移動醫療與ACP 的結合,為解決我國ACP 推廣面臨的文化阻礙、資源不足等問題,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目前,我國ACP 無正式的立法保障,未廣泛普及,在這種情況下,應充分利用民間團體力量,組建多學科團隊,以移動醫療為載體,加強知識宣傳,提高公眾接受度。相信在多方力量的支持和努力下,本土化的ACP 移動醫療體系會逐漸建立,最終推動國內安寧醫療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