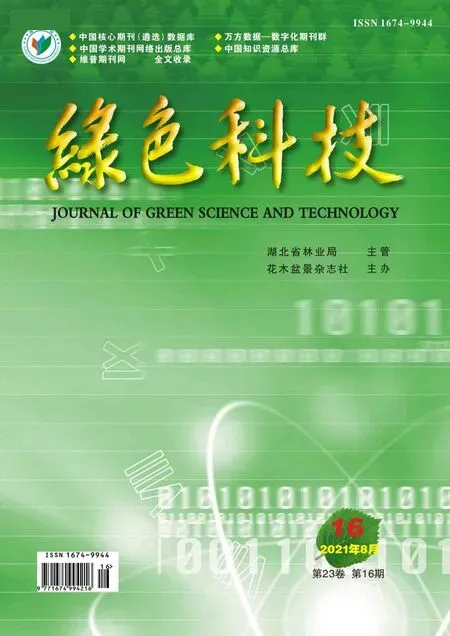可燃冰的開發(fā)現(xiàn)狀與前景
凌君誼,楊再明,高海波
(1.上海海事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上海 200120;2.武漢理工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3)
1 引言
可燃冰是在深海的高壓低溫條件下,大量水分子經(jīng)由氫鍵范德華力緊密結(jié)合建立的固態(tài)類冰狀結(jié)晶物質(zhì)[1],最典型的水合物構(gòu)型有SⅠ、SⅡ和SH三種。每單元可燃冰包括8個甲烷分子和46個水分子即CH4∶H2O=1∶5.75,具有極強的儲氣能力,其完全燃燒后主要變?yōu)槎趸己退?/p>
在礦物能源枯竭的背景下,全球化石能源的儲量較低,雖然新能源的發(fā)展緩解了這一狀況,但其能源供應(yīng)比重較低,如圖1所示核能與水力發(fā)電所提供能源不足全球能源供應(yīng)的10%,主要能源供應(yīng)還是來自于煤炭,但在2005年版BP世界能源統(tǒng)計年鑒中提到石油儲量為1619億t;天然氣儲量為179.5兆m3,僅能滿足全球41年的石油需求與66年的天然氣需求,所以開發(fā)另一能源迫在眉睫。全球可燃冰潛在儲量超過1.5×1016m3,并且放出的熱量達到煤氣的數(shù)倍(4.2×108J/kg),其分布如圖2所示,由此可知可燃冰具有高效、儲量大等特性,并且據(jù)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若可燃冰能進行商業(yè)開采,僅儲量的15%就能滿足世界200年的能量消耗[2~6]。

圖1 不同燃料所能源提供所占比重(21世紀)

圖2 世界可燃冰分布
因此可燃冰的開采與應(yīng)用直接影響世界各國歷史進程的演變,未來可燃冰的商業(yè)開發(fā)前景也非常廣闊,可燃冰的研究尤其是開采和實際生活中的運用對未來新能源領(lǐng)域具有重要的戰(zhàn)略意義[7]。
2 國內(nèi)外可燃冰發(fā)展政策
目前全球有3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進行可燃冰研究,尤其是美加日俄等國的開發(fā)研究處在領(lǐng)先地位,但目前的主流開采方法存在成本高以及效率低等問題,而且部分國家自身資源豐富,所以可燃冰的總體研究較緩慢,但并不影響其重要地位。
2.1 美國可燃冰研究計劃及進展
美國于1934年最早發(fā)現(xiàn)可燃冰,并于1981年制定了可燃冰“十年”研究計劃,投入800多萬美元進行研究,2005年將可燃冰開發(fā)的總撥款增加到1.55億美元。
在2014年年底設(shè)立 “深水甲烷可燃冰描述與科學評價”大型項目,其分為目標站位優(yōu)選、研究計劃制訂、野外研究3個階段實施。并于2015年9月底完成了墨西哥灣某些可燃冰研究站位的初步評價。目前,由于頁巖氣發(fā)展迅速并且其開采技術(shù)成熟,美國放緩了可燃冰的開采計劃[7]。
2.2 日本可燃冰研究計劃及進展
日本對可燃冰的關(guān)注超乎其他國家,因為其國土狹小、能源短缺并且核電受挫,急需其他能源使日本擺脫能源進口依賴。
自20世紀80 年代末日本鉆探獲得可燃冰樣品,發(fā)現(xiàn)其周邊海域可燃冰儲量可滿足自身100多年的天然氣需求。則在2012年日本首次在近海進行商業(yè)性可燃冰開采[8];2013 年3月 12日,MH21利用“地球號”探測船在愛知縣渥美半島進行開采[9],在6 d的時間內(nèi)累計產(chǎn)氣量達。
近年來,日本對可燃冰的研究腳步不斷加快,于2017年5月開始了海槽區(qū)(圖3)第二次海洋可燃冰試采研究,成功開采出天然氣。并計劃在2018年開發(fā)出成熟的可燃冰開采技術(shù),實現(xiàn)商業(yè)化生產(chǎn)。

圖3 日本第二次可燃冰鉆探位置
2.3 俄羅斯可燃冰研究計劃及進展
俄羅斯于1965年在西伯利亞凍土區(qū)發(fā)現(xiàn)第一個可燃冰存儲區(qū),試采于 1969 年開始,累計總產(chǎn)氣量約為1.29×1011m3,其中可燃冰約占 47% ,這是世界上可燃冰商業(yè)開采最成功的案例。之后在2007~2009年俄羅斯又與日本、比利時合作,在貝加爾湖進行了多次天然氣水合物開采技術(shù)工藝試驗[10],圖4為貝加爾湖可燃冰巖心。

圖4 貝加爾湖可燃冰巖心
但由于本土擁有相對豐富的油氣資源,并且經(jīng)濟發(fā)展受限,俄羅斯的可燃冰研究僅在巴倫支海和鄂霍茨克海等海域進行,但其開采技術(shù)的研究依然處于世界領(lǐng)先地位。
2.4 中國可燃冰研究計劃及進展
我國對可燃冰的研究和開采運用起步比較晚,與發(fā)達國家相比較,我國對可燃冰的研究晚了30年。
2002年我國啟動可燃冰的研究和勘探工作,2004年我國繪制首份凍土帶可燃冰分布圖并隨后進行首次凍土帶可燃冰鉆探,我國2007年于南海北部海域發(fā)現(xiàn)大量可燃冰層,2013年于南海廣東海域開采出高純度可燃冰樣品,2008年我國在海拔4500 m的祁連山南部發(fā)現(xiàn)可燃冰,我國也是第一個在中低緯度凍土層探測并發(fā)現(xiàn)可燃冰的國家。
2017年9月, 我國“科學”號科考船在我國南海首次發(fā)現(xiàn)了裸露在海底的可燃冰并在同年五月于藍鯨一號(如圖5所示)鉆井平臺上試采成功并創(chuàng)造了產(chǎn)氣時長和總量的世界紀錄。

圖5 藍鯨一號
但這些試采研究的成功,也只是證實了現(xiàn)有技術(shù)可以從自然界可燃冰藏采出天然氣。整體上看,我國可燃冰開采研究處于探索階段,仍需要加速攻關(guān),實現(xiàn)可燃冰商業(yè)開發(fā)。
2.5 加拿大可燃冰研究計劃及進展
從20世紀70年代加拿大就開始了可燃冰相關(guān)研究,在80年代制訂具有重要戰(zhàn)略意識的開發(fā)計劃。 1972年,加拿大在Mallik地區(qū)鉆Mallik L-38井時,發(fā)現(xiàn)了可燃冰的存在。1998年,加拿大與日本合作,在西北Mackenzie三角洲進行了可燃冰取樣。隨后在2002年和2008年又2次在該地區(qū)進行了試采。
但是由于可燃冰的研究難度巨大且費用高昂并受美國頁巖氣快速發(fā)展的影響,所以加拿大聯(lián)邦政府在新的財政年度開始時終止向可燃冰研究項目的撥款,加上自身油氣資源豐富,加拿大水合物發(fā)展計劃有所擱置。
3 可燃冰的開采技術(shù)
可燃冰開采技術(shù)的本質(zhì)是改變可燃冰的動態(tài)平衡(即環(huán)境溫度、壓力等),使其分解成甲烷氣體。
開采主要方法有降壓法,如圖6所示,即調(diào)節(jié)由可燃冰中收取的甲烷速率用于控制可燃冰層的壓力。俄羅斯麥索亞哈可燃冰采用此方法進行了17年開采并獲取30億m3甲烷氣體。

圖6 降壓法示意圖[10]
化學抑制劑法即利用化學試劑如鹽水等調(diào)節(jié)甲烷的收取速度,其示意圖如圖7所示。但是由于試劑費用高昂且容易造成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污染所以運用較少。俄羅斯麥索亞哈用此法使其產(chǎn)量增加四倍,但其價格昂貴,不適合商業(yè)開發(fā)。

圖7 化學抑制法示意圖[10]
二氧化碳和甲烷置換法是指在特定的壓力區(qū)間,用CO2置換可燃冰儲層中的CH4,如圖8所示。此法美國于2012年與日本在阿拉斯加北坡Prudhoe灣區(qū)現(xiàn)場試驗開采成功。此外還有循環(huán)蒸汽激勵法、雙水平井熱水注入法、部分氧化法、電加熱輔助降壓法、二氧化碳輔助降壓法、冷鉆熱采技術(shù)、工業(yè)廢氣置換等。

圖8 氧化碳和甲烷置換法[10]
而且我國在南海開采可燃冰還運用了自主創(chuàng)新技術(shù)包括窄密度窗口平衡鉆井技術(shù)、深水淺層井口穩(wěn)定技術(shù)、松軟復雜礦體開發(fā)技術(shù)、水力割縫儲層改造技術(shù)、水合物二次生成預防技術(shù)、完井與測試系統(tǒng)集成技術(shù)、精準內(nèi)波預測技術(shù)、粉砂質(zhì)可燃冰儲層試采防砂技術(shù)等。
4 可燃冰開采技術(shù)瓶頸
2018年8月25日召開的能源大轉(zhuǎn)型高層論壇上,自然資源部中國地質(zhì)調(diào)查局副局長李金發(fā)表示,未來將科學組織實施“可燃冰”試采。2020年,實現(xiàn)“日產(chǎn)3萬方,持續(xù)一個月”的擴量生產(chǎn)試采目標;2023年前,實現(xiàn)“日產(chǎn)4萬方,持續(xù)一個月”的生產(chǎn)性試采目標;2030年前,初步建成“可燃冰”年生產(chǎn)能力10億m3以上的資源勘查開發(fā)示范基地。這標志著我國可燃冰的商業(yè)化應(yīng)用已穩(wěn)穩(wěn)的站在了其跑線上,但仍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與技術(shù)瓶頸[18]。
4.1 環(huán)境問題
可燃冰雖然被稱之為清潔能源,但其開采過程中因可燃冰氣體不穩(wěn)定性所釋放出CH4導致全球變暖這一環(huán)境問題是不可避免的[19]。
在開采過程中都會釋放出大量的CH4,而且不同于其他溫室氣體,其造成的溫室效應(yīng)是CO2的10~20倍[20]。再加上可燃冰的儲量巨大,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可燃冰蘊含的CH4總量大致是大氣中數(shù)量的3000倍[20]。 所以可燃冰一旦商業(yè)化應(yīng)用,其開采時所產(chǎn)生的排放將會成為造成溫室效應(yīng)的主要原因[21]。
盡管研究表明無論是分布在大陸永久凍土、島嶼的斜坡地帶、活動和被動大陸邊緣的隆起處以及極地大陸架等環(huán)境的可燃冰都是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但是至今都沒有較好的方法在開采過程中直接影響可燃冰的解離率[22~24]。
除此之外,還存在海洋酸化、海底不穩(wěn)定所產(chǎn)生的海嘯、海底泥流以及海洋塌方等環(huán)境問題。
4.2 經(jīng)濟問題
可燃冰的經(jīng)濟問題主要是其開采成本高,因可燃冰的不穩(wěn)定性且儲存環(huán)境較特殊,所以其成本偏高。表1為各國開采可燃冰的成本。

表1 各國可燃冰開發(fā)成本
從表2中可看出可燃冰的開采成本除美國外,其他國家的開采成本極高。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日本與中國大多是從海底開采可燃冰[26~28]。除此之外,由參考文獻[25]中Walsh教授的建模實驗結(jié)果表明[29~31],如表3所示,可燃冰的開采成本比傳統(tǒng)氣體資源開采成本高出3.5~4$/Mscf。所以可燃冰的應(yīng)用不得不面對開采成本高這一嚴峻問題。

表2 Walsh建模實驗結(jié)果
5 對我國可燃冰開采研究展望
我國對可燃冰的認識和研究不到20年,總體落后了發(fā)達國家近30年,對于可燃冰的勘探、形成機理等基礎(chǔ)理論依然處于初級階段, 與國際先進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國可以按照美國的公司和大學合作方式,制定符合我國可燃冰研發(fā)規(guī)劃和技術(shù)道路,促進我國大學、研究院所、公司等機構(gòu)的統(tǒng)一研發(fā)工作,構(gòu)建由企業(yè)、高校和研究院所組成的一體化研發(fā)團隊,加快對可燃冰基礎(chǔ)知識的研究和可燃冰相關(guān)技術(shù)的研發(fā),突破關(guān)鍵理論和技術(shù)瓶頸,在可燃冰的基本物化性質(zhì)及其測試技術(shù)、勘探技術(shù)、取樣技術(shù)、開采技術(shù)、儲運技術(shù)、實用技術(shù)等方面設(shè)立國家層次研發(fā)計劃,加大政策和資金支持力度,爭取早日取得關(guān)鍵理論和技術(shù)的突破,加強與美國、日本等發(fā)達國家進行科研機構(gòu)交流合作。
6 結(jié)論
本文介紹了可燃冰在美日中俄加五國的研究進展以及可燃冰的開采技術(shù),雖然可燃冰的發(fā)展較迅速,但現(xiàn)階段可燃冰開發(fā)仍面臨環(huán)境污染與開采成本高這兩大難題,而且我國由于發(fā)展時間較短,這一方面的研究與其他發(fā)達國家相比較落后,所以應(yīng)加速攻關(guān),爭取實現(xiàn)可燃冰真正的商業(y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