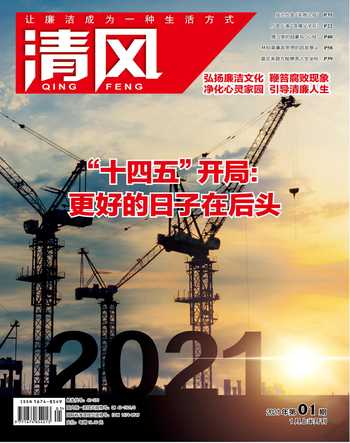印度的假酒假藥與打假
袁南生

假酒是印度的一個“老大難”問題。2019年2月,在印度北部的北方邦和北阿坎德邦,因飲用私自釀造的假酒死亡的總人數達到116人,其中超過100人來自北方邦的薩哈蘭普爾市和北阿坎德邦的赫爾德瓦爾市。受假酒毒害最嚴重的克拉卡里村村民說,在邊界森林地區存在大規模的假酒生產作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這些非法釀造私酒的人會往酒里面摻入甲醇。
回憶起向自己的丈夫賣假酒的那個女人,克拉卡里村民芮娜心里充滿了憤怒和絕望。“我很清楚地記得,一個45歲上下的女人站在高速公路旁賣酒。我的丈夫買了她的酒和朋友一起喝完之后就病倒了,然后他很快就死了。村里的很多人都認得這個女人,她從那天起就失蹤了。我希望她能受到懲罰。”芮娜說。
假酒相對便宜,口味與真酒差別不大,又容易買到,因此制造假酒、飲用假酒可以說已成為印度的一個“傳統”。印度國際烈酒和葡萄酒協會數據顯示,印度民眾平均每年飲用50億升酒,其中假酒比例高達40%。在印度的一些貧困和偏遠地區,正規的酒水飲料已成為當地難以企及的“奢侈品”,人們只能通過各種渠道尋找替代品,以獲得酒精帶來的刺激。
然而,假酒事件并不限于印度的貧困地區。例如,2011年12月,印度東部的桑格朗普爾村發生一起村民因飲用假酒而集體中毒事件,而桑格朗普爾村便處于印度相對發達的地區。貧困地區的假酒事件可能是緣于當地的經濟狀況,但假酒在相對發達的地區的泛濫呢?這確實值得反思。
除卻假酒,印度的假藥問題也十分嚴重。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通用藥品出口國,但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像印度這樣的中低收入國家,十分之一的醫藥制品都是不合格產品或完全假貨。報告稱,全球假藥中的35%都來自印度。
印度假藥生產多,長期以來,印度制藥領域的監管也十分馬虎。因為出口不合標準或已被污染的藥物,印度制藥公司現在飽受國外貿易合作伙伴的詬病。更嚴重的是,當監管者和消費者都開始意識到假藥存在后,制假商就開始在假藥里加入一點有效成分。對他們來說,含有一點有效成分的假藥會多少起點治病的作用,比較不惹人注意。而且,一旦被抓住,他們也可以狡辯說,這是制造過程中的差錯問題,其生產出來的,不是假藥,而是“劣質藥”。這種手法對制造商來說很好用,但對病人來說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這種“劣質藥”成分跟包裝信息無關,甚至可能完全不含包裝上聲稱的成分而含有其他有害病人的東西。2012年,美國田納西州56歲的托馬斯·雷賓斯基因為背痛打了一針,卻因針劑污染而感染上了真菌性腦膜炎,最終,托馬斯因醫治無效死亡。
遏制造假行為的最好辦法就是提高其違法成本。一般而言,造假成本有三種。一是直接成本,即實施犯罪過程中產生的成本,包括作案工具、材料、經費、假冒標志(防偽)等直接開支;二是機會成本,即用同樣時間通過合法途徑謀利也即自動放棄合法經濟活動可能產生的純收益;三是處罰成本,即被查處、沒收、罰款或判刑總和。在違法成本管控上,印度采取三種成本并抓的措施,不僅要打罰結合,重拳出擊,依法治假,加大處罰成本;也強調打防結合,增加造假直接成本;另外,印度政府打扶結合、堵疏結合,以加大造假者的機會成本。
打假,還需保證整個行業運作的公開透明。以假藥問題為例,印度政府政策智庫2018年10月宣布,同甲骨文公司、印度阿波羅醫院及制藥商邁向制藥科學合作,啟動一個用區塊鏈技術建立的真藥供應鏈,對藥品供應鏈的每個環節進行實時記錄,確保整個環節都透明、安全、去中心化且可驗證。除此之外,印度政府也加強了對制酒和制藥產業的監管,要求生產商承擔起其必須分擔的責任。
從本質上來說,假酒假藥的泛濫是社會腐敗的一個集中體現。應對于此,除卻施行機制化的廉潔舉措、發揮媒體效用倡導廉潔理念和設立垂直性的反腐機構,印度也設立了專門機構來整治例如假酒假藥背后的腐敗問題。不僅如此,印度政府還鼓勵和保護舉報,其專門的反貪機構設立了專門的舉報網站收集舉報信息,舉報內容一經查實,該機構便會根據具體情形展開調查。
(作者系外交學院黨委原書記,中國國際法學會常務副會長,曾任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駐蘇里南大使、駐印度孟買總領事、駐美國舊金山大使銜總領事,應本刊邀請撰寫專欄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