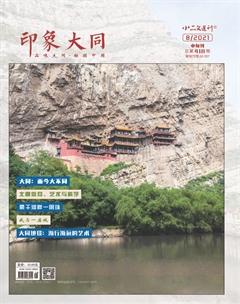我與春風皆過客
許瑋


一
有長城的地方,一定閃爍著歷史的星火。
明嘉靖十八年至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39年—公元1550年),大同府北邊的群山間,數以萬計的兵士和勞工,忙碌地修筑著一項浩大的軍事工程。人流一撥一撥地在山間往返,勞作的號子聲由遠及近、由近及遠,夯土聲由細微而宏大、由宏大而細微,宛如開戰前擂響的陣陣戰鼓,而那一副副袒露著的黝黑的脊梁,正合力將松散的黃土夯筑成一座座結實的墩臺,再彼此相連。至此,原本平緩光禿的山脊上,站立起了一道偉岸的身影——長城。
熾烈而刺目的陽光,照射著兵士和勞工們的脊梁,汗水順著脊背流下,“哼唷”聲此起彼伏。這些終年在山腳下忙碌的身軀,征服著眼前高聳的群山和腳下茫茫的大地。對他們而言,苦難無邊,工事漫漫無期,這或許將是搭上性命的工程。勞作間隙,有人會講一段誕生于這片土地上的傳說,引發大家悠長的遐想;有人會扯著嗓子唱一段家鄉的民歌,思鄉情在山間回蕩;還有的人,或許什么也不說,就那么默默地聽著傳說、聽著民歌,想念身在異鄉的妻兒,淚,從曬黑的臉膛上無聲滑落。
循著歌聲飄向的地方遠望,黃土的墻體和墩臺連接成一條蜿蜒的“巨龍”,隨山勢一路奔騰至遠方。風吹來,天地間涌動著一股浩氣,茫茫群山間,似乎鼓角相聞。可是,這浩大的軍事工程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對整個大明帝國來說,修筑長城既是為了護佑和平,也是為了迎接戰爭,因為北疆的邊防線上,時常會燃起戰爭的烽煙,那么,長城的修筑,就是經年累月的工程了,忙碌而艱辛的勞工和兵士,也許永遠不會知道長城何時能修完。
五百年后,我們來到大同北部的堡子灣。當長城出現在眼眸里的那一刻,人們都由狂喜變得靜默,感覺山間似乎有一股浩氣在繚繞、在游走。佇立在沉淀了數百年歷史的廣袤曠野,面對長城,不必去想那些讓人費解的歷史,單眼前這項工程本身的浩大,就足以令人驚嘆了。
春風從山間吹來,歷史早已歸于平靜,而曾經歷史的樣貌大抵也都無法尋找了。我努力讓自己的心靜下來,想聽聽當年修筑長城的那些血肉之軀們的訴說,還有他們扯著嗓子唱的那一曲曲或凄婉或雄壯的歌謠,然而沒有了,永遠也不會再聽到,只有風從山的那頭掠過,又呼嘯著吹向遠方。
不過我想,和長城相對,就是和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相對;和長城相對,也是和我們漸漸遠去的故土之情相對,而且,真正的歷史,永遠都無法歸于平靜。
二
長城,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最值得稱頌的奇跡,相信所有的中國人面對長城,都會生發出內心最火熱的情感,因為它曾攸關著歷史上那些王朝能否走向安定與繁榮,更象征著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性格和精神。
作家張煒在他的長篇小說《古船》里開篇寫道,“我們的土地上有過許多偉大的城墻,它們差不多和我們的歷史一樣古老。高筑墻,廣積糧,被認為是上上之策,于是在黝黑的泥土上,在貧瘠的山嶺上,就有了那么多崇高連綿的東西。”無數次走近長城,我都會想起這段話,內心隨之涌動著一份無以言說的震撼,甚至懷疑這浩大的工程非人力所能完成!然而,眼前匍匐在山間的黃土“巨龍”,確為我們的先民用雙手所筑,曾是守護家國的屏障。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以漢民族正統思想為基礎,確立了構筑家國一體的戰略防御體系,沿著北部防線設立了九大軍事重鎮,將他26個兒子中的9個,先后分封,以“九大攘夷塞王”之名,戍守邊關,史稱“九邊重鎮”。九邊由東向西分別為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九位藩王所在之地,皆是長城蜿蜒、雄關漫道。明朝中葉之后,為了加強都城防務,朝廷又增設了昌平和真保二鎮,與之前的“九邊重鎮”統稱“九邊十一鎮”,可想大明王朝家國永固的宏大方略。
明朝將長城稱為“邊墻”。明長城東起遼寧虎山,西至甘肅嘉峪關,從東向西行經遼寧、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內蒙古、陜西、寧夏、甘肅、青海十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總長度約為8851.8千米。在帝國統治者的眼中,長城攸關著王朝的興衰,是守護家國安寧最重要的軍事屏障。曾幾何時,那一座座由血肉之軀筑起的酷似藝術品的墩臺上,狼煙四起、鼓聲震天。幾百年后,歷史已然模糊,而長城卻是真實的存在。
明朝后期,朝政日趨混亂和黑暗,邊務也漸漸松弛,戰略上早已由進攻變成退守,長城是明王朝統治極度收縮的象征——長城并不能避免戰爭的爆發,也無法護佑一個王朝國祚永存。到了崇禎年間,明王朝持續走著下坡路,為籌各類軍餉,肆意向百姓攤派,導致虐政不斷,愈來愈顯現出覆滅的征兆。當遼東的“關寧錦”防線被清軍鐵騎突破后,對整個大明帝國來說,耗費無數人力和財力修筑的堅固長城,便徒有其表了。飛揚的黃土塵里,回響著勝利者的得意,也留下了戰敗者的反思。
三
來堡子灣時,正是早春。
大地還沒有解凍,寒冷依然唱著塞北氣候的主角兒,但一望無際的藍天下,已隱隱看得見春天的氣象了。當早來的春風將春天的訊息提前送達,曾經被無數邊關將士踩踏過的黃土地,便迫不及待地想要迎接春天的到來。
一聲鞭響,打破了曠野的寂靜。一群山羊從黃土墩臺下漫過,蕩起陣陣塵土,接著,是一個老漢,抄著手,舉著鞭,瞭見我們的一剎,用手在額前遮個陽棚,覺著有些稀罕。老漢慢慢朝我們走來,友善地微笑著,囁嚅的雙唇,飽含著這片土地千百年來從未更改過的質樸,盡管我們并不相識。
我想與這個放羊的老漢搭訕,因為他布滿皺紋的臉,便是一部滄桑的史書,而他肚子里的故事一定很多很多。不過我想,和質樸的放羊老漢聊五百年前的大明歷史,倒不如和他拉呱拉呱去年莊稼的收成和今春的打算。再細微的歷史也有宏大的因子,而歲月是人的一日三餐,普通人終究和歷史離得太遠,盡管老漢就生活在長城腳下,但還是覺得歷史之于他顯得遙遠。
羊群撒著歡兒在山坡上跑,蕩起的黃塵為烽火臺罩上了一層輕薄的面紗,也將絲絲縷縷的春風攪得有些凌亂。然而,只要老漢的鞭兒一響,羊兒們便很聽話地聚攏到一起,像是從天空落下一團碩大的白云;再一聲鞭響,羊兒們便向老漢這邊跑來,大地隨之一陣躁動,但烽火臺下卻歸于平靜了。
原本寂靜的村莊,回蕩著放羊老漢甩起的聲聲鞭響,循著鞭響望去,老鄉家的窗花明艷絢麗,整個村莊因之而涌動著春天的活力。炊煙像五百年前一樣緩緩升起,我不知人家灶上做的是莜面、黃糕,還是熱乎乎的面條,但想必放羊老漢邁進家門時,炕桌上便飄過飯菜的香氣了吧,盤腿而坐,抿上一口酒,一聲細微的吧咂,人生的知足和逍遙,想必都在那里頭了。
和這放羊老漢一樣,在堡子灣,隨便遇見一個人,坐下來,一支煙、一杯酒,便能給你講出許多故事——透著酒的醇厚,帶著歷史的鋒芒。村里人不懂什么叫“歷史”,他們只知道,那些往事一輩一輩傳下來,都是這么說的,說得人熱淚盈眶,也讓人無端生起鄉愁。酒罷,憨實的身影從長城下走過,腳步輕慢,但影子拉得很長,一步一步踏著時光的聲響,恍惚間,竟看不出他們與長城哪個年輕、哪個遲暮?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這是誰的詩句?或者,是誰在人生的長旅中發出的慨嘆?我與堡子灣的土長城相對,耳畔有呼呼的長風流過,忽然覺得,所有人皆是過客,連春風也不例外,只有長城不會走遠,沉默卻堅固地與黃土地同在,依舊默默塑造著我們這個民族和黃土一樣的品格:一千年如此,兩千年不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