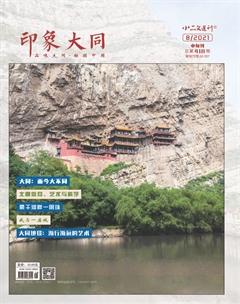我的“半壁江山”
李廣青


我妻劉俊英幾次三番數落我:“你寫這個,寫那個,寫了那么多,也沒見你寫寫我!”
我上高中時,就愛好文學,至今,結集出版幾本小冊子。但是回想起來,還就是沒有關于妻的文字記述。暗自想,哪天吧,我好好寫寫關于你的文字,不為別的,為的記錄我們的曾經,曾經擁有的愛情和三十多年的相處。
我妻小學畢業,娘家在我剛參加工作的鎮上。她的父親,是一所縣辦中學的教導處主任,弟兄四人,家庭條件比較優越。后來,因為愛好寫作,我到安寨鎮上班后,被同事孩子的父母介紹給我妻。
我和我妻見面時,是在她村一位媒婆家。是一個夏日,我站在狹長的院子里等她,也沒有換衣服,穿一件平時穿的白色汗衫,腳穿一只裂開口的棕色涼鞋。停一會,她穿一件可體的碎花衣服,高挑的個兒,娉娉婷婷地走來了,一直走到人家的屋子里,坐下,滿含笑意。我告訴她,自己早年喪父,母親和姐妹供我上學,高中畢業,家中困難,家境不好,高中還是勉強上完的;愛好文學,因為寫就一篇所謂的報告文學作品,被推薦到安寨鎮來了,從事信息資料工作,等等。
也是有心插柳柳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我幾乎沒有問過她什么,這事就這么成了。
結婚時,我家偌大的院子,只有三間北屋和四間東屋。那北屋,很簡陋,秫秸頂蓋瓦,幾層磚砌“堅崛”,二尺厚的“土打墻”;東屋呢,也好不到哪里去,紅磚外包皮,內里都是土坯,花布吊頂,這也是我們的婚房。婚前,我只給了她500元,但結婚時,她大哥開著大貨車,來了很多人,給我帶來了雙人床、立柜、沙發、被褥……應有盡有的東西。
“你曾答應給我買一輛自行車的,沒想到,還是個舊的!”
婚后,說起結婚時的情景,她嘴一撇,埋怨說。
的確,那輛自行車,是我姐結婚時留下的騎過兩年的陪送品。
婚后不久,她便下田下地勞動,泥里水里,沒有計較過。第二年,兒子出生,她除了照料兒子,擠時間,也做家務,還到地里參加勞動。倒是我,因為年輕,珍惜工作和榮譽,也想進步,很少過問家里事。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是她和我多難的母親支撐起我們這個貧弱的家。
而我,剛參加工作時,工資很少,除了零花,也抵不上什么大事,更不要說給她買衣服、買首飾了,改善生活的時候也極其有限。
待到女兒出生,她的內心和我一樣地高興,歡天喜地,過日子的勁頭更加旺盛,仿佛,在我們的面前,展開了一片蔚藍的晴空。我們好像擁有了“小太陽”。她的奶水不足,便買來奶粉喂養女兒,有時也喂雞蛋羹、小米粥、掛面……洗尿布、換被褥,冷了,熱了,白天黑夜地精心照顧。即使如此,她也沒有忘記作務我們的責任田。當時,夏日收割,她頭包毛巾,手拿鐮刀,彎下腰去,“嚓嚓”地,一鐮一鐮地收割著小麥,鐮刀與麥稈親吻,在她身后,是一排排匍匐的麥子;夏收過后,棉花出土,她頭頂艷陽,鋤地、間苗,未曾停歇;棉花該打叉了,她背著年幼的女兒,在高過半身的墨綠的棉田里,伏下身子,一手一手地剝去棉花多余的枝杈……那些年,棉花似乎也值錢,我們因為種植棉花,好像也有些收入,也是全仗憑了她——我的妻。
她身體單薄,可是一個好勞力,干活利索,不惜力氣,似乎不知道“累”是什么?!她用她柔弱的肩膀,挑起了這個家庭的重擔,昂首挺胸,闊步向前。
難怪我已長大的女兒說:“媽媽,你還記得嗎?小時候,我在你背上爬著,你還打花叉吶。”這,讓我心酸,內疚,動情,感恩!
我妻曾因眩暈綜合征住過醫院,我背她上樓,她很感激,事后問我:“現在還背得動嗎?”
但是,我倒應該感謝妻,感謝妻對我的關心、照顧與理解!
因我患痔瘡,曾到醫院做過手術,事后很麻煩,不能動,一動就鉆心痛,每天服藥,換藥,擦洗,全仰仗妻,她沒有絲毫不耐煩,更沒有嫌棄過,一直照顧我到痊愈。
我害病,她心里比我還急,陪我住院,一陪就是一周時間,打飯、喝水、服藥,也全仰仗她。
遵醫囑,每年,我需要輸液保養兩次,每到春天和冬天,她就開始念叨了,什么“你什么時候輸液呀?你該保養了。”說的人心煩,直到我答應輸液保養,她才放心。
夫妻之間,或因觀點不同,或因看法各異,難免勺子碰鍋沿,發生口角,而我的妻,似乎分外的剛強、執拗。一次,我們吵架,她一氣之下,回了娘家,我去叫她,她不回,她的父親和顏悅色地勸我說:“兩口子,不能老吵架,夫妻之間,不是說理的地方。閨女有啥錯,你跟我說。”這話,讓我醍醐灌頂,猛然頓悟,思考很久,至今難忘。
我的脾氣同樣不好,往往愛發“麥秸火”,看不慣的事,往往到家說,我妻總是開導我:“誰好誰壞誰帶著,早晚會有報應的。”讓我甭生氣,消消氣。
近些年,在我妻勤扒苦作和我們的共同經營下,家庭條件明顯好轉,不僅翻建了北屋和東屋,還建起門樓和南屋,償還了一些債務。目前,我們既無外債,也無內債,還有個積蓄。但是,兒子害病,結婚又離婚,讓我們備受煎熬和打擊之苦,我妻的內心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焦急,何等的失望,可想而知。為了開心,融入大伙,也是勞作慣了使然,她開始到蓮花湖公園當園林維護工,勞動著,愉快著,用勞作洗去她積郁的揮之不去的許多煩惱。
我妻對文字似乎不感興趣。家中那么多書籍,她不看,就連我的集子出版后,她也不看,偶爾翻翻內中的圖片。倒是有時間閑暇了,愛玩玩手機,愛看快手之類的東西,我也是納悶了。
記得,結婚前,我曾送她一本白話《聊齋志異》,在書的扉頁寫道:“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企圖引導、激勵她看些書。婚后幾年,我去看她,發現此書,原封不動地保存好好的,沒有一點兒翻動的痕跡。
我妻粗通文墨,認字不多。有次,我們從地里回來,路過一戶人家,門楣上寫著對聯,橫批是“瑞氣盈門”,妻念到:“喘氣盈門”,讓我笑了好一陣子。此后,我說起這事,她也笑了,然后正色道:“你不知道俺文化淺嗎?往后,不許說這事!”
我妻是一位農婦,一位地道的樸實本分的農婦,終日的勞作,使她的臉膛和膚色被曬得黎紅,皮膚似乎也粗糙了,那是勞作留給她的印記,是她的榮耀與飽滿的收獲。至今,我不曾為擁有這樣一位妻子后悔過,倒是為她感到驕傲、自豪與滿足。
前些天,我所在的單位讓我補繳欠繳的養老金,我們的積蓄也很有限,平時,都由我妻掌管。說過此事,我妻慷慨地拿出存款折,和我一同到金融部門,辦理了較大數額的匯款手續。
那錢,有我掙來的,也有我妻掙來的,當然,也有種田的收入,包含著我妻的辛勞和汗水,它是我們共同勞動的產兒。
妻,我的“半壁江山”。如此說,并不為過。
我愿與我妻攜手并肩,歷經風雨,生死相依,默默地度過每一個晨昏,走過年輕,走過半百,走向年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