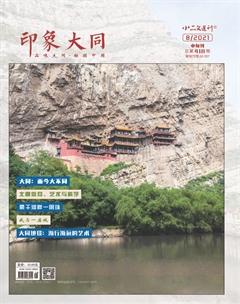新的審美向度與生存困境的抒寫
馬桂君

時代紛繁復雜,今天的文學觀念和創作形式呈現多元分化的狀態,經典文學創作的份額被切分。再加之理論上的文學原型和母題早已在太陽底下攤開幾千年,新銳的各路文學寫手又無孔不入地翻熟了通俗到高雅的可耕地,作家想要創新突圍越來越困難。今天的嚴肅寫作及寫作的成果,在眾多蕪雜的數字娛樂自媒體中使傳統文學守住了一席之地,描摹時代面影的同時葆有詩性的審美價值,并給予多層次閱讀需求深度體驗和評論研究的延伸,這些都是傳統作家寫作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石囡(史龍躍)的兩篇新作《子虛鎮的蝙蝠人》和《蜜蠟是個流氓》,可以作為一個系列來分析。前者是兒童視角,而且是特殊兒童的視角;后者則是少年視角,合在一起可以命名為“成長羅曼司”系列。革命的羅曼蒂克,指的是將革命和戀愛結合的寫作模式,而“成長的羅曼司”,則是從孩提到少年,幻想中的黑道風云、城市超人和現實生活的灰暗污濁、貧乏平庸相對照。不過有一點是共同的,今天的羅曼司和過去的羅曼蒂克都僅指涉想象和言說,照不進現實。
《子虛鎮的蝙蝠人》最重要的意義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個新的意象——蝙蝠人,并隨之發展出新的審美向度——介于審丑和暗黑之間。從未知國度流浪來的蝙蝠人既像一個工業時代的廢棄品,又像是娛樂時代的文化怪胎。它有多面立體的行為表現,畫畫、讀書、說外語。“異人”自唐宋傳奇就多有記載,自古便是文學創作天然獨特形象的來源。出現在子虛鎮背景下的它,在展示自身的同時也展示了時代的荒蕪:天氣惡劣異常、工廠不景氣、學校破敗不堪,官僚主義橫行。它作為時代的廢棄物,只能看到什么吃什么,因為無從選擇。這又讓我們想起了卡夫卡《饑餓的藝術家》,他徒勞的抗爭與蝙蝠人的屈從有一定內在的關聯。
但是子虛鎮的蝙蝠人既不像變成甲蟲的格列高里,又不是石頭崩裂造出的神猴,它是我們這個時代幻想和現實交疊后的產物。蝙蝠人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可以用來標記我們的時代,說是時代烙印也不過分。因為我們的時代印記,不應該僅由政治社會事件來命名劃分。文化娛樂形象已經成為社會的一員,它們作為人人熟知的共同記憶,可以視為一個個標簽或者時代的象征物來分割歷史。所以我們的文學話語中會自然而然出現這樣的表達:那是在遙遠的2021年,李煥英正在各個城市里面引得人們痛哭流涕……。
諧謔并消解城市超級英雄的故事,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融合,把跨越了地域文化限定的大眾形象移植、再生,進行再利用再創作。可資書寫的資源已經不僅來自現實生活,還包括既有的精神創造。今天的城市沒有神話,神祇跌落到人間象征著文明發展的拋物線。超級英雄落難,是因為現實不能提供英雄生長的土地和空間,就像污染干涸的河水不能再養育出游魚。
其次,小說形象化地表現了農業社會在工業化沖擊下生命的存在困境。污濁、干涸、怪異的生存世界像猙獰的荒原,與傳統理念架構下的溫柔敦厚優美和諧形成對照,言說的是現代人的生存困境。作者配合魔幻超現實的手法,以類似現代聊齋志異的怪異人物荒誕故事為中心,傳遞出來的已經不僅是個人化的情緒體驗,而是上升為寓言性的人的整體存在困境——異化。對于社會和人生的荒誕及不可理喻,作家本能地感知到,但是傳統的手段在此刻顯得無力,因為既有的話語經驗難以表達尚未表達的空間。既有的表達信息輸出者和接受者已經在建好的軌道兩端,溝通瞬時完成。而“孤獨”“漂泊”“失語”等等諸多已有詞匯都不足以表達存在本質上的荒誕性。語言的盡頭是意象,于是獨特的意象被創造出來,蝙蝠人如同一個蒼老的先鋒,獨行在現實的荒原。
如果非要提煉一個主題的話,我的揣測是文本試圖通過一個美國故事里的形象代碼,植入對環境異化的思考,當然也包括人的異化問題。一個超級英雄類的傳奇人物,被迫吃進各種垃圾,異化為長著膿包的怪胎。讓人聯想到《千與千尋》里面被污染成腐爛神的河神。焦化廠、棉毛廠、廢水等詞匯,都和工業化的后果相關聯。可惜的是這樣的主題意念太過陳舊,關注環境保護,早已過了提出問題的階段。現在面臨的是如何積極應對的現實選擇問題,如碳中和、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等等。
作者的創作動機首先是影響的焦慮(來源可能是馬爾克斯、尋根文學、陳染林白某些私人寫作等),再加上創新的焦慮。如果主體想要表達的觀念很急迫,往往在文本中體現為多線索觸角。作者使用拼接的手法,讓故事和記憶的點滴隨機組合。既然康定斯基讓我們認識到可能沒有形式才是最深刻的形式,所以隨機拼湊或許比人為刻意擺布能達到更合理更現實的結果。生活的非本質性讓邏輯和規則喪失了統領性。作者在此觀念上又配合兒童視角的形式,以無先驗性理論填充和認知建構的懵懂頭腦、不解的眼睛、無法言說的限定(因為皮皮只啞不聾),來看怪誕荒蕪的現實。三重疊加后文字的折射散射效果,因光線多次變形,波互相干擾,形成光怪陸離的繁復畫面。
《蜜蠟是個流氓》呈現的則是曾經年代留在記憶里的場景,包括物質貧乏年代關于貧困的個人記憶和成長的煩惱。小鎮上的少年,幻想和凡俗平庸生活邏輯不一樣的“黑道”社會,打打殺殺快意恩仇。香港黑幫電影實際是傳統武俠小說與現代言情文摻和后的產物,在個人英雄歷史中加入了情愛糾葛的元素,滿足平凡卑微孩子的英雄幻想。渴望成人世界大概是每個少年體內都必須要有的生長素,同時也可以成為催生藝術創造的力比多。
到了后半部分,幻想中的反日常還是掉落到了平庸的日常中。關于群毆過程兩種矛盾的說法,一種可以代表想象的電影式的場景,另一種則是真實的日常的場景。既沒有真刀真槍的流血犧牲,更沒有驚世駭俗的桃色事件,蜜蠟既沒有成為流氓(這里流氓約等于英雄),連偷窺女生洗澡的小插曲都輪不到他主唱。
對于個人而言言說過往非常重要,因為這些碎片是僅存的記憶填充物,作者展示出來,是期待讀者閱讀后產生共情,如果愿望達成,那么作品可以說是充實立體的。這要求基于個人成長背景下的成長記憶,要實現對社會歷史的還原、勾連的有機建構。言說記憶如果沒有形成具有個人性的、藝術化的表達,或者說在別的作品里面有更形象化的方式表現過了,記憶碎片的價值要大打折扣。簡言之,沒有典型化的環境和典型化的人物,個人記憶會因缺乏深度而降低辨識度,人物形象也無法鮮明立體,容易湮沒在時代的混沌底色上。
典型的環境加上典型的人物,依靠藝術性的轉化方式,創造出新的意象或者觀念,是現實主義的必由之路。對比《山鄉巨變》《暴風驟雨》的寫作過程,說到底還是因為創作主體真正地經驗了生活,實現對生活由細節部分的紋理到整體邏輯的把握。作品缺乏典型性,首先是因為生活的限制。創作一方面來自生活,另外一個維度就是虛構。具體的創作主體如果生活經歷不能體驗到足夠的“典型性”,缺乏歷史的深度,那就要擴張虛構的能力。可是虛構歸根結底又不是天馬行空的,而是必須建立在符合生活邏輯的基礎上。
我們今天的批評是為了讓一個有希望的作品更加完善,所有我說的大部分都是問題。我想作者最大的問題是回避了現實主義,他的回避直接原因是缺乏生活現場的經驗,跟不上時代的節奏,只能從印象中捕捉到零散的意向進行演繹,導致發力點不是形象自身,而是作家自己的虛構能力。實際上當形象按照自身的邏輯站立起來后,作家的主體性對歷史邏輯、人物性格的掌控幾乎失效。馬列主義文論強調“現實主義的勝利”,能夠成為現實鏡子的作品,就是因為充分把握生活的現實和人們的精神意識以及社會生活矛盾沖突的本質,所以表現的東西超越了創作主體的世界觀。比如托爾斯泰生活在沙皇年代,他代表的是地主階級,但是他的作品能傳遞出資本主義甚至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信息。
作者在創作中勇敢地進行了形式方面的創新。但是形式創新的空間相對比較狹窄。以形式開啟文學創作的先鋒性,只有第一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后面跟隨的都是影子,大多給讀者留下的只是一個模糊的印象。另一方面,缺乏歷史內容創作會流于現象的層面,局限在個體的天地,走上自然主義的小徑,而現實主義卻是無邊無際的。所以,就上述兩篇作品來看,如果將應有的歷史深度和典型性有機關聯,提煉出能表征時代和社會的主題意象,加上石囡富有詩性的語言功力,相信他的創作會更上一個新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