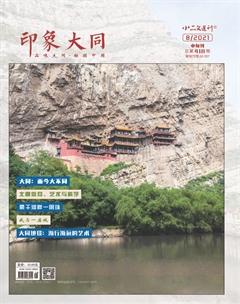大同地毯:漸行漸遠的藝術
宋元林


地毯是我國著名的手工藝品。有文字記載的可追溯到 3000 多年以前;有實物可考的也有 2000 多年。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在《紅線毯》詩中有“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的名句。根據文獻記載,在唐宋到明清,地毯的品種越來越多,常以棉、毛、麻和紙繩等作原料編制而成。編制中,使用強度極高的面紗股繩作經紗和地緯紗,在經紗上根據圖案扎入彩色的粗毛緯紗構成毛絨,然后經過剪刀、刷絨等工藝過程而織成。其正面密布聳立的毛絨,質地堅實,彈性又好。
地毯最先始于西北高原牧區,維、蒙、藏少數民族為了適應游牧生活的需要,利用當地豐富的羊毛捻紗,織出絢麗的跪墊、壁毯和地毯。我國西部的新疆早在 2000 多年前就生產地毯,并能織出各式圖案。尤其以新疆和田地區所生產的地毯最為名貴,有“東方地毯”之美譽。與大同毗鄰的呼和浩特市的地毯早年也來自新疆,俗稱“西營毯”。后來從寧夏等處來了幾位師傅,帶來了編織地毯的技藝,才有了當地的地毯業。
我們大同地處塞北高寒地區,又處在游牧民族與中原農耕民族的接壤地,所以也盛行使用毛織地毯,大同人習慣稱之為羊毛地毯或栽絨毯子。大同自古與內蒙古民間貿易往來頻繁,最早內蒙古的地毯和毛制品流入大同,被大同人稱之為“西路貨”。
新中國成立后,大同、山陰、渾源、廣靈等地相繼建立了地毯廠,尤以大同縣(今云州區)地毯廠為最。
大同地毯廠的組建,大約在 20 世紀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當時,大同市城區人民街(后改為大北街)辦事處興辦了街辦工業“人民街地毯廠”,廠址設在大東街太平街口路東,開始了手工編織加工羊毛地毯。羊毛原料主要從內蒙古地區購進,先用羊毛加工成毛線,再經過反復試編最終編織出了大同生產的地毯產品。基本具備了彈毛、紡線、染色、織地毯這些工序。大同地毯具有舒適耐用、隔潮保溫、除邪祛寒、冬暖夏涼等特點,既有使用價值,又有藝術欣賞價值,且物美價廉。一經投入市場就受到人們的歡迎。
那個年月大同地毯廠很是火了一把,產品銷量很好,職工福利待遇也不錯。后來,大同市毛紡織廠與大同市城區人民街地毯廠合并,地毯廠成為毛紡廠的一個車間,隸屬市二輕局管轄。雖然兩個廠子資源整合強強聯手,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還是被淘汰,大同地毯只能留在大同人的記憶中了。
那時,我老公中學時的美術老師在鄉下一家地毯廠任廠長,他特意帶我去工廠參觀,讓我有幸見識了地毯的編織工藝。趙老師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先給我們普及了一些基本常識。從地毯的分類說起,按制造工藝分為手工栽絨地毯、手工編織平紋地毯、手工簇絨地毯、手工氈毯等;按用途分有地毯、炕毯、壁毯、祈禱毯等;按原料分有羊毛地毯、絲毯、黃麻地毯、化學纖維地毯等。產品分三藍地毯和帶彩地毯。道數有 60 道、70 道、90 道,最密的有 120 道。聽說后來又發展到 540 道和 720 道以上的地毯,規格也有十來種。
加工地毯有紡紗、染色、繪圖、加工、平整、干洗等多種工序。編織地毯需要木制機梁、刀子、耙子、剪毛剪子、平毯剪子、剪花剪子等。其中主要工具是地毯梁,由四根木頭搭成一個正方體。上下木頭要求質量高,因為織工要把纏在上面的緯線繃緊;左右的豎木打千斤,次一點也行。緊挨地毯梁的是能上下伸縮的副梁,織毯的人坐在上面可上下調節。趙老師帶我們來到一間工作間,幾名女工正在看圖編織掛毯。看她們嫻熟地繞邊、過頭緯、拉絞……她們眼里看著圖紙,一手抓著毛線,拴在緯線上,一手用刀砍斷,太長了浪費毛線,太短了又不合格,必須拿捏得較為準確。我們親臨實地觀看她們編織,猶如靜觀一朵花慢慢綻放,體會到了“慢”的妙處。我看著墻上寫著生產掛毯的上百道工序,僅僅是編織工藝,就有上徑、拾徑粘膠、打水平、鎖底子等 30 多道工序。這一道道工序下來,是手藝人莊重于物的一段心路歷程。
地毯不僅有使用價值,還有藝術欣賞價值。臨行前,趙老師又給我們展示了廠里的圖案樣本,約有 20 多種。五龍、五云、五牡丹、孔雀、龍鳳、八駿全圖、梅蘭竹菊、鹿鶴同春、山水、水鳥等圖案,淡雅素靜,新穎別致。趙老師說圖案的繪制原來由老師傅用符號點在格子紙上,后發展到請畫師畫樣子。趙老師到地毯廠工作,可謂學以致用了。
大同有地毯廠的歷史雖短,但使用較早。大同人最早使用地毯不是鋪在地上而是炕上,所以把地毯稱作“炕毯”。早年間大同四合院民居房屋的面積小,除了一條火炕所用的地方以外,地就更小了。而大同地處塞上,一年四季氣溫很低,如果不燒炕火炕皮很涼,鋪上一塊地毯或氈子,可以起到隔潮和防寒的作用。當時地毯的尺寸有 3 尺乘 6 尺的單人地毯,還有 5 尺乘 6 尺和 5 尺乘 8 尺的。不過,那時炕上能鋪一塊地毯屬有錢人家,一般人家鋪的是蘆葦或高粱蔑青編成的席子或花油布。隨著改革開放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曾經貴族化的地毯變身平民化,許多入住到電梯樓房的人家都在大客廳地上鋪上了地毯。
地毯的生產隨著機械化的加速度,機器制作漸漸取替了手工制作,手工地毯成了漸行漸遠的藝術。而使用地毯的人家也嫌打理不方便,漸漸從家庭中退出了。
選自《今日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