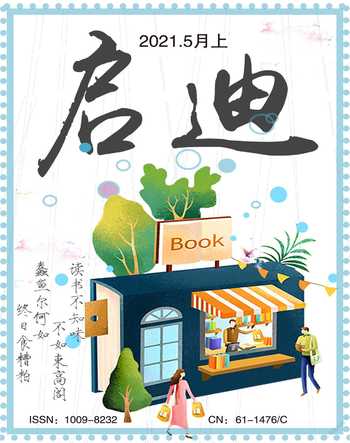從“花街”到“耶路撒冷”
馬圓圓
摘要:《耶路撒冷》記錄了花街一群70年代出生的孩子成長、離開、迷失、回歸的人生歷程,向讀者呈現了70后“一代人復雜的精神世界和完整立體的社會”。小說采用了多種敘事方法,使每個故事都在層層遞進,在互不相干中又相互關聯,形成蜘網狀的敘事結構。本文將淺談作者是如何運用并置結構的空間敘事來展現《耶路撒冷》的人物故事以及敘事藝術。
關鍵詞:空間敘事;并置結構;景天賜
《耶路撒冷》主要講了主人公徐則臣為了籌集到求學耶路撒冷的學費,回到老家花街賣掉祖宅,接著與幾位兒時伙伴,易長安、秦福小等人以及初戀舒袖相遇,面對不同的人生,他們分別開始回顧起曾經的生活境遇以及理想追求。這部小說記錄了70后這一代人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的故事的縮影,描寫了花街一群70年代出生的孩子成長、離開、迷失、回歸的人生歷程,向讀者呈現了70后“一代人復雜的精神世界和完整立體的社會”。小說采用了多種敘事方法,使每個故事都在層層遞進,在互不相干中又相互關聯,形成蜘網狀的敘事結構。本文將淺談作者是如何運用并置結構的空間敘事來展現《耶路撒冷》的人物故事以及敘事藝術。
“并置”這個概念最早是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并置”的概念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弗蘭克在1945年首次提出,這個概念是他對現代小說使用的一些敘事技巧的歸納總結。它是指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各種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聯系,使他們在文本中取得連續的參照與前后照應,從而結合成一個整體。并置強調的是打破敘述的線性時間流,并列的置放那些或大或小的意義單位,使文本的統一性不是存在于時間關系中,而是存在于空間關系中。作為小說結構上的情節并置是并置敘事的主要組成部分,也就是主題-并置。就如在這部小說中,70年代為大背景,以花街作為出發點,幾個人物去向了不同的人生。每章都圍繞他們各自的人生展開故事,同時穿插一個關于70年代的“我們這一代”專欄,作者用主題上的統一性把這幾個人物再全部連接起來。70年代的人都有自己一本難念的經和一直在訴說的過往,他們來自同一時代,他們向往理想主義,他們都需要精神的自我尋找。通過幾個人物故事的并置,讓作者更加深化主題,他將筆端觸及到了整體社會的文化結構和集體潛意識中,以純凈的精神領域為敘事立場,給作者筆下的人物乃至當代處于精神困境的群體以精神上的終極寄托。這幾個在情節上互不相干的人物故事由一個統一的主題,也就是“到世界去”將其連接起來。幾個故事的中心人物都被卷入一個“心靈救贖的精神世界”的漩渦事件當中去,通過幾個人物故事的并置,以70年代正在轉型的生活作為大背景,從社會不斷變遷發展的角度來看“耶路撒冷”這個理想世界的不斷進展。
在《耶路撒冷》這部小說里,作者直接以人名給每個故事進行直接命名。并且設置了奇數章和偶數章,作為主人公初平陽依次和其他主要人物舒袖、易長安、秦福小、楊杰以對稱的方式從兩邊往中間排列,其中景天賜則是對稱軸的軸心。這樣的巧妙設計是因為每個人物之間的故事各不相干,但又因為景天賜的死讓每個人都飽受折磨,大家內心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結,誰都和小時候害死景天賜有間接的關系,從而想要獲得心靈救贖。這又讓幾個人物的精神層面相互聯系起來,希望出去、或回歸都能獲得解放。最終發現,能夠獲得救贖的“耶路撒冷”就是回到共同的故鄉-花街,前后呼應。以“初平陽”開始,也以“初平陽”結束,形成一個封閉的體系。
從小說的外部狀況來看,以花街為中心的世界以及人物等都被被置于平行結構狀態。小說一共并置了幾個主要人物;易長安、秦福小、楊杰,和景天賜以及他的初戀舒袖。同時,作者穿插了十個“我們這一代”專欄,主要討論70這一代人的故事。小說里的專欄看似和每個人物都毫無關系,但作為70這代人,每個人都像專欄故事里的縮影,專欄里的故事也像就正在發生在每個70代人的身上。幾個并置的人物故事就像平行的縱軸,而景天賜就像一個橫軸將每個人連接起來,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小說以一群年輕人逃離與回歸故鄉之路為核心,探尋迭代更新的社會下人們復雜的現實與精神生活縮影,構筑出“70年代人的心靈史”。文體的交叉互補和語言的變化多端形成敘事空間的多重性,嵌套、并置、殘缺、互補,它們在一起構成一張蛛網,隨著人物的歸鄉、出走、逃亡,蛛網上的節點越來越多,它們自我編織和衍生,虛構、記憶、真實交織在一起,挾裹著復雜多義的經驗,最終形成一個包羅萬象但又精確無比的虛構的精神世界。《耶路撒冷》這種看似沒有中心,每個人又很重要的結構和寫法,讓每個人物都變得像主角一樣重要,就像我們正在身處這個世界的感覺。它關乎鄉村/ 城市、出走/ 歸來、故鄉/ 世界之間的選擇與平衡……以及永不停息的追尋美好的理想與渴望。
參考文獻:
1、羅玉超,地理·情感·精神:《耶路撒冷》的多重意涵解讀 《美與時代(下)》 2020,2
2、徐則臣.到世界去---都市重壓下的心靈回歸[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1.
3、徐則臣長篇小說《耶路撒冷》:花街的“耶路撒冷”,梁鴻,《文藝報》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