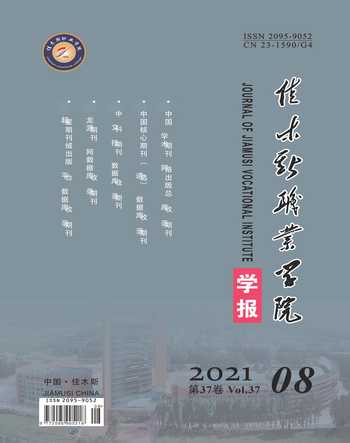城市邊緣人的精神隱憂
梁明月
摘? 要:陳倉的《反季生長》是在作者探討一系列進城小說的主旨的基礎上再次探討的還鄉主題。通過塑造一系列以農作物命名的人物,傳達出城市邊緣人物的精神掙扎,在抒寫這些進城邊緣人物精神現狀的同時,試圖用文字來喚醒眾生對這些群體的關注,深切地體現出陳倉的悲憫情懷和社會責任感。本文以陳倉的《反季生長》為例剖析異域文化中城鄉人的精神隱憂。
關鍵詞:城市邊緣人;陳倉;精神隱憂;《反季生長》
中圖分類號:I20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1)08-00-02
一、關于城市邊緣人的形象
拓撲心理學的創始人庫爾特·勒溫在“邊緣人”的概念中提出,“邊緣人是對兩個社會群體都參與不完全,處于群體之間的人[1]。”在社會學中“邊緣人”主要指游離于多數群體的少數個體,他們在邊緣環境下過著進退兩難的生活。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原本的城市迎來了一批又一批的他鄉人,給城市和社會注入活力,他們存在并重要著,但是城市對他們是排斥并接納著。這些城市中的異鄉人,他們因為太多不可調和的矛盾而努力掙扎,在城市生活中懷念著故鄉的影子,卻也無法做到身心完全回歸故鄉。就像是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馬爾克斯在他的代表作《百年孤獨》中談到的,如果沒有一個親人埋在這里,這里就不能稱之為故鄉一樣,陳倉獨特的人生經歷促使上海成為他所謂扎根的一個地方[2]。同時,扎根生活的城市上海和出生地陜西小城對于陳倉來說就是一片寫作的陣地。《反季生長》以一段從上海回老家陜西丹鳳縣的大巴車上的故事,剖析了社會現實和人物情感的隱痛。
(一)努力扎根的城市農民工
陳倉的《反季生長》中塑造的大白菜、棍子山藥、大鴨梨等角色就是努力扎根城市的一批農民工形象。他們來上海的目的很簡單,純粹是為了賺錢,但是往往付出與得到無法成正比。他們處在所謂城市的下層,想努力融入城市生活,但是城市卻一直排斥著他們,正如棍子山藥在與大白菜的聊天中憤怒說出的只有在上海這個地方充當小日本,才能抬頭生活,不被別人欺負的那番話一般[3]。他在上海這個城市的夾縫中求生,并努力偽裝自己,為的只是讓上海人看得起,只想在上海這個城市生存下去,可是這座大都市并沒有因為他的這些“努力”而真正接納他。棍子山藥的內心還是明白自己終究還是要回到家鄉的,他似乎能在城市的生存中想象到自己回歸家鄉的情形,所以他和大白菜說他們這類人終究還是要回到家鄉的。但是他所謂的回到家鄉對于他來講只是肉體的回歸,在城市這么多年,他們已經習慣城市生活的節奏,適應了城市生活的規律,即便是生他的故鄉,所有與城市生活對比該有的不適也會伴隨他們肉體的回歸接踵而來。他們至少眼前的奮斗目標是能夠在大城市中扎根生存。
(二)城市中的農門學子
城市異鄉人物陳沅,是通過高考的途徑脫離了鄉村,并且和上海人結婚。看似是扎根城市的生活,但是卻因為生活習性、價值觀的不同以及身邊人作為上海人的優越感,讓他們覺得備受屈辱。就像是陳沅和妻子商量在假期一起回陜西老家時,妻子無比失望的狀態一樣,因為妻子所謂的假期旅游至少應該去日本這樣的國家[3]。陳沅內心是想帶妻子回家的,但是兩人因為對旅游的概念理解不同,加之妻子確實是內心看不起陳沅的陜西老家,所以他內心深刻明白,對于上海人,對于城里人,回家是沒有任何意義的。他也不明白回家的概念意味著什么,因為上海本就是家。但是對于出生在大山里的陳沅來說,回家的意義卻意味深長,家對于他來講更是精神的一個歸宿。
陳沅第一次吃車厘子時因為并不知道車厘子這種水果的存在,所以說它是櫻桃,他的妻子嘲笑說,“我就說你們鄉下會有櫻桃,怎么會有車厘子呢?”陳沅原以為他與妻子結婚的事實,至少能夠讓他在上海這個大城市徹底地穩定下來,擁有屬于自己的家[3],這也是他來上海的目的,也是在上海的所得。可最終陳沅選擇了逃離婚姻,他想去尋找櫻桃樹下的女孩。小說結尾談到,當他知道那個女孩擁有自己一片果園的時候,他覺得自己釋然了,同時他也覺得有必要回到喜歡吃蘋果的年代。可是事實再一次叩問他,櫻桃可以反季生長,陳沅能做到反季生長嗎?他在參加完侄女的婚禮之后還是要回到上海的,他在上海能找到漂泊的終點嗎?陳倉在簡單的鋪敘中,直面人性的軟弱,直面時代的迷茫,對當下許多背井離鄉、選擇城市生活的人進行了認真的反思,進城人員在扎根之后如何才能讓自己的靈魂得到安妥。
二、城市邊緣人物的精神掙扎
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在作品《鄉土中國》中曾指出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特征[4]。陳倉說,我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讓我用幾個詞來反映,有冷漠,有浮躁,最想說的是不安,不安是一種常態,正如女大夫所言,像有一枚炸彈。作家路遙作品《人生》中的德順老漢在勸高加林的時候說,農村人無論什么時候,總是要落葉歸根的,因為都是土里生土里長的苗,根都深深扎在土里面。這是那個年代的人對故鄉的情感,隨著社會的發展,越來越多進城的人為了生活、醫療、教育等因素努力扎根城市,但是城市卻是他們始終融不進去的一堵厚墻。
(一)進與退的抉擇
陳倉從城鄉對立的角度切入,以粗獷的語言塑造出大白菜、棍子山藥等角色。大白菜和棍子山藥進城的目的很簡單,純粹是為了賺錢,就像棍子山藥說他們在上海賺的那點錢還不夠買房子,所以終究還是要回到農村的。在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很難遇到棍子山藥所說的既愛吃土豆又愛吃漢堡的兩邊都懂的人,朋友于他們而言可能就像是奢侈品一樣不可遇,更難求,所以他說不得憂郁癥也會變成瘋子[3]。可是他真的能夠回歸故鄉嗎?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大白菜所說的“關鍵是夫妻之間說不到一塊去了”。他的老婆死活不相信樓比山高,橋再長也長不過他們家門前的小河,并且他的老婆見到人多就惡心,所以她出不去山村,更不可能到城市中生活,這便是棍子山藥在城市生活的一道鴻溝。他說自己在外邊混了那么久,不能說有多大出息,起碼是見過大世面的,所以鄉村生活已經滿足不了他對生活的需求,回不去也是必然的。他們已經習慣了大城市的文明和繁華,就不想要再回到農村,可是城市卻因為種種原因,并沒有他們的容身之處。就像是看過了大海,才會無視河流的渺小。農村的生活就是渺小的河流,已經容不下看過大海的這些進城人員了。面對這些情況,他們的不安更加明顯。陳倉在細致深入地刻畫大白菜和棍子山藥等城市務工人員內心的迷茫和在城鄉對立下他們婚姻上出現危機的同時,試圖用文字來喚醒中國對這些城市邊緣群體的關注,深切地體現出他的悲憫情懷和社會責任感。
(二)身與心的分裂
陳沅在上海無法融入的精神困境使他無比羨慕家鄉人的生活,雖然處在可能令人羨慕的大上海,他的心靈還是向往故鄉的。在商洛老家,陳沅從姐姐口中得知,“櫻桃樹”承包了村里荒廢的莊稼地,成為農村致富的典型,完成自己的人生逆襲,他開始思考自己當年的選擇正確與否。所以他覺得如果沒有十八年前的那件事,“櫻桃樹”也應該到城里去了,同時他也覺得如果當年“櫻桃樹”也像他一樣進城的話,可能和他一樣逃脫不了這些悲哀與苦惱。而陳沅的堂弟卻和他們有著不同的經歷[3],因為當年學習成績差落榜而回家種地,卻能靠著收購核桃木耳和山藥成為富裕人家,至少不會有成為邊緣人的苦惱。他們沒有通過高考這條必經之地進入到城市,過上城市人的生活,在十幾年前,與陳沅相比,他們都是十足的失敗者。但是十幾年之后,他們這些遺落在鄉村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如今的生活比進城人員過得更加富裕穩定。陳沅明白自己的隨波逐流已經與“櫻桃樹”的成功之間有巨大鴻溝,自鄉人對故鄉精神家園的堅守是陳沅這些進城人員體會不到的。相比而言,他們這些進城人員是悲哀的。所以他對自己進行叩問,如果當年的自己同樣也失去上學的機會,留在封閉的農村,他是否也能像“櫻桃樹”一樣擁有自己的果園呢[3]。
面對自鄉人對故鄉家園的成功堅守,異鄉人對自己看似成功的人生開始懷疑。所以當堂弟來上海的時候,陳沅妻子以上海人的優越來俯視關于陳沅的一切,所以她以聽不懂鄉下人講話為理由而拒絕與他們一起吃飯,此時的陳沅內心深處再一次叩問自己選擇的正確性。現在的陳沅在堂弟面前,唯一有優越感的是自己還是一個文化人,還有一個當作家的夢。但是對于陳沅自身來講,他本身所取得的文化人的身份也不能改變他的窘迫和尷尬[3]。
三、結語
反季生長的本義就是違背了自然規律來改變一些作物的生長環境,其結果是無法與正常時令的農作物相比較的。“異鄉人”就像是反季生長的作物一樣,成為名副其實的反季人物,在進入城市完成自我他者化的過程中,導致其主體意識的喪失和身份認同尷尬。他們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完全接納他們的文化,甚至連家鄉也逐漸不再擁有屬于他們生存的文化之地。在現代信息網絡快速發展的時代,或許網絡的多元化發展能縮短城鄉之間的距離,消解一點異鄉人的在城市生活中的隱憂。
參考文獻:
[1]鄒林鳳.精神的漂泊者——論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中思特里克蘭德的邊緣人形象[J].青年文學家,2011(24):81-82.
[2]張曉英.背著故鄉去遠行——論陳倉的“進城系列”小說[J].曲靖師范學院學報,2017,36(5):32-35.
[3]陳倉.反季生長[J].作品,2018(8):4-33.
[4]孫長江.“城市游牧人”:異鄉人的宿命?——評《家在水草豐茂的地方》[J].美與時代:城市版,2018(2):107-108.
(責任編輯:張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