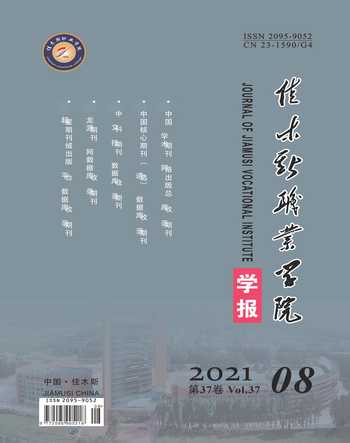《書面糾正性反饋與二語發展》評介
朱一凡 湯志明
摘? 要:本文對John Bitchener 與Neomy Storch的新作進行了介紹,并做了簡要評價。該書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了二語寫作反饋領域的最新研究以及理論依據,為國內二語寫作教師的教學實踐提供借鑒以及為二語寫作反饋研究提供理論指導。
關鍵詞:《書面糾正性反饋與二語發展》;二語寫作;反饋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1)08-00-02
二語習得在研究領域里一直具有爭議性,因此也產生了很多關于此方面研究成果的話題就是書面糾正性反饋。其中, 反饋是否能促進二語的發展是一個引發了很多針鋒相對的觀點。例如,Truscott持續地對二語習作中的語法錯誤提供反饋這一行為進行了批評,而有大量的研究人員則通過實證研究表明書面糾正性反饋無論是對于學習者在短期,還是長期的寫作表現方面都有明顯幫助。
奧克蘭大學的John Bitchener教授以及墨爾本大學的Neomy Storch合作的新書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L2 Development(John Bitchener&Neomy Storch.2017.Written Corrective Feedback for L2 Development. Bristol;Buffalo:Multilingual Matters.ISBN 9781783095049 )從認知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兩個視角,圍繞糾正性反饋是否對二語發展有積極影響這一議題,提供了較為全面的綜述和批判性的分析并基于該分析提出一系列研究建議和展望。
一、全書簡介
全書分為六章。在第一章中,作者介紹了該書的寫作目的,界定了核心概念,解釋了書面糾正性反饋研究的意義,并對全書的結構框架進行了總體介紹。第二章從認知理論視角探討了書面糾正性反饋與二語發展的關系。第三章從認知理論視角下對書面糾正性反饋研究進行了回顧。第四章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探討書面糾正性反饋與二語發展關系。第五章在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對書面糾正性反饋研究進行了回顧。第六章作者提出了未來研究的方向。
二、簡評
(一)認知理論視角下的書面糾正性反饋
作者分析了二語學習的中心目標與兩種能力(習得性的能力和學得的能力)以及兩種語言知識(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之間的關系[1]。作者認為二語學習的中心目標就是在理解和使用目標語言的過程中達到或者接近本族語的語言能力,這種語言能力達到的標準就是語言學習者可以在口頭的真實互動中連續、自動、準確、恰當地使用目標語言。
對于這兩種語言能力和語言知識,并不是沒有爭議。一種觀點認為兩種知識處在大腦的不同部位,學得的知識無法轉化為習得的知識。這就是二語習得理論中的無接口立場(non-interface position)。這一立場也為Truscott 所支持。持強接口立場的人認為,顯性知識通過恰當語境下的練習,可以轉化為隱性知識。弱接口立場的人,認為顯性知識可以轉化為隱性知識,但是該轉化在方式與時間上有諸多限制,比如語言中的一些變體形式(如be動詞),通過不斷地強行記憶,可以轉化為隱性知識,最終在使用過程中可以實現無意識地正確使用。但是類似于否定這種結構,其顯性知識轉化為隱性知識則要求學習者剛好處在需要使用這種語言形式階段的時候才能實現。
認知加工理論、顯性知識、陳述性知識的內化理論等都是建立在來自外界的信息輸入基礎上。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存在正面輸入(Positive evidence),也就是目標語中可接受的語言形式、語言結構和負面輸入(negative evidence),即目標語中所不能接受的語言形式,書面糾正性反饋屬于后者。輸入假說認為可理解性的輸入(正面輸入)就足以促進二語的學習,但是互動論學說認為,僅僅接觸正面二語輸入是不夠的,學習者還需要知道哪些輸出不符合二語規范,二語學習者需要能夠在糾正性反饋的幫助下糾正自己的錯誤。互動論學者以基于內容的語言學習環境以及沉浸式的語言環境的學習者為例,他們的語法準確性要遠低于二語的流利性,但是這些學習者如果被提供負面輸入(糾正性反饋),他們的語言準確性則可得到有效提升。
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展開的研究,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一些研究僅僅觀察有限的語言錯誤上的改進;其次,對于一些結論,例如有焦點的(focused)比分散式的(unfocused)書面反饋更有效,缺乏重復性的研究進行跟蹤比較;最后,不同研究中的變量控制不統一而導致研究結論不一致的情況。
(二)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書面糾正性反饋
社會文化理論是建立在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的研究基礎之上,該理論解釋人類的生物學意義上的認知稟賦如何發展演化為獨一無二地相比其他物種的更高層次的人類自身可以掌控的認知能力。其關鍵假設是人類的更高層級的認知發展只能發生在專家和新手之間的互動,這些互動受到諸如物質性的和符號性的媒介諸如電腦、語言、手勢的影響。在所有的符號性媒介中,語言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工具。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發展理論的最大的區別是,它認為認知功能首先出現在人類的社會互動交流中,然后在個體之間內化,該內化并非新手模仿專家的簡單過程,而是新手與專家一起建立知識,該知識被新手加工成為自己獨一無二資源的一個過程。在社會文化理論里,二語習得的影響因素(比如動機、教育環境等)被視作是一個整體體系,而不是一組松散的變量。
社會文化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最近發展區。在最近發展區內提供幫助,該幫助可以讓學習者完成高于自己的能力范圍的任務。該幫助是最低限度、必要的幫助、靈活的(contingent)和動態的(dynamic)幫助。學習者的需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專家需要能洞察學習者對幫助的需求的變化,不斷做出調整:當有信號表明學習者不再需要幫助時,幫助就需要立即退出。當學習者發出需要幫助的信號時,幫助就需要再次進入。需求的變化并不是一個線性的、逐級漸進的過程,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專家所提供的幫助需要最終能幫助學習者不僅完成手頭的任務,更重要的是鼓勵其逐步承擔更大的責任、實現更大的任務目標。這一過程中,學習者獲得自我調節的能力,這是一種自我發展的能力,最終學習者可以不再需要依賴于專家完成任務。專家需要在恰當的時間實施或放棄對學習者的控制。在最近發展區內提供的幫助是無法事先設定的,它是在協商過程中發現的結果,這種幫助被稱為“支架”。
社會文化理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認為媒介在學習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媒介是講個體與社會連接起來的過程,通過實體或者符號象征實現。一切人工制品如計算器、電腦等都是實體媒介,而數學公式、樂譜、語言等都是符號媒介。這些工具是行為發生的條件,可以塑造人們的行為。媒介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媒介的改變也會引發行為的改變,例如尺子被計算器所替代改變了人們進行算術計算的行為方式。社會文化理論中的一個重要理論之一是活動理論,其最初由維果茨基提出,在經過Leontiev和Engestrom的發展以后,逐漸成為完善的理論體系。從活動理論視角看,書面糾正性反饋不再是一個單獨發生的提供幫助的事件,而是一種活動。這個活動發生在一個具體的教育環境里而不是社會真空中。運用活動理論分析和研究書面糾正性反饋會同時關注活動中的個體和社會因素,而不是將微觀和宏觀割裂開看待,因為這些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很難將它們分開。要更好地理解學習者和教師在書面糾正性反饋中的行為,就需要考慮個體與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不僅如此,研究應該采用一種歷時的案例研究設計,因為歷時研究中對多稿的反饋觀察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反饋活動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這些變化包括目標、規則,以及行為規范。
在社會文化理論框架下展開的研究,一些結論的局限性則表現在:首先,一些研究聲稱教師所提供的支架式的書面反饋,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內能比非支架式的反饋更有利于學生的語言學習,然而在互動中合作構建的知識是否被內化,學生在寫作新的文本時能否獨立使用該內化的知識,缺乏相關證據;其次,一些研究主要關注的是一對一的會議形式的反饋;最后,一些研究雖然證明反饋能提升學生的寫作稿件的質量,但是并不能證明學生的二語得到了發展。
三、結語
該書的最顯著的特點是邏輯架構非常清晰,理論綜述深入淺出,實證研究的綜述簡明扼要。各個章節既能相互呼應,也可以獨立成章。其能較為全面系統地從語言習得的理論角度對書面糾正性反饋做了一個綜述性的研究。并且,它也可以作為二語寫作教師的在書面反饋方面的工作手冊,這是它的實用價值。該書將書面糾正性反饋置于主流的兩大語言習得理論框架之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且對近些年的相關研究案例進行了分析。對于從事寫作研究的人員而言,該書為書面糾正性反饋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糾正性反饋多發生在外語或者二語的環境里,二語發展的衡量標準應該可以更有靈活性,外語學習者的語言體系,根據Spolsky(1990)的觀點,是自成一個整體的系統,從語言學習者的視角判讀其語言是否有發展,也許更能體現糾正性反饋的意義和價值。
參考文獻:
[1]岑海兵.基于弱接口說的語法教學[J].嘉興學院學報,2011,23(1):112-116.
(責任編輯:張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