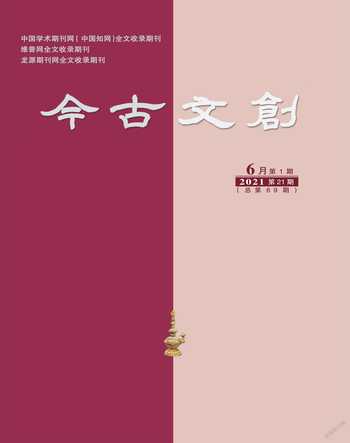《鴿災》中的共同體書寫與身份建構
王馨
【摘要】厄德里克的長篇小說《鴿災》表現出了強烈的共同體意識。通過描寫混血兒埃維利娜的個體成長軌跡和文化困惑,作品表現了印、白兩個民族從對立沖突走向雜居、融合的過程中,印第安人原有的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族裔共同體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印第安人個體面臨著倫理身份困境。為了解決身份危機,以埃維利娜為代表的新生代印第安人不得不選擇回歸或重新建構起新的共同體。本文試將共同體理論同文學倫理學相結合,探討埃維利娜的身份建構問題。
【關鍵詞】《鴿災》;種族融合;族裔共同體;倫理身份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標號】2096-8264(2021)21-0036-04
作為當代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本土裔作家之一,路易絲·厄德里克(Louise Erdrich,1954—)以豐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詩意的表達方式展示了北達科他州奧吉布瓦族保留地幾代印第安人的生活。2008年,厄德里克的第十二部小說《鴿災》(The Plague of Doves)問世,小說沿用厄德里克一貫的寫作模式, 由四個敘述者講述了二十個相互關聯的故事。作者將小說故事發生地設置在北達科他州的普魯托(Pluto)鎮,這是作者虛構的一個區域,靠近奧吉布瓦族保留地。小說以一場私刑事件為原點,圍繞白人和印第安人兩大社群,通過追溯家族史展現種族的沖突、融合和殖民擴張的歷史,講述了三代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間的恩怨情仇。
厄德里克為小說分別設置了一條倫理主線和一條倫理副線——印第安人遭受種族歧視和殖民迫害的歷史是倫理主線,兩個民族不可避免地雜居、通婚與融合是倫理副線。同時,新一代混血兒埃維利娜等人的身份認同過程構成了小說一個重要的倫理結。面對新一代印第安人的倫理身份危機,厄德里克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共同體意識,即通過共同體的建構幫助個體找到自身定位,實現身份認同和療愈創傷。
本文將嘗試借助共同體理論深入剖析《鴿災》中個體與共同體的關系,探索小說的共同體建構和身份建構問題。這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環境,進一步了解厄德里克的共同體意識。
一、族裔共同體建構與族裔身份雛形
共同體概念最早由學者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提出,他將“共同體”定義為“現實的和有機的生命”的一種結合關系,一種“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1]52-53。人們在長期共同的生活中形成了趨同的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具有共同利益,互相幫助,彼此依賴,具有心理認同感和共同的歸屬感。在此基礎上,滕尼斯還特別強調了共同體中精神領袖的作用:“有一種優越的力量,它被用于下屬的福利或者根據下屬的意志實施,因此也為下屬所首肯,我把這種力量稱為威嚴或權威。”這種力量“保護、提攜、領導著他們”[2]64,對共同體形成支持和促進。毫無疑問,《鴿災》中,混血女孩埃維利娜的外祖父穆夏姆在其家族中充當的就是這樣一個“精神領袖”式人物,他以講故事的方式使后代了解本族文化和家族歷史,激發了埃維利娜等人的“民族感”和對族裔共同體的想象,完成了對族裔身份雛形的建構。
在穆夏姆講述的若干故事中,讓人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穆夏姆作為當事者所親歷的那場謀殺——私刑案件。1911年,穆夏姆與三個族人偶然路過一場兇殺案的發生地——一個白人農場。案發現場,一個白人男子和兩個男孩早已喪生,唯有襁褓中的女嬰尚還存活。心生惻隱之情的印第安人們寫信給白人治安官告知嬰兒的幸存。然而,幾個當地白人知曉案件后,不顧印第安人申辯與治安官阻攔,將他們視作兇手并私自施以絞刑,甚至連那個十三歲的印第安男孩也沒有放過。只有穆夏姆因其妻子是現場一位白人施刑者的私生女,才得以逃生。顯然,私刑事件不僅僅是個人與家庭的創傷,亦折射了整個印第安民族在漫長的殖民歷史中所遭受的不公待遇。
主流文化中,印第安人常被進行失真性描寫,被扭曲為愚昧無知的野蠻人,這是為了強化種族偏見,以達到否定他者異質性和整體性的目的。由于對白人的偏見了然于胸,四個印第安人曾為是否要救助孩子發生爭執:“我們一無是處, 我們是印第安人。如果你們告訴白人治安官,我們就死定了。” 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不帶走孩子, 孩子必死無疑;帶走孩子,他們自己將面臨死亡威脅。滕尼斯認為,共同體中的人們依靠本能的習慣和共同的記憶結合在一起,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或活動、有著共同的經歷和信念,人們因為共同的傳統、習慣、信仰和價值觀逐漸形成相同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使社區成員緊緊團結在一起。對于以穆夏姆為首的老一代印第安人來說,除了共有的文化習俗、信仰,人們最一致的記憶和經歷就是那段被種族歧視和被殖民迫害的歷史,這也是族裔共同體構建的核心。共同的創傷和記憶都將老一輩印第安人;連結在一起,休戚與共、守望相助。
家庭是一個“傳承系統”,它不僅傳承血緣,還有文化、家庭故事、家庭關系模式。作為唯一的幸存者,這份傷痛與記憶被穆夏姆傳承與講述下來,后代埃維利娜等人則出于血緣關系與情感共鳴自覺參與到族裔共同體的建構與守護中。共同體的存在對于個體的身份認同無疑有著重要作用。“身份即‘我是誰’的問題需要在具有客觀必然性的倫理關系體系中確證。這些倫理關系體系以倫理實體或者倫理共同體的方式呈現。”[3]1其中,家庭則被視作個體獲得身份認同的起點。“在家庭這一生命共同體中以血緣和倫理性的愛為起點獲得直接的、自然的倫理認同” [4]2。這是因為在血緣關系中,家庭成員之間通過彼此關心而形成了強勁的心靈紐帶。因此,埃維莉娜雖未曾親眼目睹這起給家人帶來身體和精神雙重傷害的私刑事件,但作為受害者的后嗣,私刑事件還是給她帶來了強烈的沖擊,喚起了她的倫理身份意識。這表現在她對家族譜系產生了強烈興趣。埃維利娜將了解到的私刑事件的細節以及與私刑案件相關的人員都記錄在冊,想方設法追溯這些人的血緣史,最終整理出一張家族關系網。作為團體群落的基本單位,家庭的幸福或創傷會延展至更為廣闊的社會語境。私刑事件使埃維利娜深刻地認識到,她的倫理身份不僅與私刑事件連結在一起,更與印第安部族失去土地、遭受偏見和不公的歷史連結在一起。是故,情感共鳴不僅發生在埃維利娜與穆夏姆祖孫之間,亦突破時空限制,在潛移默化中使埃維利娜與整個印第安部族構建了聯系,其族裔身份在對族裔共同體的想象和建構中得以初步確立。
二、共同體瓦解與倫理身份危機
由于身處認知能力尚為有限的幼年時期,埃維利娜對族裔共同體的想象逐漸陷入一種誤區,即簡單地將血緣關系視作族裔共同體的基礎和共同體成員連結的唯一紐帶,這使她迷失在復雜的倫理關系中。在穆夏姆對私刑事件的講述中,白人對印第安人犯下滔天罪行。那么自然,私刑事件的參與者及其后代的交往乃至通婚就成為一種倫理禁忌。這便得以解釋埃維利娜的母親克萊門斯,一個善良溫順的印第安女性,何以對妹妹杰拉爾丁和混血法官安東·巴基爾·庫茨的正常婚戀表示竭力反對。只因庫茨同謀殺案遺孤科迪莉亞——當年唯一存活下來的白人女嬰曾有過一段感情糾葛。然而,埃維利娜在追蹤世系的過程中敏銳地發現,倫理禁忌似乎正逐漸被打破,到了第三代,血緣已經把白人和印第安人兩個沖突的社群緊緊連結在一起 。“保留地上不乏有人同不該糾纏的人陷入感情糾葛”,甚至連埃維利娜本人都不可避免地深陷其中。她先后對同為混血兒的科溫·皮斯和白人修女瑪麗·阿妮塔·巴肯多夫產生情愫。不幸的是,他們恰巧都是仇人的后代,他們的祖父都是當年私刑事件的直接參與者。部族的恩怨、情感的困惑構成一股合力,將埃維利娜置于倫理兩難的境地,預示著埃維利娜想象中的以血緣為基礎的族裔共同體終將走向瓦解的結局。
厄德里克為小說設置的倫理副線是兩個民族隨著殖民進程的深入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融合。眾所周知,美國的迅速崛起得益于西部的開發;而西部開發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土地所有權。印第安人本是這片土地的最早居民,但由于一直未能形成有效占有和開發土地并確認其主權的制度,這就給白人的侵占留下了可趁之機。1830年,美國政府實行遷移政策,迫使大批印第安人離開了祖居地遷往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區。1887年推行的《道斯法案》,表面上是聯邦政府對印第安保留地實行土地托管,實質是剝奪他們對土地的支配權。[5]這段殖民歷史在《鴿災》中得到了影射,在《城鎮狂熱》和《普路托郵票的災難》兩個故事中,厄德里克以白人的視角詳述普路托的建鎮始末,揭示了美國城市化的本質即蠶食印第安人的土地。可以說, 普路托小鎮的歷史就是美國社會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但不能忽視的是,殖民化進程亦伴隨著種族融合,至20世紀60年代,普路托小鎮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已被三座城市包圍,印第安人后代、歐洲拓荒者和混血印第安人共同生活在該地。白人的入侵和兩個民族的長期雜居打破了印第安傳統的家庭結構,使原先單一的婚姻狀態開始變得復雜:白人與印第安土著居民開始通婚,保留地附近逐漸形成了一個由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組成的種族緩沖地帶。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間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也隨之被打破。“在這樣一個‘邊界空間’中,不同身份相互融合、對峙及影響,使得人物文化與社會身份發生變化。”[6]
厄德里克在小說中著力描寫異族婚戀及其對人的倫理身份的影響,比如庫茨的爺爺和父親,他們都娶了奧吉布瓦族的女人。對此,庫茨有句意味深長的點評:“這樣的雙重身份在當時還是件新鮮事。”從先輩與白人發生沖突,到晚輩渴望融入白人社會,埃維利娜亦擁有相悖的倫理身份。她是私刑事件受害者后人,是承載著苦難歷史的印第安人后代;同時,她又是在一個“大熔爐”中成長起來的新一代歐美混血兒,不可避免地受到白人文化影響。她喜歡加繆,夢想去巴黎讀書,甚至想做個法國人。顯然,在種族融合的背景下,族裔共同體難以僅僅依靠血緣關系與地緣關系來維系。隨著種族融合的進程不斷加深,埃維利娜在幼年時期所想象和建構的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族裔共同體逐漸暴露出其無為性和不穩定性,進而走向瓦解。共同體為個體成長提供歸屬感和精神家園。伴隨著舊有的共同體瓦解,埃維利娜的生理安全感和身份認同感也失去保障。在復雜的倫理環境中,如果人物不能準確定位自己的倫理身份,很容易使自己遭遇倫理困境并深陷其中。正因如此,她迫切地希望參與一個新共同體以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高中畢業后,埃維莉娜只身來到北達科他州大學接受教育,在地緣關系上暫時脫離了承載著歷史和傷痛記憶的土地。入校初期,埃維莉娜就意識到自己與其他女孩的不同。與白人女孩的生活方式相比,她的生活習慣被貼上了怪癖的標簽。在母親的影響下,埃維莉娜從小就習慣把周圍所有的物品都整理得井然有序,但她的舍友卻是一群不愛打掃衛生的“嬉皮士”。埃維利娜曾嘗試通過模仿來融入主流文化,卻以失敗告終。
“個人從屬于共同體,需要通過分享共同體倫理精神確證自我身份的倫理合理性且確定主體精神。”[7]顯然,埃維利娜“沒法融入這種時代精神”。如果說埃維利娜遭遇的第一次倫理身份危機來源于族裔共同體的瓦解,那么第二次則是來自主流社會完全的漠視。埃維莉娜中斷了與印第安傳統文化的聯系,又無法融入主流文化的時代精神,她深深感受到被邊緣化的痛苦。她不斷追問自己,自己究竟是誰。她“慢慢意識到集體不再作為一個有效的支持來源而存在,而與之相連的自我重要的一部分已經消失了” [8]。甚至于,她通過吸食毒品、尋找同性戀人來放縱自己的困惑。
三、精神溝通的搭建:走出倫理困境
同很多年輕的印第安人一樣,埃維莉娜曾在白人社會中迷失身份,她渴望融入一個新的共同體,從而構建起新的文化身份,但她的膚色,她的生活習慣卻使她成為白人凝視下的“他者”。埃維利娜的敘述展現了她作為新一代混血兒在身份建構中的困境。第一人稱拉近了讀者和作者的距離,使讀者感同身受,由此深切地感知到歷史文化沖突中個人的困惑和絕望。回歸部族,重構族裔身份成了埃維利娜身處困境中的唯一選擇。
回到普路托小鎮后,埃維莉娜在穆夏姆的帶領下,重返當年私刑事件的發生地。只有在部族的土地上,印第安人“才能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認識自我,才能為自己界定出一種地方感,一種歸屬”[9]。走在這塊充滿著痛苦回憶的土地上,埃維莉娜在想象中再次重溫了印第安族人遭受迫害的經歷。站在那棵用來施以絞刑的大樹面前,她將那個十三歲男孩穿過的靴子扔了上去,以示緬懷。通過再次回憶穆夏姆等人當時經歷的私刑事件,她開始意識到,生理上的血脈傳承和空間上的接近,只是個體聯結的一種表層方式,共同的價值取向、共通的記憶和情感才是真正將族裔共同體中的個體聯絡起來的紐帶。換言之,只有當個體之間達到精神層面的契合才能維系共同體的穩定性。于是,她自覺承擔起自己族裔身份的使命,成為這段苦難歷史的新一代的言說者,她將這段家族歷史講述出來,讓更多受眾了解整個部族的苦難歷史和當代印第安人的真實生活,從而加強他們與部族歷史的精神聯系。在對印第安族人受到的身體和精神創傷產生了情感的共鳴的同時,埃維利娜重新建立起與部族歷史的精神聯系,其族裔身份也得到重構。
然而,如前文所述,血緣關系的混亂是族裔共同體的瓦解的起點,亦是埃維利娜陷入困惑的起因。因此,如何面對罪人和受害者雙方后裔紛雜纏繞的關系,不可避免地交往乃至通婚亦是埃維利娜走出倫理困境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在醫院休養的日子里,埃維利娜試圖再次理順白人后代和印第安人后代的關系:“我還想到歷史是怎樣自動交匯的:巴肯多夫一家、懷爾德斯特蘭德一家,皮斯一家,這些人都因為一場絞刑糾纏到了一起。”然而他們之間的關系如錯綜滲透的枝蔓,實難殊難厘清出處或交集。恍惚中,她決定重回普魯托小鎮拜訪巴肯多夫修女。在與修女的交談中,她突然意識到,白人的后代也承擔著不可言說的傷痛。巴肯多夫修女的曾祖父是私刑事件的參與者之一。從父親口中,她了解到曾祖父是一個極其溫和的人。著實難以想象,溫和與暴戾一體兩面,竟如此共存于同一個人身上,這讓巴肯多夫修女和她的父親始終難以接受。因此,盡管如修女本人所說,自己并非十分“虔誠”,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選擇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神。只有如此,方能以善行化解上輩人的恩怨糾葛,方能將祖先遺留在她身上的污點和罪惡洗刷至凈,進而重獲內心的平靜。
“就共同體形成的基礎而言,共同體從不單純意味著‘共同的生活’,而是意味著在共同的生活中已經形成一種特定的倫理關系和共同的價值取向。” [10]作家不僅在新一代印第安個體與部族歷史之間重新建構聯系,亦在兩個民族之間搭架了一座精神橋梁。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在埃維利娜所處的那個時代里,種族間的流血和沖突已過去許久。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與白人和平共處,他們可以戀愛通婚,可以結為莫逆,他們對相同歷史事件進行不同角度的反思,他們甚至有著共同的歷史創傷。受害者與罪人之間再也沒有涇渭分明的界線。“受害者和施刑者后代的通婚, 將兩個社群的生活緊緊相連, 彼此已無法互相指責”[11]。直到此時,讀者才終于領會到,這些錯綜復雜、難以梳理的關系本就是作家有意為之的設計。“我們中的一些人身上既流淌著罪人的血液,也流淌著受害人的血液。這其中的關系剪不斷,理還亂”[12]。區分和梳理失去了必要性,仇恨和追溯也在融合中褪去,埃維莉娜作為受害者的后代,與罪人的后代真正地達成了和解,這終于使埃維利娜走出了混亂的血緣關系的漩渦,不再糾結于此。寬恕、和解,這是在痛苦的掙扎和困惑后才能企及的精神高度,亦是治愈創傷的“愛藥”。
四、結語
解讀《鴿災》中的共同體書寫是理解該作品的一個新角度。正如學者殷企平所言,“大凡優秀的文學家和批評家,都有一種’共同體沖動’,即憧憬未來的美好社會,一種超越親緣和地域的、有機生成的、具有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體形式。” [13]厄德里克在作品中首先肯定了族裔共同體的積極意義:印第安族人因共同的歷史回憶種族文化、和身份認同而緊密聯系在一起。族裔共同體使族人找到生存和發展的力量,印第安文化和歷史記憶因共同體得以保持和傳承。同時,厄德里克在參加訪談時也曾明確指出,她拒絕被定義為族裔作家,并以為全人類寫作為追求。因此,她并不局限展示在族裔文化與主流文明之間的矛盾,而是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意在揭示更高層次的普遍人性。與之相呼應,在《鴿災》中,她將既有強烈的情感聯系,又有彼此的差異和傷害的兩個民族共同安置在普魯托鎮這片虛構的土地上,揭示了差異和矛盾之上的精神追尋和力量。
參考文獻:
[1][2](德)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M].林榮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52-64.
[3][4][7]竇立春.身份的倫理認同[D].東南大學,2016:1-69.
[5]李劍鳴.美國印第安人保留地制度的形成與作用 [J].歷史研究,1993,02:159-174.
[6]尚廣輝.猶太存在危機:論《太警察工會》的非自然空間[J].當代外國文學,2019,02:25.
[8]Erikson, Kai. “Notes on Trauma and Community.”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Ed. Cathy Caruth.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P, 1995:127.
[9]陳召娟,鄒惠玲.論《鴿災》中的族裔身份重構[J].名作欣賞,2016,(17):91.
[10]王露璐.共同體: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及其倫理意蘊[J].倫理學研究,2014,(06):79.
[11]黎會華.暴力·愛情·歷史——評厄德里克的小說《鴿災》[J].外國文學動態,2010,(03):31.
[12](美)路易絲·厄德里克.鴿災[M].張廷佺,鄒歡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7:251.
[13]殷企平.西方文論關鍵詞:共同體[J].外國文學,2016,(0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