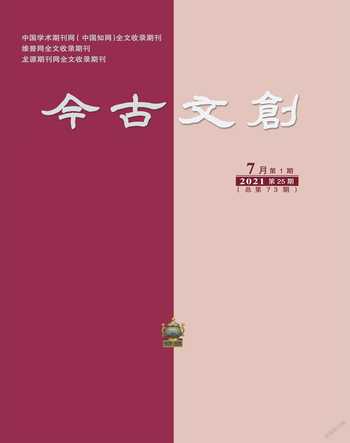淺談《叔于田》及《大叔于田》的解讀可能及其邊界
【摘要】 《叔于田》及《大叔于田》兩詩收錄于《詩經·鄭風》,其內容的關聯性與詩旨的多重解讀可能使其獲得廣泛關注。但與此同時,重義輕文,以及詩旨雜糅難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對于這兩首詩的解讀,目前以認為“叔”即鄭莊公之弟共叔段為前提的“刺莊公說”影響最大。而回歸詩作本身,結合《鄭風》的藝術特點,賞析評價兩首詩藝術手法、思想內涵的異同,并結合對闡釋有效性的探討,從文本出發進行詩旨重估,能發現作為愛情詩的《叔于田》及《大叔于田》。
【關鍵詞】 《叔于田》;《大叔于田》;詩歌主旨;闡釋有效性;鄭聲淫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25-0020-02
一、歷史反復的偏見
《鄭風》為《詩經》十五國風之一,其收錄的是先秦時代鄭地民歌。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提出了“鄭聲淫”的主張。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殆”,可見孔子對“鄭聲”思想內核“淫”的批判態度。春秋時期已有將新興的樂音稱為“鄭衛之音”的說法。后朱熹為支持自己的理學體系,更是在《詩集傳》中指出“《鄭》《衛》之樂,皆為淫聲”。
然而,在古代詩樂一體的文化形態下,正是鄭地樂音婉轉優柔的性質影響著對于《詩經·鄭風》中詩歌特質的判斷。楊慎有言:“聲過于樂為淫聲”,一則警示著“淫聲”一詞作為偏正性主體,“淫”對于“聲”而非“風”的修飾關系;二則對當代偏重于取“奸淫”義而忽略“浸淫”本意的語法情況造成的古今疏離有警示作用。并且,《鄭風》中絕大部分是情詩,這與鄭國地理位置地處中原、與京畿臨近、文化形態活潑、人民感情激越緊密相關,詩經中如《子衿》《溱洧》等流傳度較高的情詩皆源于《鄭風》。這更加劇了因“淫”字的誤解而在“鄭聲淫”與“鄭風淫”之間產生的混淆。
孔子以“鄭聲”代“鄭衛之音”稱呼諸侯分封地新產生的樂音,批評新樂音對傳統雅樂的沖擊,這與孔子本人“移風易俗”的治樂觀及重整禮樂的政治理念極為符合。然而自此之后,對鄭地音樂“鄭聲淫”的批判逐漸轉為了對《詩經·鄭風》“鄭風淫”的批評,朱熹在《詩集傳》中更是在為《鄭》《衛》之樂扣上“淫聲”的帽子后,指出:“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1]這便從對于“鄭聲”的批判轉而為對于“鄭風”的討論了。這樣的批判與其“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主張不謀而合,但是朱熹這種“以《詩》考之”的研究態度,顯然是擴大了孔子對鄭聲的批判,利用了“淫”的引申義,無形中分割了詩樂的關聯性與交互性,形成了對于“鄭風淫”的偏見。
然而,即便朱熹對《鄭風》持批判的態度,而《叔于田》一詩也因其詩旨不明,讓他表現得相當猶豫,“斷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故作此詩……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說之詞也”。這截然不同的詩旨猜測在根本類屬上分割了本詩可能存在的政治性傾向與愛情詩傾向,對后世評《叔于田》的主流態度產生了兩極分化的影響。
由此可見,“鄭風淫”的見解是在歷史反復的偏見中逐漸成形并鞏固的。因此,梳理“鄭風淫”的歷史形成既有助于整體把握占據釋經話語權的儒家對于《鄭風》的整體定位,從而切入對《叔于田》及《大叔于田》的實際分析;又能彰顯作為《鄭風》第三首詩的《叔于田》其釋詩的復雜性,因而跳脫出潛意識中對于傳統觀點的迫近,從文本出發,辨明詩旨。
二、文本語言的回歸
學界目前對《叔于田》及《大叔于田》的詩旨研究分歧主要在于其言政治或寫愛情的基本屬性,即:作為政治詩的《叔于田》還是作為男女相悅之詞的《叔于田》。政治詩觀點下又以“刺莊公說”及“美段說”為主流。
即便文本闡釋從古典時期到現代分別經歷了以作者為核心,以語言為核心和以讀者為核心的不同歷史階段,但文本語言本身提供的信息卻是任何一種闡釋觀點都無法拋棄的。因此就詩論詩,考察背景,解剖文本,能夠排除詩論的影響,得到富有實證性的結論。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2]
《大叔于田》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雁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3]
縱觀《叔于田》全詩,以“賦”的手法鋪陳開來,側面描寫“叔”外出打獵時旁觀者的心理狀態。通篇采用設問和夸張的手法,在一問一答之間生動地傳達了女子嬌羞又熱切的愛慕之情。這里敘述者的自我心理剖析生動傳神,顯然是女子唯傾慕“叔”一人的近乎偏執的情感抒發。
然而,《毛序》評《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4]這是延續了《左傳》記史《鄭伯克段于鄢》一章的說法。因為“血統純正”,這一說法得到廣泛的認可。朱熹《詩集傳》中也明顯受到了這一觀點的影響。如果接受這一說法,即默認“叔”即鄭莊公之弟共叔段,而作詩的本意也是為了通過對共叔段英武形象的描寫,宣揚共叔段功績,諷刺莊公不教而虐的寡德。
崔述在《讀風偶識》中指出:“大抵毛詩專事附會,乃稱叔即以為共叔,情勢之合與否皆不復問。”誠然,《詩經》中女子稱男子伯仲叔季的表字極為常見,如《鄭風·萚兮》有“叔兮伯兮,倡予和女”之句。故毛詩此注,似有牽強附會之嫌。而且,如果從這種觀點出發,甚至可以揣度,此詩會否是共叔段反叛前夕為宣揚自己功績而進行的偽作?這些觀點目前顯然是無法考證的。朱熹稱:“或疑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也”,此觀點做到了從文本出發,客觀表述詩句中呼之欲出的女子的愛戀追求。因此,綜合以叔為共叔段的前提受到質疑,以及原詩明顯的“增其美”修辭及抒情性兩點,將其視為政治詩顯然是不可靠的。
《大叔于田》一詩在《詩經·鄭風》中位于《叔于田》之后,后世學者以聯系的眼光認為兩詩可能出于同一母題。而根據當代普遍認同的觀點,《詩經》中題目大多為編書者所加,因此會否是獻詩、采詩時恰巧選錄入兩首鄭地狀獵手出列的民歌,亦未可知。在寫作技法上,《大叔于田》一詩也運用了賦的手法,但更多地側重正面地寫實,與《叔于田》聚焦于女子內心描寫不同,《大叔于田》的敘述焦點始終在于“叔”,因此對于他打獵時的動作描寫刻畫得細致入微,從正面直接描寫了他英武的人物形象。
《毛序·大叔于田》言:“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此思路顯然與《叔于田》的詩序相通,且“獻于公所”暗示的“叔”的貴族身份,這更助長了“刺莊公”說的流行。然而,《鄭風》二十一篇中描寫愛情的詩歌占據多數,其本身就有書寫男女之間情愛的傳統,在《大叔于田》文本中,更是對“叔”本身英武形象的描寫居多,因此將“叔”理解為一獵手的形象頗有理據。且鄭地有虎牢天險,春秋戰事之多者莫如鄭,這更為民歌中歌頌精壯勇猛的男性形象提供了客觀佐證。上文對于兩首詩是否出自同一母題的存疑同樣表明,仍不能肯定兩首詩的詩旨皆為“刺莊公”的同一性。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鄭地活躍的文化背景下,催生出許多表達男女情愛的清麗自然的詩歌,《大叔于田》不過是其中之一的猜測,卻是可以被接受的。
三、有效闡釋的邊界
當代學者楊帆在《〈鄭風·大叔于田〉詩旨辯證》中綜合大量中外學者論據,歸類得出十二種觀點,著重分析了“刺莊公說”及與之一脈的“愛段說”,以愛情詩說為最后一種。[5]《詩經》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詩作途徑多元,年代久遠,其詩作創作本意難以考證,因此當代讀者往往廣泛收集歷代評論者的詩序及詩評,并進行再組合,形成自己的觀點。因此易造成對文本的忽視及再忽視。然而,正如前文所言,在歷史反復的誤解中,在忽視文本尋章摘句的研究模式下,原詩所提供的鮮明的信息及鮮明的詩歌背景往往被疏忽。伽達默爾指出,“本文的意義超越它的作者,這并不是暫時的,而是永遠如此的。因此,理解不只是一種復制行為,而始終是一種創造性的行為。”[6]誠然,當一部文學作品呈現在讀者眼前,作者本身也已經喪失了對它的完全解釋權,而讀者的闡釋作為主體性的伸張,往往因個體差異產生分歧并引發創造性過剩導致的混亂。艾柯指出“在最近幾十年文學研究發展進程中,詮釋者的權利被強調得有點過火了。對于文學作品的開放性閱讀必須從作品文本出發,因此,它會受到文本的制約。”[7]正是清晰地勾勒了當代開放性文本闡釋的有效邊界,即文本自身。因此,回歸文本,就詩論詩,在保證闡釋有效性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叔于田》及《大叔于田》作為《詩經·鄭風》中兩首藝術水平高超的愛情詩的結論。從詩旨出發,聯系詩歌背景,回歸詩歌文本,正如“戴著鐐銬舞蹈”,能夠為新時代評詩論詩明確邊界,尋回傳統的卻易被忽視的研究角度。
參考文獻:
[1]田宇昕.“鄭聲淫”考論[J].文化學刊,2020(10):
205-208.
[2][3]毛亨傳,鄭玄箋,陸德明音義.毛詩傳箋[M].北京:中華書局,2018:108-109.
[4]王亮亮. 《叔于田》與《大叔于田》之叔非段考辨[J].鄭州師范教育,2020,9(03):40-43.
[5]楊帆.《鄭風·大叔于田》詩旨辨正[J].名作欣賞,2020(29):32-37.
[6][7]張良叢,唐東霞.闡釋的邊界:文本闡釋的有效性問題探析[J].江漢論壇,2017(05):61-66.
作者簡介:
郭晉瑋,男,漢族,山東濟南人,天津師范大學,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