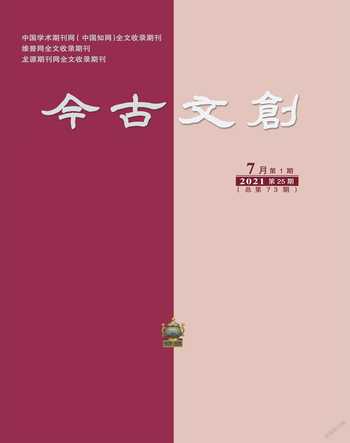當前中國人類學的任務: 回歸學科本體
任振一 陳朋
【摘要】 20世紀以來,人類學在救亡圖存思潮下傳入中國,并于抗戰時期達到第一個高峰。近年來,中國人類學界要求學科本土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人類學在中國的第二個高峰即將到來,但它仍然存在發展困境。重視全球視野下的跨學科合作與跨文化比較,以使中國人類學回歸學科本體,走出學科發展困境。
【關鍵詞】 中國人類學;本土化;學科本體;跨學科合作;跨文化比較
【中圖分類號】Q98-0?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25-0046-02
基金項目:中南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項目編號:3212020sycxjj251)。
一、中國人類學發展簡史
1888年的“托雷斯海峽之行”開創了人類學社區研究的先河,為現代人類學的誕生埋下伏筆。此外跨學科合作在本次調查中初露鋒芒,與古典人類學家的閉門造車不同,跨學科合作是現代人類學發端時期的典型標志之一,它也是人類學學科的重要特點。
20世紀以來,人類學東漸傳入中國。20世紀30年代,拉德克里夫-布朗和派克曾受邀來華講學,使得吳文藻加大了對社區研究方法的引介。后來經過費孝通、林耀華等學者的發揚,社區研究方法開始廣泛用于中國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社區研究是人類學研究的外在表現,而非人類學研究的本質。無論是托雷斯海峽之行,抑或功能學派的田野調查,在社區中獲取地方性知識與在社區中進行田野調查均不是人類學研究的本質,人類學研究的本質是跨文化比較,亦即從他者回到自身。
抗戰時期,由于中國國土的大面積淪陷,學者們難以進行宏觀研究,而只能進行邊疆社區的微觀研究。他們對中國西部進行大量民族、社會、歷史等方面的調查。期間,中國人類學研究達到第一個高峰。傳統的社區研究開始轉入類型比較階段,如費孝通的《云南三村》,通過選取幾個典型個案進行比較研究,得出較普遍的結論,從而認識中國社會。在此提到的類型比較研究已具有明顯的跨文化比較研究的性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專家學者組成的中央訪問團進行了全國范圍的民族識別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這批調查在跨學科合作方面表現突出。
社區研究方法在中國人類學界的廣泛應用,與現代人類學誕生之初便關注小規模社會的取向密不可分。從社區研究方法來看,似乎人類學僅僅進行微觀研究,但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社區,目的是與本文化進行比較,宏觀或微觀僅僅是形式。
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人類學被民族學取代,而后其經歷了60-70年代的沖擊。20世紀80年代,人類學迎來復興,但其學科地位尚不明確。此時,以費孝通對城鎮化模式的研究為代表,社區研究方法由小范圍的類型比較研究擴大至區域性的跨文化比較研究。
學科恢復重建以來,新近研究匱乏的同時,中國人類學遭遇后現代,學科的未來一度不甚明晰。帶著強烈的人文關懷,中國人類學加快了本土化進程。近年來,人類學本土化的呼聲越來越高,將人類學發展為一級學科的訴求也層出不窮,人類學在中國的第二個高峰正在到來。一些中國人類學者建議未來中國人類學重點關注三個領域:農村漢族的鄉土人類學;少數民族研究的民族學;海外社會研究[1],這些研究均需要跨學科合作與跨文化比較。
二、中國人類學的本土化困境及其根源
費孝通、林耀華、陶云逵、楊成志、林惠祥、凌純聲等先驅篳路藍縷,開辟了中國人類學本土化道路。但是中國人類學命運坎坷,直到1980年之后,在費孝通、陳國強等人的努力下,幾近夭折的人類學才又獲得了新生……本土化是混雜的語言,擁有豐富的層次,在本土學者的身份訴求中,至少包括以下五種回應:
第一,援引西方現代人類學的本土化趨勢。第二,海外人類學的研究。第三,區域文化的研究風氣正在形成。第四,西方作為對話者是學習還是抵抗,本土化尚且包含了接納西方的態度……第五,費孝通在晚年提出心態的概念,它從史祿國的“Psycho-mental complex”、潘光旦的位育思想受到啟發,超越生物和需求的層面,關注人的精神世界,反思功能學派[2]。本土化的面向與成就的背后既有幾代學者前仆后繼的努力,又有難以逃離的困境。
這一困境的主要表現:由于中國人類學的立身之本不明確,致使中國人類學的學科規范沒有很好地建立,可謂“先天不足,后天畸形”。
中國人類學的困境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怎么研究,這是中國人類學的立身之本。追求地方性知識以及田野調查是回答“怎么研究”這一問題的部分答案。雖然追求地方性知識是在進行研究對象的創新,但是這將使得中國人類學的知識越來越碎片化;同時若忽略地方性知識又會錯過豐富多彩的研究內容;而通過田野調查來獲取資料的方式也非人類學所獨有,其他學科借助田野調查甚至可以獲取比人類學更完備的知識。可見地方性知識和田野調查并不能成為中國人類學本土化的主力。中國人類學確實需要一種結合地方性知識與田野調查的取向,不過這種取向應該有更普遍的關注,而不能僅僅停留在偏重地方性知識和田野調查這些特殊性的層面。
“怎么研究”這一問題是中國人類學本土化困境背后的根源。回歸學科本體,是中國人類學走出本土化困境的鑰匙。
三、中國人類學需要回歸學科本體
(一)學科本體中的兩個要素
早期中國的人類學前輩基本都在多個文化差異性大的地區做過調查,同時他們在研究中進行跨學科合作,亦即他們將跨文化比較與跨學科合作結合,從而提煉出經典理論。任何一個學科理論都要有普遍的解釋力,發展中國人類學必須回歸學科本體中利于進行理論綜合的要素,即跨學科合作和跨文化比較。
跨學科合作在大型研究中運用較多。例如區域研究,即在一定地理區域內綜合多個文化因素進行的人類學研究。此外,人類學對于復雜課題的研究也需要團結多個學科的力量。例如,人類學在未來對鄉村社會的研究單憑借鄉村人類學這一分支學科的力量是無法進行的,需要借鑒、吸取民族學、社會學、生態學、政治學、地理學、旅游學、風景園林學等其他相近或交叉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3]。在研究對象日益復雜化的今天,跨學科合作這一學科本體要素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
跨文化比較是人類學研究的本質。通過抗戰前后的中國人類學研究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規律,中國人類學研究總體而言是由本文化走向異文化,進而走向跨文化比較。這與西方人類學先研究異文化再走向本文化,最后進行跨文化比較的路徑殊途同歸。
縱觀人類學的發展史,無論是剝削他者的殖民活動(歧視他者),還是為反思自身而對他者世界的探索(仰視他者)以及為改造社會而對人類普同性的尋找(平視他者),都是在進行跨文化比較。可見,跨文化比較始終是人類學研究的本質。
自費孝通2005年辭世之后,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界似乎進入了一個沒有大師引領的時代……因理論創新不足,這些年幾乎沒有出現任何重要的學術突破[4]。這使我們不得不反思其中的原因,與其說問題出在努力上,不如說問題的根源是方向不對。
中國人類學本土研究的傳統不是對人類學一貫傳統的背離,而是人類學學科具有較強生命力和適應力的體現……構建全球化時代中國人類學的學科話語體系,擺脫西方人類學話語束縛,爭取國際學術舞臺中國人類學的話語權,這是當前中國人類學海外研究視域延伸的深層緣由[5],海外研究的興盛為理論創造提供了條件,這是因為將中外進行跨文化比較能得出新的觀點。跨文化比較是學科創新的切入點,中國人類學要想走出本土化困境必須回歸跨文化比較這一學科本體要素。
(二)中國人類學回歸學科本體的前景展望
全球化開始以前,人類學尚未產生。全球化使得多種文化交流與碰撞,人類學就是這一交流過程的重要先行者。跨學科合作與跨文化比較在人類學產生之際就已經顯現,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類學應當做的是對二者的回歸。
長期以來,對于西方人類學家來說,中國主要作為研究對象而存在……中國人類學希冀達到的是,“中國”從作為研究對象的“異邦”,成為人類學知識生產的主體,最終實現從中國自身的傳統思想脈絡中挖掘和發展人類學知識,從而對普遍人類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有所貢獻[6],中國若要成為人類學知識生產的主體,必須建立起學科規范,回答中國人類學“怎么研究”這一問題。中國人類學回歸學科本體,重視跨學科合作和跨文化比較,這將利于學術規范的建立和學科力量的集中,最終為中國創造人類學理論提供可能。
參考文獻:
[1]陳剛.改革開放40年以來中國人類學發展現狀及未來[J].百色學院學報,2019,32(02).
[2]參見馬丹丹.1995年:中國人類學的一個“拐點”[J].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05).
[3]曹晗.鄉村振興與中國人類學研究的新議題[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41(05).
[4]張繼焦.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范式的轉變:從“差序格局”到“社會結構轉型”[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3(03).
[5]楊文筆.從“本土”到“海外” ——中國人類學研究的傳統視域與時代延伸[J].廣西民族研究,2018,(06).
[6]黃劍波,李靜.如何發展中國人類學的知識體系——以少數民族研究為例[J].文化縱橫,2018,(05).
作者簡介:
任振一,男,漢族,山東安丘人,碩士生,中南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研究方向:社會人類學。
陳朋,男,漢族,安徽阜陽人,碩士生,浙江師范大學法政學院,研究方向:移民社會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