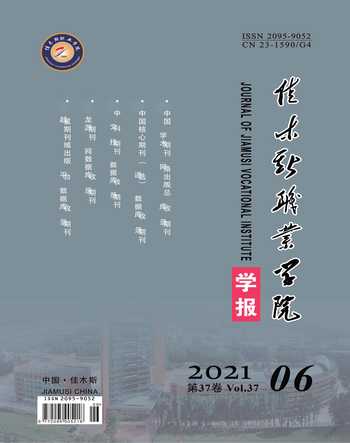《全隋文補遺》錄文校補若干則
摘 ?要:韓理洲先生整理、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全隋文補遺》一書,輯錄了《全隋文》沒有收錄的七百五十篇散文,為學者研究隋代歷史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是通過碑刻拓片收錄的墓志中存在很多俗字的情況,在釋讀上可能出現一些問題,故本文在原拓片的基礎上,運用文字學、詞匯學和歷史學的一些知識,對錄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進行討論。
關鍵詞:《全隋文補遺》;俗字;校勘
中圖分類號:H1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9052(2021)06-00-02
隋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極具典型意義的朝代,它結束了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面,實現了統一,雖然強盛而又短命,但是對后來的唐代政治制度具有深遠影響。因此對隋文華的研究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的重要環節。韓理洲先生整理的《全隋文補遺》(以下簡稱《補遺》)對這種研究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當時隸書和楷書間行,加上隋朝是由亂到治的王朝,各地文化的碰撞造成了碑刻文獻釋讀的困難,難免出現不妥之處。本文通過考證,對墓志錄文中出現的問題分條校補如下。
一、典故未識
墓志志文中尤其是銘文,會使用大量的典故和固定詞語搭配,如果沒有識別出來,就會造成釋讀的錯誤。
(一)《茹洪志》:“配巾出宰,分竹共治理。”
《補遺》錄作“巾”,誤,應為“印”。《說文解字注》:“印,執政所持信也。從爪從卪。”“配印”意為做官,如蘇秦曾配六國相印。后文“出宰”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由京官外出任縣官,《后漢書.卷二·顯宗孝明帝紀》:‘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1]。’”這里是指墓主人被皇帝從京城派去外地做官,故此應為“印”。
(二)《李和志》:“入司猑虎,出總禽熊。”
《補遺》分別錄作“猑虎”“禽熊”,不詞,應為“貔虎”“螭熊”。貔虎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貔和虎,亦泛指猛獸,比喻勇猛的將士,出自《尚書》[1]。”杜甫《觀兵》詩:“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熊螭”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均為猛獸名。用以喻豪杰[2]。”本句旨在說明墓主人統領著一批驍勇善戰的將士。“豸”在俗寫中多寫作“犭”,如《大魏征東大將軍大宗正卿洛州刺史樂安王(元緒)墓志銘》:“豺”[2],《處士房周陁墓志》:“情高志潔,心直貌溫”[2]。故“貔”在俗寫中有時會簡寫作“猑”。
“螭”在俗寫中有“蠄”的寫法,《正字通》:“蠄,螭之偽字[3]。”《龍龕手鏡》:“蠄,俗[4]。”《金石文字辨異》寫作“蠄”。《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蠄”[5]。故而此處應為“貔”“螭”。
(三)《李和志》:“蹈顏舟而為儔,躡韓彭而可輩,孝有絕人,誠亮有本。”
《補遺》錄作“舟”,誤,應為“冉”。經查黃征《敦煌俗字典》“冉”有 ? ?的寫法[3]。《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為‘冉’之增繁異體字。碑刻中從‘冉’之字多如此。[6]”志文中本句是駢文,上句的“顏”“冉”指的是孔子的學生顏回、冉耕,二人都以德行著稱。孟堅《幽通賦》:“聿中和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唐·李善注引曹大家曰:“聿,惟也。顏,顏淵也。冉,冉伯牛也。二子居中履和,庶幾圣賢。然淵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下句的“韓”“彭”指的是韓信、彭越。《文選·李陵》:“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李善注引《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本句是贊美墓主人德行比肩顏回、冉耕,謀略媲美韓信、彭越。故該字應為:“冉”。
(四)《李和志》:“七札可穿,嘗云未兼;五行俱瞻,終夜忘疲。”
《補遺》錄作“未兼”,不詞,應為“末藝”。《漢語大詞典》:“微不足道的技藝。《儒林外史·第一六回》:‘士先器識而后辭章,果然內行克敦,文辭都是末藝。’亦作末技。[6]”這里是指墓主人能穿上七層鎧甲,但是跟別人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技藝,表示墓主人能文能武并且很謙虛。故此應為“末藝”。
(五)《寇遵考志》:“揚鳥豫玄,雖聞前史;黃童辯日,當時獨步。”
《補遺》錄作“鳥”,誤,應為“烏”。“揚烏”是西漢蜀郡成都人,楊雄次子,被稱為神通。錢謙益《桂殤》:“七歲已看過頂蠹,九齡那得到揚烏。”本句指的是揚烏九歲時幫助父親楊雄創作《太玄》的典故。下句“黃童辯日”說的是《論語》中孔子見兩小兒辯日的典故,都是在夸贊墓主人幼年的天才。從字形上看,原刻中“鳥”右上角有三橫,而“鳥”的俗寫一邊是四橫,故應為“烏”。
二、形近而誤
漢字字形比較復雜,加上碑刻文獻年代久遠,難免發生字跡的漫漶,多種情況都有可能造成釋讀的錯誤。
(一)《茹洪志》:“昔數合聲和,伐水德木,以宣母弟建桓于鄭,公子之孫,禮氏王父,藏志脫禑,因加草為茹族焉。”
《補遺》錄為“伐”,誤,應為“代”。上文“數合聲和”出自國語“凡人神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后可同也。”是以樂理喻指政治,說明政事的處理應和音樂一樣和諧。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鄒衍提出了五德始終說。“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種德性。“終始”指“五德”周而復始的循環運轉。鄒衍常常以這個學說來為歷史變遷、皇朝興衰作解釋[7]。古代統治者建國后為本國賦予了五行屬性,希望通過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為朝代更替尋找合乎倫理的原因。本句中的“水”和“木”就是這個意思。《說文解字注》:“?也。從人,弋聲。”本句志文意為墓主人的祖先對政治治理有方,所以取代了之前的統治者,成為新的諸侯,并且得到“茹”字作為姓氏。所以此處應為“代”。
(二)《茹洪志》:“公行唯德柄,言成禮則,和羹善碟,每平其心,遂便應詔,舉之上府,授梁州總管士曹,又除白云縣令。”
《補遺》錄為:“碟”,誤,應為“渫”。《說文解字注》:“除去也。從水枼聲。荀爽曰:‘渫去穢濁。’清潔之意也。”本句“和羹”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比喻良臣賢相輔佐國君處理朝政[1]。”與“善渫”連起來意為墓主人善于處理朝政,為國君分憂解難。故此處應為“渫”。
(三)《梁邕志》:“從容華闥,徐步禁闈,吹卷玄纓,風飄絲袖。”
《補遺》錄作“絲”,誤,應為“絳”。《說文解字注》:“大赤也”。絳袖意為紅色的袖子,是古代官服的顏色,和上句的玄纓構成駢文句式,指的是墓主人做了大官在朝堂之上意氣風發的樣子。這里可能是碑文的漫漶導致字形右下角不夠清晰,造成釋讀錯誤。故此處應為“絳”。
(四)《梁坦暨妻杜氏墓志》:“既毗周翼晉,受魏稱蕃,但厥邑不常,凡經五從,因都梁國。”
《補遺》錄作“從”,誤,應為“徙”。在俗寫中,止的上半部會寫成?,在其他碑刻中亦有此寫法,如《高潭志》:“孝昭皇帝承制作宰,除霸府參軍事,襲爵乘氏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徙并州騎兵參軍事。”《魏故高宗耿嬪(壽姬)墓志銘》:“父紹,除建中將軍、魏郡太守,母冀州渤海吳[2]。”從語義上說,“徙”在《說文解字注》中:“迻也。[5]”意為移動,碑文中本句意為墓主人的祖先經過五次遷徙,最終在梁國定都。故應為“徙”。
三、俗寫而誤
在碑刻文獻中存在著大量的俗寫現象,如果在釋讀的過程中對俗寫情況不了解,就會造成釋讀錯誤。
(一)《李和志》:“魏之末年,政去王室,猬毛蜂起,寓縣沸騰。”
《補遺》作“寓”,誤,原刻作“?”,是“宇”的異體字。《說文解字注》:“屋邊也。從宀于聲。《易·系辭下》曰:‘上棟下宇。’籀文宇從禹。”因為聲符音同,所以當時可以互換,如《元融墓志》:“?望魁悟,風情峻異”。《元昉墓志》:“烈矣垂布于區?”。《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中也記錄了“宇”有?的寫法,“宇,又作?”[6]。從語義上說,“寓縣”不詞,在《漢語大詞典》中解釋為“猶言天下。《史記·秦始皇本紀》:‘大矣哉,宇縣之中’”。本句的意思是魏國末年,王室衰微,各方勢力揭竿而起,天下大亂。故而該字應為“宇”。
(二)《□靜志》:“皇帝養孝尊賢,有踰三代。”
《補遺》錄作“孝”,誤,應為“老”。“老”下半部的“匕”在俗寫中存在寫作“工”的情況,如《賀蘭祥妻劉氏志》:“三呪多男,五福終老。”《中國楷書大字典》引《高貞碑》“老”。《敦煌俗字典》引顏元孫《干祿字書》:“老老:上俗,下正”。“養老尊賢”出自《孟子·告子下》:“養老尊賢,俊杰在位,則有慶。”意為老人得到贍養,賢人受到尊敬。在這篇志文中意為皇帝贍養老人,尊敬賢人,已經超過三代了。故此處應為“老”。
墓志作為一種出土文獻,歷史學、文字學和語言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都是巨大的,所以我們在研究的時候首先要對錄文進行準確釋讀和整理。《全隋文補遺》是我們研究隋朝歷史文化的重要資料,希望對其研究能夠為隋史研究者提供有益幫助。
參考文獻:
[1]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字典[M].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長江出版集團 ;北京:崇文書局,2010.
[2]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墓志匯編[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3]董琨.正字通[M].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6.
[4]釋行均.龍龕手鏡[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M].北京:中華書局,2014.
[6]段玉裁.說文解字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3.
[7]蔡立偉.淺談色彩藝術在服飾中的特性[J].河北旅游職業學院學報,2010(1):93-95+105.
收稿日期:2021-02-05 修改日期:2021-04-0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元明清文獻字用研究”(19ZDA315)
作者簡介:江如昊(1994—),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學2018級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漢語史方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