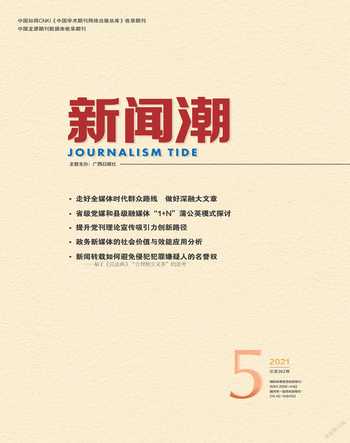新聞轉載如何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譽權
【摘 要】無論是原創媒體,還是轉載媒體,在新聞報道中都應該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譽權。文章認為,原創媒體可以通過持續關注,避免對最終排除犯罪嫌疑的當事人造成名譽侵權。但轉載媒體受海量信息、地域限制、核實能力等因素的制約,持續轉載可能性偏低,較之原創媒體有更大的名譽侵權風險。新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規定了新聞媒體負有“合理核實義務”。文章基于“合理核實義務”的思考,提出新聞轉載中如何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名譽權的策略。
【關鍵詞】新聞轉載;侵犯名譽權;合理核實義務;特定人
犯罪嫌疑人是法律專有名詞,是刑事案件中,對偵查機關立案偵查的對象的統稱。犯罪嫌疑人的稱謂中,核心是“嫌疑”。顧名思義,當事人是否有罪,還處于正在查證的未知狀態,其結果自然就存在“罪”與“無罪”的兩種可能,即存在顯著的不確定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
在新聞實務中,刑事案件發生后,新聞媒體在案件偵查階段便介入報道屬于“常規操作”。在結果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原創媒體可以通過持續關注,避免對最終排除犯罪嫌疑的當事人造成名譽侵權。然而,對轉載媒體來說,尤其是在新媒體環境下,受海量信息、地域限制、核實能力等因素的制約,持續轉載可能性偏低,較之原創媒體有更大的名譽侵權風險。更重要的是,這種風險還受制于人。
2014年4月,H省C市發生的一起非法制造、買賣槍支彈藥案(以下簡稱“徐某涉槍案”),因證據不足,檢察機關作出不予起訴決定。原創媒體在偵查階段對案件報道后,未就審查起訴階段的后續進展進行持續跟進,其結果不得而知。因此,該報道引發了當事人徐某某訴諸媒體系列名譽侵權案。據不完全統計,從2015年10月到2020年9月,全國有31家媒體成為名譽侵權案被告,且無一勝訴。其中,有27家是網絡轉載媒體。[1]
2021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明確規定,新聞媒體在報道過程中負有“合理核實義務”,并明確載明了在認定新聞媒體是否履行合理核實義務時,應當考量的主要因素。在此,筆者結合“合理核實義務”,分析新聞轉載中如何避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名譽權。
一、核實的基礎:考量報道內容與“特定人”關聯的必要
人物是新聞的基本要素之一,刑事案件報道自然也不例外。但偵查階段僅是刑事訴訟的階段之一,充滿了不確定性,無論是犯罪事實,還是可能實施犯罪的人,不僅需要偵查機關、公訴機關的反復探索求證,還需要審判機關的最終認定。從刑事訴訟的角度上說,偵查階段的“人”的確定性是存疑的。
就名譽權而言,名譽權是具體人格權,具有專屬性,是對特定人的社會評價,只為特定權利人所享有。如果行為人的行為不足以確定針對的是某個或某幾個特定的人,則不能認為該行為侵害了他人的名譽權。
確認新聞報道中當事人與被報道對象的“關聯性”是確認是否構成名譽侵權的關鍵。在結果不確定性的背景下,基于多數刑事案件報道的首要目的是警示、教育等,需要反映的是“發生的事”,而非“做事的人”。所以,轉載媒體在對需要轉載的刑事案件報道進行核實時,核實報道內容與“特定人”有無關聯的必要是基礎。這就包括這些內容是否對被報道的當事人進行了必要的匿名、化名處理。對于根據案件報道的需要和案件偵查的需要,確有特定化需要的新聞報道,如協助查找犯罪嫌疑人、協助查找犯罪嫌疑人的可疑行為的,需要對犯罪嫌疑人予以“特定化”的報道;而對于以警示廣大受眾“不可為”某種行為,或者提醒廣大受眾應當注意哪些危險行為,避免將自身的人身財產安全置于危險境地的報道,并無報道對象與“特定人”建立關聯必要的,可以對被報道對象進行必要的匿名處理。一方面尊重結果未定情況下當事人的基本權利,這是法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避免結果“反轉”后將自己置于侵權的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法律規定,確定這種“特定人”的關聯,并不一定需要指名道姓,如果轉載內容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是根據特征描述,依然能夠使社會一般人明確這些內容具體指向“特定人”,同樣也可以認定該轉載行為具有明確的“特定人”指向。所以,轉載媒體在對轉載內容進行審核時,還要核實該內容是否過度披露了不必要的“特定人”特征信息,盡可能的將轉載內容控制在“事”本身,避免過度對不必要的人物特征進行渲染。
此外,在核實“特定人”指向必要的同時,轉載必要同樣也是核實的重點。媒體堅持必要的“有所為有所不為”報道觀點,尤其是刑事案件。并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有報道的必要,相反,過度的報道刑事案件,不僅不能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甚至還可能適得其反。以徐某某涉槍案為例,這是一個普通的涉嫌非法制造、販賣槍支案,其警示、教育意義有限。案件本身所涉的行為影響性低、地域性強、專業性強、可復制性弱。對于轉載媒體來說,缺乏轉載的必要性,也不具備長期跟蹤價值,并且在海量信息的當下,長期跟蹤的難度大,這種內容的轉載,在結果不確定性下,無疑增加了侵權的風險。所以,轉載必要的合理核實,于轉載媒體來說,同樣也是關鍵。
二、核實的關鍵:考察信息來源是否具有權威性
《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六條明確規定了認定新聞媒體是否盡到合理核實義務的數種情形,其中內容來源的可信度是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對轉載媒體而言,需要核實的是該轉載內容的來源,即報道“由誰而做”的問題。雖然《民法典》未就此進行進一步的闡述,但是就內容生產制度、流程管理來說,報道生產機構的專業性可以作為來源可信度的衡量標準之一。在2011年出臺的《關于嚴防虛假新聞報道的若干規定》第二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新聞機構要嚴格使用社會自由來稿和互聯網信息制度,不得直接使用未經核實的網絡信息和手機信息,不得直接采用未經核實的社會自由來稿。對于通過電話、郵件、微博客、博客等傳播渠道獲得的信息,如有新聞價值,新聞機構在刊播前必須派出自己的編輯記者逐一核實無誤后方可使用。”據此,依據規定,就可信賴關系上來說,專業媒體的內容生產從國家制度層面到內部管理層面都有嚴格的管理規范,制度性、程序性、嚴謹性都要高于自媒體。就此而言,其內容可信度更高。
另外,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此前公布的《互聯網新聞信息稿源單位名單》,在業內又稱為轉載新聞“白名單”,有300余家新聞單位在列。依照規定和新聞慣例,這些新聞單位可以作為新聞來源,提供稿源給需要轉載新聞的媒體。從制度、管理層面來說,這些新聞單位生產的內容,其可信度、權威性又更勝一籌。據此,轉載媒體就內容來源的可信度進行核實時,自然要從報道生產機構的可靠性、權威性入手,進行合理的、必要的排序。不能為追求“熱度”,以“吸睛”的可能性來衡量轉載的必要性。
除了報道生產機構的可靠性、權威性核實外,所涉內容出處的權威性同樣也是轉載媒體需要核實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刑事案件,罪與非罪的刑事偵查活動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嚴密性,以偵查機關為代表的權威機關的信息來源是毋庸置疑的要高于其他途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就明確規定:“新聞單位根據國家機關依職權制作的公開的文書和實施的公開的職權行為所作的報道,其報道客觀準確的,不應當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可見,國家機關依職權披露的內容的可信度,是得到認可的。當然,隨著《民法典》的施行,該司法解釋已自然失效。但其留下的司法慣例依然可以作為轉載媒體在履行核實義務時的參考,以降低不必要的侵權風險。
三、核實的底線:恪守無罪推定的原則
無罪推定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通俗地說,在人民法院沒有判決前,不能確定任何人有罪,哪怕此人已經被列為犯罪嫌疑人。
不可否認,社會上許多人的固有觀念中,“被抓”與“有罪”是等同關系。這也是諸多偵查階段刑事案件報道名譽侵權的重要誘因,徐某某訴諸媒體系列名譽侵權案正因如此。
新聞實務中,原創媒體由于地域便利等,及時地了解案件發展的動態,通過連續報道進行一定程度的補救。轉載媒體,尤其是網絡轉載媒體,一般刑事案件持續關注的可能性極低,并且關注的條件也嚴重受限。即便是原創媒體及時連續報道,轉載媒體及時捕捉到的可能性也較低。可見,無罪推定不僅是原創媒體的新聞生產的底線,也是轉載媒體進行核實的底線。避免轉載過程中發生的名譽侵權,于轉載媒體來說,無罪推定就顯得更為重要。
據此,在新聞轉載中,轉載媒體首先要保持必要的克制。對“定性式”語言、“臉譜化”內容、“情緒性”表達的高度戒備,尤其是原創媒體為了使情節生動曲折、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而進行了非案件關聯、非報道必要的過度渲染等。事實上,《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六條明文規定的“合理核實義務”中,也明確地談到了“受害人名譽受貶損的可能性”“內容與公序良俗的關聯性”是核實的重要內容。同時,《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條也明確提出,“使用侮辱性言辭等貶損他人名譽”是損害他人名譽權的行為。
此外,恪守無罪推定的原則,還體現在對時限的核實。偵查活動是一個階段性極強的活動,其有明確的“期限”概念。轉載媒體在進行轉載時,對所轉載的內容披露出的時間,必須進行必要關注。一方面,避免因為信息傳播的滯后性,導致報道所涉內容在轉載時,已成了被否定的“過去式”的可能;另一方面,可以通過披露的時間,及時捕捉原創媒體連續報道的可能。
四、結語
互聯網環境下,在轉載新聞的廣度不斷擴展的背景下,只要恪守無罪推定的底線,把握來源權威性的關鍵,考量“特定人”關聯的必要,勢必能降低或避免轉載新聞侵犯犯罪嫌疑人名譽權的可能。畢竟,其他需要核實的事情,已經超出了轉載媒體核實的能力范圍。而且,《民法典》還明確規定,核實能力和核實成本是評價新聞媒體是否盡到了合理核實義務的要素之一。
參考文獻
[1]譚明.偵查階段刑事案件新聞報道的操作與限制——以徐某某涉槍案引發的系列媒體名譽侵權案為例[J].中國記者,2018(10):96-98.
(責任編輯:黃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