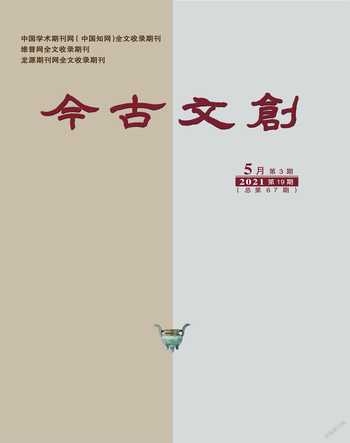女性主義視域下的好萊塢婚戀電影
荊璐
【摘要】 女性主義學者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男性是“此者”而女性是男性的“他者”。如果女性想要自我解放,就必須擁有自我意識,追求自己的超越性,并且最終尋求與男性和解。好萊塢電影《克萊默夫婦》與《婚姻故事》就討論了女性解放的話題,兩位女主角都經歷了覺醒、斗爭、和解三個階段。本文將從女性主義的視角出發,對這兩部電影進行解讀。
【關鍵詞】 女性主義;他者;《克萊默夫婦》;《婚姻故事》
【中圖分類號】J905?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1)19-0078-03
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是法國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是現代最重要的女性主義理論家之一。她一生著書頗豐,其中最負盛名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出版于1949年,被譽為“女性圣經”。此書從哲學、歷史、文學、生物學等多個角度出發,討論了歷史發展過程中女性權利和地位的變化。波伏娃認為女性總是依附于男性,并且處在他者(The Other)的位置。每個人都有其內在性(immanence)和超越性(transcendence),但女性的超越性被嚴重束縛了。這本書還給出了一些關于解放婦女的建議。
在好萊塢,女性解放不是一個新的主題。1979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克萊默夫婦》(Kramer vs. Kramer)就是關于家庭主婦喬安娜的突然出走。丈夫泰德多年的忽視使喬安娜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她決定遠離丈夫和兒子,找回迷失的自我。妻子的離開讓工作狂泰德不得不學做家務,照顧兒子,但他拼盡全力也難以平衡家庭和事業。另一邊,喬安娜恢復了心理健康后,回到紐約索要孩子的撫養權,于是泰德與喬安娜走上了法庭。另一部電影也有相似的主題。《婚姻故事》獲得2019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提名,講述的是查理和妮可的離婚故事。妮可與查理本是一對郎才女貌的璧人,但妮可在婚后多年逐漸明白查理從來不尊重她的個人意愿,限制了她的事業發展。起初,他們決定和平離婚,但是自從妮可請了律師以后,事情開始變得難以控制。
本文共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關于波伏娃的他者理論。其余三個部分將詳細闡述喬安娜和妮可從他者到此者的轉變。第二部分主要講述兩位女主角作為他者的生活,以及她們離開家庭的決定。第三部分是關于她們對超越性的追求。第四部分講述了她們離婚后作為此者的狀態。結語會對全文做一個總結。
一、理論背景
他者是波伏娃女權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也是理解她思想的關鍵。他者是指那些沒有或喪失了自我意識、處在他人或環境的支配下、完全處于客體地位、失去了主觀人格的被異化了的人。[1]這個概念是《第二性》中關于男女關系的部分被提出的。一方面,男女關系不等于陰陽兩極,因為男性既是陽性又是中性,女性只是陰性。比如英文里man既代表人類又代表男性,而woman只代表女性。另一方面,男性是定義女性的參照物,而女性卻不是定義和區分男性的參照。故而男性是唯一的標準,是主體,是絕對,而女性是次要者。例如男人不會寫一本有關男性特殊境遇的書,也不必在序言中介紹自己的男性身份,因為這是不言自明的。但女性的書會提前闡明自己的女性身份,這是后文所有討論的前提立場。在《圣經》里,上帝從亞當身上取出了一根肋骨,將它變成夏娃。這意味著女性不是自主的個體,而是男性的附屬物。女性存在的意義是滿足男性的需求,讓男性生活得更加舒適自在。總之,男性是此者(the One),女性是他者,男性把女性變成了他者。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在分析西方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時提出了內在性和超越性的概念。她說,人需要同時擁有超越性和內在性,為了生存,人不僅要向未來發展,與家庭以外的世界接觸,還需要延續和保存過去的東西。超越性的活動包括寫作、探險、發明,具有一定的創造性和挑戰性,能夠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內在性的活動有烹飪、打掃、生小孩,它們只產生最基本的意義,不僅無法產生經濟價值,還十分費時費力。在傳統家庭中,丈夫是超越性的化身,是具有生產能力的勞動者,是一個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會利益的人,在建設集體未來的同時,通過合作開創他自己的未來[1];妻子是內在性的化身,她被困在照顧家庭和生兒育女這類延續過去的事情上。對于男性來說,婚姻能使他的超越性與內在性完美融合。男性在白天工作中感受變化與進步,在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中遨游,享受存在的意義。當夜幕使他疲倦了,就可以回家舒適地休息。而他的妻子一直為他操持家務,確保家里看起來毫無變化,保障日常生活的穩定節奏和家庭的連續性。但她不可能直接影響未來或世界,她只有以丈夫為中介,才能實現自己的超越性。總之,女性如果想要擺脫男性的支配,就必須努力擺脫僅有內在性的工作,并且勇敢地追求自己的超越性。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還為女性提出了幾個擺脫他者地位的方法。首先,波伏娃堅信女性應取得經濟獨立。換言之,女性應該有一份工作,這樣她與男性的差距便會縮小不少,她的自由也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因為一旦女性不再是寄生者,以她的依附性為基礎的制度就會崩潰,她和這個世界之間也就不再需要男性充當中介。[1]第二,育兒會讓女性在事業上的競爭力降低。有小孩的女性要想繼續工作,只能將幼兒交給親戚、保姆或托兒所,所以獨立女性必須想方設法找人分擔育兒工作。第三,有工作不等于自由,世界仍舊由男性主宰。為了取得終極勝利,女性必須正視她們與男性的自然差異,同男性建立和諧關系。雙方要在關系上自由,在具體問題上平等。
二、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
《克萊默夫婦》的男女主角是一對再平常不過的年輕夫婦。他們婚前都是很有前途的設計師,泰德在廣告公司工作,喬安娜在時尚雜志就職。喬安娜婚后作了家庭主婦,每天獨自料理所有家務,照顧年幼的兒子比利。她很想重回職場,可丈夫斷定她就算能找到工作,工資也不夠付保姆費,所以不同意妻子工作。泰德認為他對家庭的責任就是養家糊口,所以他專注事業,長期忽視家人的情感需求,不做家務也不照顧比利,他甚至不清楚比利在上幾年級。年復一年,喬安娜被困在一成不變的機械性的家務活中:干凈的變臟了,臟的變干凈了,周而復始,就像西西弗斯的詛咒。喬安娜失去了主體性,看起來不像一個獨立的成人,而是一個仆人,她的整個生活都圍繞著丈夫和孩子,圍繞著家務。她勞碌的成果不屬于她自己,而是屬于家庭,屬于做家長的男人。沒有工作的喬安娜失去了和外界接觸的機會,淪為丈夫的附庸,成為一種消極的、內在的、否定性的存在。她逐漸失去自我,變得越來越抑郁。在她十分需要幫助時,泰德沒有耐心去傾聽,他們漸漸變得疏離。喬安娜認為在目前脆弱的精神狀態下,她無法很好地照顧比利,所以她決定離家出走。
《婚姻故事》的女主角妮可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電影新秀,她出生于洛杉磯,與男主角查理結婚后,搬到了他位于紐約的公寓,成了查理導演的劇團的御用女主角。起初大部分觀眾都是被妮可吸引來的,后來查理和劇團的名氣逐漸超過了妮可,妮可在劇團中變得越來越渺小。查理是個控制欲很強的人,每次妮可談到她想嘗試指導一部戲,談到想搬回洛杉磯居住時,查理就開始推脫敷衍,他甚至回絕了一份在洛杉磯的工作。妮可多次收到洛杉磯那邊的電影或電視劇邀約,但為了家庭她都拒絕了。而這次她收到了讓她心動的電視劇試播集的邀約,下定決心要回洛杉磯,查理只淡淡回應道,你賺的錢可以用來投資劇團。妮可終于忍無可忍,她的自我意識覺醒了,終于意識到自己婚后從沒為自己活過。查理控制了她十年,將她變成他者。于是妮可帶著兒子亨利回了洛杉磯的娘家。
雖然這兩部電影相隔四十年,但是喬安娜和妮可在婚姻中都是他者。她們被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困住,失去了自我實現的機會。她們的犧牲被遺忘了,她們的情感需求被忽視了。喬安娜和妮可被看不見的力量強迫著接受自己的次要地位,因為她們的丈夫想讓她們永遠做個他者。
三、女性對超越性的追求
在挪威劇作家易卜生創作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中,同樣被當作他者的 女主角娜拉在故事的最后也離家出走了。然而娜拉出走后的境遇會如何呢?魯迅先生在一場演講中說,娜拉走后只會有兩種結果,不是墮落,就是回來[2]。那個時代的女性很難獨立生存,女性可從事地職業少之又少,薪資比男性低得多,而且非常容易被壞人利用。而對娜拉來說依附于男人繼續做一個“玩偶”也許是相對最容易的選擇。
對于本文的兩個女主角來說,情況就更樂觀一些了。喬安娜生活在《玩偶之家》上演一百年后的時代,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方興未艾。19世紀70年代中期,61%的育齡女性有自己的工作,而對于上過大學的育齡女性,這個數字是86%。[3]雖然還是飽受薪資歧視,但女性已經能夠自己養活自己。喬安娜離開丈夫和兒子以后,到加州重新找到了工作,繼續做起了設計師。她是著名的女子學院史密斯學院的畢業生,再加上婚前的工作經歷,所以找工作對于她來說其實不難。她在加州開始積極尋求心理醫生的幫助,逐漸從失敗的婚姻中恢復過來。她終于可以為自己而活了,有了目標的她找回了那個自由快樂的自己。這是因為她不再是那個只有內在性的家庭主婦了,現在的她既有內在性也有超越性。
與婚后即成為主婦的喬安娜不同,妮可一直有一份工作。但是她的發展受到了丈夫查理的限制。在查理的劇團中她無法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做導演。在離開丈夫回到洛杉磯以后,她參與了電視劇試播集的拍攝。工作人員都很歡迎她并且很欣賞她的演藝成就。與查理不同的是,工作人員們還非常愿意采納她的建議,并且歡迎她參與到編劇的工作中來。當妮可詢問可否嘗試執導時,他們依舊欣然同意。這是妮可在查理那邊永遠也得不到的待遇。在查理眼中電視劇只是不入流的藝術,這個試播集的劇本也很糟糕。在劇團里查理是那個掌控一切的人,所有的細節都由查理決定。在排練或公演時他總是坐在漆黑的觀眾席上用小本子給每個演員寫評語,確保所有演員的演出都能按照他的意思來。妮可雖然表面上很重要,但在劇團里永遠無法發揮創造力,也就是說她無法充分實現自己的超越性。而在劇組里,大家離開攝影棚的時候,妮可走在所有人的前頭,大家緊緊跟隨在她兩側和身后,這說明妮可是這個劇組的核心人物。后來這部電視劇還幫她拿到了艾美獎最佳導演提名。離開查理以后妮可的個人事業發展迅猛,她的超越性不再受到束縛。
去了加州以后,兩位女主角都實現了內在性與超越性的統一,也都由家庭中的他者變成了自己的此者。
四、女性與男性的和解
喬安娜在離家十五個月后終于重新回到紐約工作。她想得到比利的撫養權,于是她和泰德走上了民事法庭,法官最終把撫養權判給了喬安娜,因為法官認為孩子更適合由母親來撫養。但是在比利與泰德分別前,喬安娜前來對泰德說,她很愛比利也很想讓比利同自己住,但是她明白兒子真正的家是他從小長大的地方,也就是泰德的家。所以喬安娜選擇了妥協,并且與泰德和解。電影雖然沒有明說,但是以后他們二人定會一起分擔照顧比利的責任。如果喬安娜獨自撫養比利,她也許很難平衡家庭和工作,因為不論是父親還是母親,獨自養育孩子都很艱難。喬安娜不在的這段時間,泰德為了照顧比利,在工作上犯了許多錯誤,甚至被原公司辭退了。一年半的家務勞動使泰德明白了喬安娜曾經的辛苦,現在的他也很欽佩喬安娜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在他心里喬安娜不再是他者了。
再說妮可,她的同事向她力薦離婚律師娜拉(與《玩偶之家》的娜拉同名)。能力出眾又好斗的娜拉使查理不得不聘請一位同樣好斗且昂貴的律師杰伊。杰伊和娜拉在法庭上劍拔弩張,用夫妻二人的生活隱私來互相攻擊。在付出大量金錢后,查理和妮可終于離婚了。他們平分亨利的監護權,但亨利會跟妮可繼續在洛杉磯生活。萬圣節前一天,查理來拜訪妮可,他說自己接受了一份在洛杉磯的工作,會在這邊待一段時間。妮可也和查理分享了自己得到艾美獎最佳導演提名的喜訊。查理很為她高興。妮可非常幸運,因為她的母親和姐姐在育兒方面幫了很多忙,讓妮可能夠全身心投入到導演和表演的工作中。
喬安娜和妮可在追求超越性的同時,都實現了經濟獨立,并由他者變成了此者。與前夫共享監護權也讓她們更好地投入工作,她們的成功也得到了前夫的認可與贊賞。
五、結語
本文用波伏娃的女性主義理論對好萊塢電影《克萊默夫婦》和《婚姻故事》進行了分析,指出了兩位女主角在丈夫的壓制下淪為他者的本質。隨著她們的女性意識的覺醒,她們開始掙脫自己的身上的枷鎖,離開不平等的婚姻。喬安娜和妮可的經歷表明,女性有能力拒絕父權社會所定義的傳統女性角色,成為自由獨立的女性。因此,運用女性主義來解讀這兩部電影,不僅有助于觀眾更深刻地理解電影,更能引起對女性問題的關注。
參考文獻: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2]魯迅.娜拉走后怎樣.墳[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3]Chafe, William H. Women and American Society. Making America[M].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