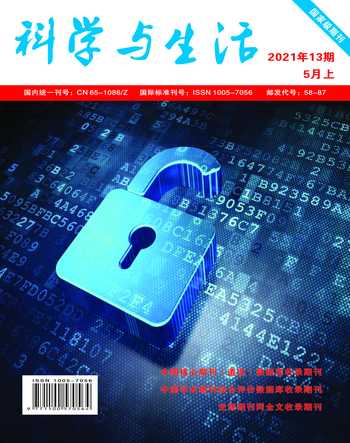科創(chuàng)時(shí)代下,創(chuàng)業(yè)投資機(jī)構(gòu)的挑戰(zhàn)與破局之策
田雨
摘要:在創(chuàng)新驅(qū)動(dòng)的時(shí)代背景下,投資機(jī)構(gòu)的投資方向向硬科技賽道轉(zhuǎn)型。由于我國當(dāng)前的主流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成長于互聯(lián)網(wǎng)模式創(chuàng)新時(shí)期,形成了一套投資方法和投資邏輯。而硬科技企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主體多為科技工作者,背靠知名高校和研究機(jī)構(gòu),投資機(jī)構(gòu)在面向硬科技企業(yè)時(shí),產(chǎn)生很多不適應(yīng)現(xiàn)象。本文旨在對投資機(jī)構(gòu)在科創(chuàng)時(shí)代下的挑戰(zhàn)予以分析,并給出部分破局之策。
關(guān)鍵詞:創(chuàng)業(yè)投資,風(fēng)險(xiǎn)投資;科技創(chuàng)新
0引言
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從高速增長轉(zhuǎn)向平穩(wěn)增長的同時(shí),也進(jìn)入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的關(guān)鍵時(shí)期,逐步從粗放型發(fā)展轉(zhuǎn)向精細(xì)發(fā)展,一大批落后產(chǎn)業(yè)將會(huì)逐步淘汰,以高技術(shù)、高知識(shí)密度為要素的新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時(shí)期。這一時(shí)期,以高技術(shù)壁壘為特點(diǎn)的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將迎來重要機(jī)遇。尤其是科創(chuàng)板的正式運(yùn)行,為硬科技企業(yè)和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帶提供了資本市場環(huán)境。中國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多成長于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在上世紀(jì)80年代末期起步的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革命,中國并未真正引領(lǐng)技術(shù)發(fā)展,而更多的是在應(yīng)用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進(jìn)行模式創(chuàng)新。于是,在一段時(shí)期,我國早期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產(chǎn)生一種獨(dú)特投資邏輯,就是尋找美國的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品在中國的同類型創(chuàng)業(yè)者,并通過資本加持,幫助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快速發(fā)展。這直接誕生了一批以BAT為代表的互聯(lián)網(wǎng)巨頭,并催生了一批頂級(jí)私募投資機(jī)構(gòu)。然而,在互聯(lián)網(wǎng)流量紅利被收割殆盡之后,中國經(jīng)濟(jì)轉(zhuǎn)軌換道的歷史大背景下,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對高技術(shù)壁壘的創(chuàng)業(yè)者,產(chǎn)生了不適應(yīng)。總體而言,對技術(shù)創(chuàng)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律仍未真正摸透,即使是行業(yè)現(xiàn)行的部分投資機(jī)構(gòu),也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主要面臨如下挑戰(zhàn):
一、創(chuàng)業(yè)主體的特殊性
當(dāng)前,很大一部分早期高技術(shù)企業(yè)源生于科研院所與高校,其技術(shù)創(chuàng)業(yè)主體多為科研工作者,在國家頒布成果轉(zhuǎn)化法,人社部頒布《關(guān)于支持和鼓勵(lì)事業(yè)單位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的指導(dǎo)意見》以來,以中科院為代表的科研機(jī)構(gòu)配套一系列促進(jìn)成果轉(zhuǎn)化辦法,高校、科研院所的產(chǎn)業(yè)化熱情高漲,釋放出一批科研人員的創(chuàng)業(yè)嘗試。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面臨一批前所未有的創(chuàng)業(yè)者,與當(dāng)年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者不同,他們可能從未或極少有過參與企業(yè)經(jīng)營的經(jīng)歷,對資本市場的認(rèn)識(shí)還未充分形成,價(jià)值追求與上一批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業(yè)者也有很大的差異。對技術(shù)的研究深度和知識(shí)深度遠(yuǎn)勝于互聯(lián)網(wǎng)黃金時(shí)期的創(chuàng)業(yè)者,但對外部商業(yè)信息的敏感性卻也天然存在缺失。誠然,優(yōu)秀科學(xué)家是稀缺資源,優(yōu)秀企業(yè)家也是稀缺資源,期待兩種人的特質(zhì)集中在同一人身上,是可遇不可求的。如何從原有對創(chuàng)業(yè)者的“人”的評(píng)價(jià)邏輯中走出來,重構(gòu)技術(shù)型人才主導(dǎo)創(chuàng)業(yè)團(tuán)隊(duì)的評(píng)價(jià)邏輯,是一大挑戰(zhàn)。曾有文章報(bào)道,有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以科技成果水平和科學(xué)家科研地位去對項(xiàng)目進(jìn)行估值,這顯然有失正確性。心態(tài)更為開放,能夠找到并接納好的商業(yè)合伙人的科研人員應(yīng)當(dāng)受到投資方的更多信任。
二、單點(diǎn)技術(shù)生命周期與規(guī)模挑戰(zhàn)
創(chuàng)投資本天然追求高增長性和規(guī)模性,科技型企業(yè),越是超前技術(shù),其技術(shù)成熟和需求釋放也越需要更長的時(shí)間。此外,從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規(guī)律看,一種技術(shù)的參與者不夠多,要么形成壟斷,要么會(huì)走向另外一個(gè)極端,即不被產(chǎn)業(yè)界接受。科研成果實(shí)現(xiàn)工程化,再到商業(yè)化,是存在高度不確定性的,面向統(tǒng)一需求,多種技術(shù)路線可能并行。科研院所所孵化的技術(shù)創(chuàng)業(yè)企業(yè),與原有創(chuàng)業(yè)者提供2C產(chǎn)品相比,往往是解決產(chǎn)業(yè)需求,客戶以其他企業(yè)為主。這就使其商業(yè)爆發(fā)周期也變慢。同時(shí),由于外部需求的不斷變化,在單點(diǎn)技術(shù)帶來的早期技術(shù)壁壘期,若沒有真正形成企業(yè)自身的獨(dú)立持續(xù)創(chuàng)新能力,未形成創(chuàng)新機(jī)制和文化土壤。單點(diǎn)技術(shù)企業(yè)還面臨生命周期過短的問題。這給投資機(jī)構(gòu)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
三、投資機(jī)構(gòu)需要加強(qiáng)對技術(shù)規(guī)律的理解
投資機(jī)構(gòu)的經(jīng)理人團(tuán)隊(duì),原多為財(cái)經(jīng)、金融背景出身,在面向技術(shù)創(chuàng)業(yè)項(xiàng)目時(shí),表現(xiàn)出對技術(shù)的理解不足。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技術(shù)領(lǐng)域,涉及多門類的基礎(chǔ)學(xué)科及理工科知識(shí)。這直接造成對技術(shù)看不懂,進(jìn)而變成了追熱點(diǎn)似的投技術(shù),對一些科學(xué)家做出的“冷門技術(shù)”無人問津,造成某些方向的資本過密,形成了投資泡沫。技術(shù)發(fā)展有其客觀規(guī)律,從實(shí)驗(yàn)室到工程化,再到產(chǎn)品化,相同的技術(shù)可能會(huì)誕生不同的應(yīng)用方向。底層技術(shù)應(yīng)用的可遷移性,是實(shí)現(xiàn)企業(yè)范圍經(jīng)濟(jì)的一種重要路徑。因?yàn)閷夹g(shù)的理解不夠,可能會(huì)出現(xiàn)對市場應(yīng)用空間的誤判。
四、盲目的科學(xué)家崇拜以及盲目的輕視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
在科技創(chuàng)投領(lǐng)域,出現(xiàn)了對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的兩極分化,一部分投資人開始極力追逐頂級(jí)科學(xué)家團(tuán)隊(duì),神話科學(xué)家在企業(yè)發(fā)展中的作用,進(jìn)而出現(xiàn)人才帽子估值法、影響因子估值法的鬧劇,科學(xué)家之間也出現(xiàn)盲目攀比,把估值當(dāng)做另外一張”學(xué)術(shù)身份”,把估值高低當(dāng)做了資本市場對學(xué)術(shù)成績的評(píng)價(jià)。另一部分投資人則走向極度不信任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的另一個(gè)極端。認(rèn)為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不靠譜,學(xué)者不懂商業(yè)規(guī)律,缺少企業(yè)、產(chǎn)業(yè)經(jīng)驗(yàn),在創(chuàng)業(yè)這件事上,科學(xué)家主導(dǎo)的企業(yè)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事實(shí)上,企業(yè)發(fā)展在不同階段,需要的人才也不盡相同。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要素的企業(yè),在其早期需要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扮演重要角色。在這一過程中,主導(dǎo)企業(yè)的科學(xué)家,需要實(shí)現(xiàn)從學(xué)術(shù)思維到工程師思維、產(chǎn)品思維、商業(yè)生態(tài)思維的幾次躍遷。如果不能躍遷,則需要有信賴的商業(yè)合伙人的介入。所以,兩個(gè)極端都是盲目的。
五、科學(xué)家對創(chuàng)投本身的理解不到位
有部分科學(xué)家,可能會(huì)對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產(chǎn)生認(rèn)知偏差,優(yōu)質(zhì)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在對項(xiàng)目盡調(diào)時(shí)相對嚴(yán)密,投資決策周期相對長。而部分個(gè)人資本和小基金,反而表現(xiàn)出了快捷性。另一方面,投資人的文化和價(jià)值觀特質(zhì),跟科學(xué)家有時(shí)會(huì)產(chǎn)生沖突。這都增加了雙方?jīng)Q策選擇上的誤判,可能導(dǎo)致部分機(jī)構(gòu)在投資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項(xiàng)目時(shí)的重重障礙。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些有研究所、高校背景的投資機(jī)構(gòu)。這些投資機(jī)構(gòu)具備很強(qiáng)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型項(xiàng)目渠道,在歷史大背景下,表現(xiàn)亮眼。但是,仍舊需要周期的磨礪。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在面對上述挑戰(zhàn)的過程中,需要作出一系列調(diào)整。投資完成前后,需要為被投企業(yè)提供更多的服務(wù)。這些服務(wù),未必由機(jī)構(gòu)自身完成,但必須具備一定的“孵化”能力。
六、投資機(jī)構(gòu)需要扮演好多元中介角色
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有其中介屬性。在科技創(chuàng)業(yè)大潮中,面對上述挑戰(zhàn),不僅要扮演好資本的中介,還需要扮演更多的中介角色,成為一個(gè)創(chuàng)業(yè)要素的交匯地。首先,就要成為人才要素的中介。科技創(chuàng)投機(jī)構(gòu)能夠發(fā)揮好自身在不同產(chǎn)業(yè)中的鏈接作用,把產(chǎn)業(yè)中的人才,引向被投企業(yè),把科學(xué)家的成果引向產(chǎn)業(yè)界。第二,扮演市場中介,科技創(chuàng)業(yè)團(tuán)隊(duì)的技術(shù)壁壘夠高,但新興產(chǎn)品面向市場,缺少渠道。第三,地方產(chǎn)業(yè)落地中介,由于技術(shù)企業(yè)的研發(fā)多源自一線城市,生產(chǎn)制造環(huán)節(jié)往往需要在,應(yīng)當(dāng)能夠?yàn)槠髽I(yè)真正找到能夠適于其長期生產(chǎn)經(jīng)營的落地地點(diǎn),其核心是產(chǎn)業(yè)區(qū)域性優(yōu)勢。
七、為企業(yè)輸出創(chuàng)新文化和機(jī)制
從長期看,一個(gè)技術(shù)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真正實(shí)現(xiàn)長期的競爭力,必須具備持續(xù)的創(chuàng)新能力。只有具備持續(xù)的創(chuàng)新能力的高科技企業(yè),才能真正避免僅靠單一技術(shù)優(yōu)勢保持幾年的領(lǐng)先性,而后快速被新技術(shù)企業(yè)淘汰。這里所強(qiáng)調(diào)的創(chuàng)新,是全面的創(chuàng)新,首先是根據(jù)市場的需要,技術(shù)方面的持續(xù)迭代和研發(fā)能力。其次,避免在商業(yè)模式上創(chuàng)新的阻力。硬科技企業(yè),容易輕視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甚至有企業(yè)將模式創(chuàng)新擺到對立面。此外,在用人機(jī)制,激勵(lì)方式,企業(yè)創(chuàng)新文化養(yǎng)成上,硬科技企業(yè)也需要做出大的突破,因?yàn)楹芏嘤部萍计髽I(yè)會(huì)受制于研究機(jī)構(gòu)固有模式的影響,導(dǎo)致機(jī)制僵化。幫助硬科技企業(yè)形成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新文化,也是投資機(jī)構(gòu)需要具備的能力。在技術(shù)團(tuán)隊(duì)期權(quán)池(按照技術(shù)轉(zhuǎn)化規(guī)定,多數(shù)硬科技企業(yè)技術(shù)人員可以獲得一半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獎(jiǎng)勵(lì))基礎(chǔ)上,形成管理團(tuán)隊(duì)期權(quán)池,引入其他普適的激勵(lì)創(chuàng)新的機(jī)制,對一家硬科技企業(yè)的持續(xù)發(fā)展有重要作用。為被投企業(yè)創(chuàng)始人提供體系化的商業(yè)培訓(xùn)課程,是一個(gè)不錯(cuò)的選擇。
八、構(gòu)建多元能力的投資團(tuán)隊(duì)
投資機(jī)構(gòu)推崇的合伙人機(jī)制,強(qiáng)調(diào)人才要素在投資中的作用。面對硬科技企業(yè)這一新的投資標(biāo)的,投資人的人才畫像也需要重構(gòu)。目前,越來越多的投資機(jī)構(gòu)開始招募理工科碩博士,尤其是具有研究機(jī)構(gòu)工作經(jīng)驗(yàn)者,這有利于加強(qiáng)對硬科技技術(shù)原理的理解。但是,也急需投資機(jī)構(gòu)快速形成機(jī)制,讓符合新需要的投資經(jīng)理群體,快速理解投資,快速走進(jìn)投委會(huì),從而快速提升機(jī)構(gòu)的決策力,形成真正高效的決策機(jī)制,才能實(shí)現(xiàn)最終的投資團(tuán)隊(duì)的能力轉(zhuǎn)變。此外,因?yàn)橛部萍计髽I(yè)面向行業(yè)客戶為主的性質(zhì),導(dǎo)致投資機(jī)構(gòu)面向產(chǎn)業(yè)吸納具備行業(yè)認(rèn)知的投資人,也是不可回避的路徑選擇。更深的產(chǎn)業(yè)知識(shí)+技術(shù)理解力,是硬科技創(chuàng)業(yè)周期下,投資機(jī)構(gòu)必須補(bǔ)強(qiáng)的能力。
九、與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者建立互信
觀念的對沖,嚴(yán)重阻礙投資決策的平滑性。科研人員的觀念和資方觀念沖突點(diǎn)主要集中在對技術(shù)要素和資本要素孰輕孰重上,集中爆發(fā)在投資協(xié)議條款談判上。這需要盡快與科學(xué)家群體建立互信。科學(xué)家往往就職于大的研究機(jī)構(gòu),屬于事業(yè)單位,相對更加注重誠信,也更加純粹,與原有創(chuàng)業(yè)群體相比,重視對投資機(jī)構(gòu)的承諾,但不愿意簽署業(yè)績對賭,不愿意接受回購條款。實(shí)際上,科學(xué)家的嚴(yán)謹(jǐn),導(dǎo)致往往有做“十分,說三分”傾向,與創(chuàng)業(yè)圈原有的“做三分,說十分”的不良傾向不同。所以,在重視技術(shù)要素的時(shí)代背景下,資本需要與科學(xué)家群體增加互信,減少觀念對沖。機(jī)構(gòu)需要尊重客觀規(guī)律,更有智慧,面向科學(xué)家創(chuàng)業(yè)群體,在硬科技企業(yè)的早期投資輪,給到更多的理解和傾聽,做更聰明,寬松的投資人。
參考文獻(xiàn):
[1]創(chuàng)業(yè)投資對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作用機(jī)制研究[J]. 白素霞,陳彤.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 2018(03)
[2]風(fēng)險(xiǎn)投資對我國區(qū)域創(chuàng)新能力及經(jīng)濟(jì)增長的影響——基于全國21個(gè)省市的實(shí)證研究[J]. 張俊芳,郭永濟(jì). 科學(xué)與管理.
[3]科創(chuàng)板:中國創(chuàng)新助推器[J]. 石琳. 張江科技評(píng)論. 2019(03)
[4]五個(gè)角度深入了解科創(chuàng)板[J]. 許志峰,屈信明. 商業(yè)文化. 20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