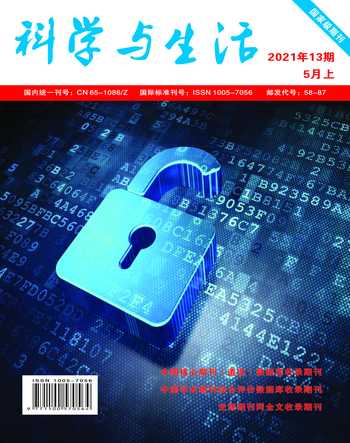從歌手阿蘭維權簡析填翻歌曲是否侵權
劉爽 高雅娟
摘要:目前,仍有許多填翻創作的主體們對著作權使用制度存在誤解,他們認為只要不以盈利為目的,即使未取得原作者授權,使用他人作品也不會觸犯著作權法。基于此,我們提出以下問題:填翻創作的歌曲究竟有沒有觸犯著作權法?在越來越重視版權的今天,填翻歌曲將何去何從?本文將從學理關系、合理使用的界限、原作授權入手,對填翻歌曲的地位進行闡釋。
關鍵詞:版權;著作權使用制度;填翻歌曲
2019年11月28日,歌手阿蘭的工作室發布了一條微博,要求下架所有未經授權的翻唱歌曲,這引起了一波來自古風圈和原創音樂圈的討論。這些翻唱歌曲大部分為二次創作的產物——即利用原曲重新進行填詞,或主動、或由系統抓取發布在各個音樂平臺上。同年12月1日,阿蘭再次更新微博,表示很多侵權翻唱的歌曲已經被下架,次日,QQ音樂小助手也在其微博下評論,放出了一張配合這次維權下架的歌單。
對此,有人點贊有人憤怒。點贊是因為這是版權意識加強的表現,展示出對原創音樂的鼓勵和支持;憤怒則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填翻歌曲本來是自娛自樂,并沒有上升到“侵權”這樣嚴重的程度。對歌曲進行填詞翻唱,造成了侵權行為嗎?這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問題。
一、填翻歌曲解讀
填翻歌曲,即填詞翻唱歌曲,屬于二次創作的范疇,是在已存在的音樂的基礎上重新填詞并進行演唱的作品。早在2005年,由于仙劍奇俠傳等仙俠類游戲興起,一些傳統文化愛好者便利用游戲中的配樂和日本歌曲進行填詞,這也是古風圈的雛形。
填翻歌曲的主體最初活躍在中國原創音樂基地,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與發展,逐漸轉移到網易云音樂等新興音樂APP中,如2019年大熱的填翻《起風了》《我的一個道姑朋友》等,就是在網易云音樂一炮而紅的。填翻歌曲本身含有一定特殊性與依附性,其一,雖然填翻歌曲是借助原作素材進行再創作的,但是其中包含了填詞者的智力成果,不同于簡單的搬運與復制;其二,填翻歌曲的“創作者們”的創作動機很大程度上是自娛自樂的,不論是填詞者還是翻唱者,都是憑借興趣、出于愛好,展示個人情懷,并非為追求商業利益[1]。
可以說,填翻歌曲是由互聯網催生的一種新型創作模式,十幾年的發展間,為文學、音樂愛好者們提供了展示自我的機會,也間接捧紅了很多二次元的“唱見”。填翻歌曲發展迅速,但是實際上問題頻發,幾乎成了音樂作品侵權的“重災區”。
二、從學理關系看填翻歌曲
判斷填翻歌曲侵權與否,需要先厘清概念,即填翻歌曲與原著作權人的人身權、財產權是否產生沖突。
(1)署名權層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十條,著作權人享有署名權,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權利。這是著作權人的人身權之一,保護期不受限制。根據網友提供的截圖,有些填翻歌曲選用了阿蘭的原創歌曲,但是標注的信息不完全,未明確標出原作詞作曲及演唱者的姓名,或者標上填翻創作者自己的姓名,更有將原作姓名標錯的現象出現。在實踐中,這種現象導致雙方可能圍繞署名權產生侵權糾紛。
這并非個例。在2017年,歌手張靚穎在音樂綜藝《夢想的聲音》中演唱了來自古風圈的知名歌曲《浮生未歇》,卻在當時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曲部來自日本女歌手中島美嘉的《櫻花紛飛時》,歌詞則經由詞作恨醉重新填寫。然而,節目組在播出字幕中將原唱標注為音頻怪物,而且未列出作曲者等的署名信息。雖然被人詬病,但是目前這兩版歌曲依然在各大音樂平臺播放[2]。從這一點來看,有些填翻歌曲侵犯了原作者的署名權。
(2)信息網絡傳播權
信息網絡傳播權,即著作權人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力。雖然填翻歌曲在性質上已經不同于原作品,被賦予了新的內涵和內容,但是仍然難以“掙脫”原作而存在。填翻歌曲被主動上傳到互聯網上供他人欣賞,屬于二次創作者的意愿,雖然無獲利行為,但是作品的投放平臺卻因用戶流量變現而帶來的廣告投放等方面坐收漁翁之利。除此之外,填翻歌曲的二次創作者沒有向原著作權人取得授權并支付報酬,在實踐中這種行為往往侵犯了著作權人的信息網絡傳播權。
(3)改編權
改編權,即改變作品,創作出具有獨創性新作品的權利。實踐中改編分為兩類,一類是不改變基本內容,作品由一種形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如將小說漫畫改編成電影等;另一類則是就其內容進行再創作[3]。毫無疑問,填翻歌曲要歸屬于后者,針對音樂作品而言,如果有人想要對音樂作品進行改編,必須征得原音樂作品著作權人的許可[4]。實踐中,很多填翻歌曲是沒有成功取得授權的,這就侵犯了原音樂作品著作權人的改編權。
三、從合理使用的界限看填翻歌曲
根據著作權法第22條,為個人學習、研究或者欣賞,使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過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
那么,填翻歌曲屬于合理使用的范圍嗎?普遍意義上來說,是可以合理使用的,自娛自樂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移動互聯時代,填翻歌曲會吸引粉絲或者普通用戶點擊收聽,平臺因此坐收其成,收割用戶流量,這是互聯網變現獲利的重要來源,更遑論有些二次創作者會因此受到打賞。這些流量實際上的變現,其實是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原著作權人的利益。所以從合理使用來看,這條界限并不明顯,有些填翻歌曲造成商業性侵權事實,侵犯了著作權人的一部分權利。
四、從原作授權與否看填翻歌曲
2019年除了阿蘭維權引起討論之外,《我的一個道姑朋友》也曾卷進“侵權”的輿論漩渦之中。這首歌是填翻歌曲,原曲是日本歌手田井中彩智的《一番星》,是歌手為紀念去世的爺爺而創作的。《我的一個道姑朋友》則是由三個糙漢一個軟妹組在未拿到原作授權而且在原作者聲明禁止二次創作或者商用情況下翻唱的劍網3劇情歌。在經歷了全網批評、下架之后,制作組與日文原版創作人進行溝通,成功取得了原唱授權并支付了費用,《我的一個道姑朋友》后由雙笙重新演唱,在網易云音樂發布。
阿蘭所在的愛貝克思唱片公司也明令禁止,未取得唱片公司授權,不得進行二次創作。那些利用阿蘭的原曲進行填翻的歌曲,又有哪一首曾經獲得授權?雖是興趣使然,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拿來主義”,使得原著作權人的權利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
五、填翻歌曲的發展路徑
經由以上討論我們可以看出,不論采源為國內音樂抑或國外音樂,未經過授權的填翻歌曲本質上就是侵權的,阿蘭提出填翻歌曲下架是無可厚非的,這是保護著作權人的權益和利益。那么,對于僅僅出于興趣的二次創作者來說,他們的填翻生涯是否應該就此終結?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隨著古風圈的發展,已經出現了很多優秀的音樂創作人,他們也帶來了優質的古風原創歌曲。有些歌曲會開放非商業的二次創作授權,即開放改編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但是保留署名權。這對于填翻歌曲的制作者來說,是一舉兩得的:既能保全興趣,又不會擔上侵權的風險。此外,保護期限已過的公版歌曲也可在注明姓名的情況下進行非商業的二次填翻。
未來,隨著版權意識的提升,填翻歌曲也會跨進一個新的臺階,成為互聯網平臺創作的重要模式之一,因此,需要用戶個人、平臺、政府共同攜手努力,補齊二次創作的短板。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國家版權局副局長閻曉宏曾談到:“公眾的版權保護意識怎么樣,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版權水平怎么樣。”用戶的版權意識提高對國家版權建設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見,填翻歌曲的版權保護應該從源頭出發,增強填翻歌曲創作者的版權素養,在根本上杜絕無授權使用的行為,這是避免侵權的最有效途徑。此外,平臺內的監管也應承擔一定責任,而不是要等到被起訴才開始重視,發現維權現象及時處理,完善版權保護技術,加大侵權的懲處力度;與此同時,平臺也要保護著作權人的利益,。政府應該加緊跟進產業版權保護政策,開展專項整治,三方合力之下,引導以填翻歌曲為代表之一的二次創作向規范性、健康化發展,我們的文化也就會更加繁榮。
參考文獻
[1]卞娜娜,王鵬飛.二次創作版權問題探討[J].中國編輯,2019,(6):76-80.
[2]張書樂.古風歌曲:盜版還是傳承[J].知識產權,2018,(9):80-81.
[3]燕羽豐.同人作品著作權侵權的界定[J].阜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30):93-96.
[4]方明東.翻唱《南山南》為何被作者叫停[N].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15-10-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