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合
摘 要:黑格爾將事物運動歸結為“正反合”式的辯證發展,即正題、反題與合題,這也應是判斷審美心理發展特點時的應有命題。審美心理肇始于主體對形象的直覺。作為主體的人,與對象之間是疏離的。這種疏離并非空間疏離,而是心理認知的疏離,此為正題。然而隨著審美主體逐漸掌握了形象背后的意義,人與物之間在心理上的疏離狀態會被打破,這就是對立面分化而出的反題。但真正成熟的審美心理不是心中空無一物的直覺,也并非過分貼近對象的本質而難以擺脫其現實意義,而應該是二者的綜合,在更高的層面上主動選取正題與反題中的某些積極因素,以“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的態度對待審美對象。如此,才是成熟審美心理的應有之貌。
關鍵詞:審美心理 審美直覺 心理距離 辯證發展
美是什么?這個問題從古希臘開始就一直被人們討論著。畢達哥拉斯學派提出美是數的和諧,柏拉圖倡導美在于作為普遍本質的理念,普洛丁認為美源于“太一”。可見,人們在探索人與物之間的這種特殊審美關系時,首先將關注的目光放在了“什么樣的事物是美的”或“是什么賦予了事物可以讓我們感受到美的性質”的問題上。總之,人們的思考大多聚焦于客觀的事物之美。而近代美學則開始逐漸關注審美關系中的另一端,即審美主體的心理特點。這一轉向普遍認為始于康德。康德以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將關于“美是什么”的客觀性研究轉變為“審美是什么”的主觀性研究,把美學研究的出發點歸置于審美主體的鑒賞判斷。人們開始意識到人的心理在審美活動中的重要性,用朱光潛先生的話來說即是“我們必須先知道怎樣的經驗是美感的,然后才能決定怎樣的事物所引起的經驗是美感的”[1]。
審美心理的本質特征是人對形象的直覺,也就是說當人只見事物形象而不見其現實意義時,審美愉悅才得以產生。否則,它將進化為知覺甚至概念,從而使人跌落進對事物現實性的認知中,難以獲得美的享受。但是人們在現實的審美活動中常常會感到,如果缺乏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則無法體驗其更深層的美感,以致審美體驗流于表面。可是,如果過于關注事物的現實意義,又會使人與美的感受相隔絕。審美心理的特點來自人對形象的直覺,然而產生美感的前提又不止于對形象的直觀感受,還需要廣泛的人生閱歷,以及對事物本質和運動規律的認知。如此一來,審美心理的內涵就變得相對復雜起來,在形象的直覺和人生的觀照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距離,就成為美感產生的必要條件。黑格爾將事物運動的特點歸結為“正反合”式的辯證發展,即正題、反題與合題,這恰恰也應是人們在判斷審美心理發展特點時的應有命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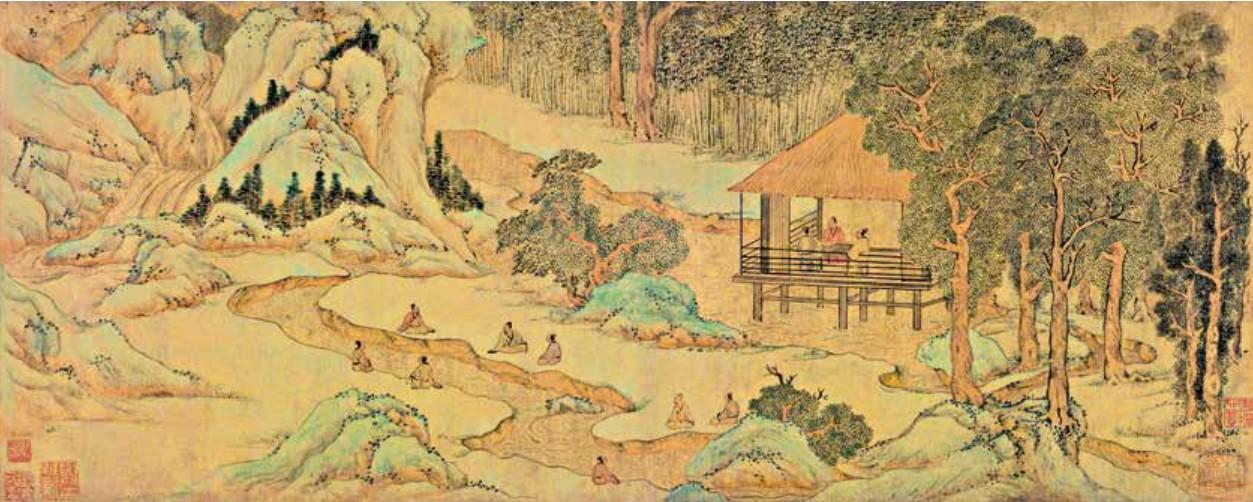
審美心理肇始于人們對形象的直覺感受,這的確是它所應有的本質意義。直覺處于人類以心知物的初級階段,直面事物的形象而非意義是由于人的認知尚未完善,作為主體的人與對象之間是疏離的。這種疏離并非空間疏離,而是心理認知的疏離。這是審美心理得以發生的條件,也是其發展的起點,即正題。隨著審美主體不斷豐富閱歷、提高認知,他在面對對象時便不再只是注意形象本身,而是掌握了形象背后的意義,從而將自我代入其中,改變了“我”與物在心理上的疏離狀態,這就是對立面分化而出的反題。但真正成熟的審美心理不是心中空無一物的內心,也并非過分貼近對象的本質而難以擺脫其現實意義。它應該是二者的綜合,在更高層面上主動選取了正題與反題中的某些積極因素,以既熟悉又陌生的態度對待審美對象,在不脫離審美的基礎上拓展其感受的廣度與深度。如此,才是成熟審美心理的應有之貌。
一、正題——形象的直覺
審美感受是一種直覺愉悅感,這種直覺愉悅感源于審美對象的觸發,而觸發直覺的是對象的形象。克羅齊認為人在形成概念之前的思維活動是直覺,直覺就是審美的本義,是審美的入門要求。直覺在于人尚未擁有認識一般事物的能力,就像幼童在面對一百元紙幣時,他能看到的只是一張長方形紙片,上面有不同的色彩,這是他的直覺感受。一百元紙幣的意義是幼童所不能理解的,唯有當他逐漸經歷世事,發現許多東西都需要用這張紙片交換才能得來時,方能明白它的現實意義。這個時候一百元紙幣在他眼里就不再是一張長方形的彩色紙片,而是可以購買貨物、儲存財富的現實貨幣,他的認知也不再是對紙幣形象的直覺感受,而是對紙幣契約本質的理解。美感也是如此,它在根本上并不是人們對事物性質“是什么”的認知,而是對形象最直接、最純粹、最強烈的直覺感受。研究審美其實就是研究直覺,直覺的經驗就是審美的經驗,而事物的形象就是審美直覺的對象,“在美感經驗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覺,物所以呈現于心者只是形象”[2]。
舉例而談,芭蕾作為一種形體藝術,展現的是人的形態美。如果帶著超越人體形象本身的認知去看待演員的身體時,可能會引發有關欲望的念頭,那這便是一種非審美的眼光,逾越了欣賞身體美的界限而落入對欲念的滿足中。如果用幼童般的直覺來感知芭蕾,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人的身體所構建出的或靜止或舞動的形象,且僅限于此。在法國浪漫主義芭蕾舞劇的開山之作《仙女》中,瑪麗亞 塔里奧尼用她那纖細而富有力量的肢體、試圖突破地心引力的腳尖舞技術以及輕盈飄逸的白色紗裙,向觀眾展示了一個夢幻浪漫的仙女形象,觀眾所欣賞的也正是由這些元素組合而成的形象本身。如果觀眾由女演員舞動的腰肢腿腳而產生欲望的念頭,感受不到眼前舞者塑造的形象,那審美感受也就無從談起了。當然,芭蕾舞女演員的選角標準是“三長一小”、四肢纖細且具有骨感美,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隔絕了人們由豐腴肉體觸發欲念的機會,在賦予芭蕾藝術高貴典雅之美的同時,也限制了觀眾對身體形象的直覺感知,保證了審美感受的發生。

王夫之用古代印度因明學中的“現量”一詞闡釋了審美心理的性質,即人的審美感受源于對事物的直接觀照。“‘現量’,‘現’者有‘現在’義,有‘現成’義,有‘顯現真實’義。‘現在’,不緣過去作影;‘現成’,一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真實’,乃彼之體性本自如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3]“現”作為審美心理的本質特點,其含義在于真實的直接感知,是當下瞬間的直覺。因此,審美感受絕不是停留在腦海中的印象,既不摻虛假,也無須做邏輯思維的判斷與分析。當人們在面對一座山、一片海時,眼前只有山和海的形象,腦海中并不會泛起與之相關的效用等聯想。這樣一種“我”與物在直覺感知上的對立是審美心理的第一個階段,即正題。也就是說,如孩童一般純真明凈的赤子之心,是人們得以感受美的主體條件。然而,如果在人的認知發端處,只有對形象的直覺感知則不一定能生發出對美的深刻感受,因為他缺乏一定的人生經歷,缺乏將對象“自我化”的力量。就像一個幼童在面對一只蟬時,蟬的形態特征可以直接作用于其直覺,但是他尚未能感受蟬之美。虞世南卻能由蟬的形象產生“居高聲自遠,非是借秋風”如此深刻的審美感受。他在面對蟬時也沒有用生物學的概念來解剖蟬,只是他在直面棲落在梧桐樹上的那一只獨立完整的蟬時,蟬在他這里成了一位立身高潔的君子,而他由蟬的形象直觀自身,以共鳴的方式獲得了強烈的審美感受。如果沒有一番閱歷,沒有自信自洽的人生品格,恐怕虞世南不會在直覺瞬間將自我代入蟬的形象之中,那么蟬作為審美的形象也就無從談起了。這時,審美心理在發展過程中就走向了第二個階段,即反題。
二、反題——人生的觀照
當審美心理發展到第二個階段時,審美主體與客體的心理疏離狀態就會被逐漸打破,有兩種方式可以體現這種變化。一種是旁觀式的,即理解形象背后的含義,從認知本質上拉近人和審美對象之間的距離,從而更從容地看待審美對象作為形象的意義。莊子在《逍遙游》中說:“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4]雖然人的審美直覺是從觀照形象開始的,但是在觀照形象前如果沒有一定的知識儲備,缺乏對形象本質的了解,就難以對形象有更透徹的把握。正是因為有了對形象本質的了解,形象所帶給人們的美的感受才會更強烈,這是一種在滿足理性認知前提下的感性審美愉悅。如此,審美感受便上升了一個層次。
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我們所說的“美感經驗源自對形象的直覺”也是這一道理。當我們面對一件事物時,經驗愈多,知識愈豐富,聯想也就愈復雜,因而在審美體驗時很難丟掉它的一切關系和意義,純粹專注于其形象本身。但是完全離開對事物本質的認知,我們又無法體驗更為深刻的美感。那么,人們又如何才能以當下的直覺深刻完整地感受到對象的美呢?自然美源于人的過往經驗和知識儲備。美感雖不是理性認識,但認識卻是觸發深度美感的前提。它們具有內在的關聯性,以往的知識可以在當下的直覺體驗中發揮作用,而當下這種剎那間的直覺也可以昭示出必然的將來。胡塞爾關于“現象學時間”的論述闡明了這一點:“直觀超出了純粹的現在點,即它能夠意向地在新的現在中確定已經不是現在存在著的東西,并且以明證的被給予性的方式確證一截過去。”[5]這說明美感作為一種當下對形象最直接的直覺感受,貫穿著對過去的認知和對將來的期待。反之,如果沒有以往經驗所帶來的知識,那當下的審美感受也無法完整。故而,審美愉悅往往起于認識,挫于不知。由空間和時間跨越所造成的認知障礙常使我們難以鑒讀某件作品。比如,當中國人讀《哈姆雷特》,西方人讀《紅樓夢》,今天的人讀《楚辭》《離騷》《荷馬史詩》時,如果沒有對作品相關背景的了解和一定的文化積淀,我們看到的也只是一個個文字符號,無法將它們串聯起來去理解其背后深刻的內涵與意蘊。這時,晦澀難懂的感受會阻礙美感的發生。再比如,如果一個人去欣賞《馬背上的戈黛瓦夫人》時,不了解這幅名畫背后的故事,其審美感受的觸發點便只停留在畫面形象以及對人體美的欣賞上。如果他了解到戈黛瓦夫人是為民請愿,自愿裸身騎馬穿城而行,而城中所有百姓都默契地躲避在屋內,令大恩人不至蒙羞,那么他還會只關注那優雅的裸體嗎?他是否會被人類高貴的精神美所震撼?又或者,當他了解到名畫背后的故事后,再度把目光轉移到畫面中戈黛瓦夫人的裸體,很有可能會低下頭不敢直面那圣潔的肉體,生怕對其有所玷污,但是此時他的心中卻涌動著對高尚人格的崇敬與向往。這時,他內心所感受到的美是否會超越起初僅由形象所觸發的美感呢?答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審美能超脫實用目的,但不能超脫認識經驗。審美主體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審美客體的形象,還有貫穿整個形象體系所傳遞出的社會意義。這種認知或許是偏重抽象理性的,并非審美活動的必要內容,但它卻是獲得深度美感的前提。審美主體愈是能深刻認識到形象背后的情理,則愈能強烈感受到形象之美,而這種美的感受也往往愈醇厚而持久。所謂形象背后的意義也并非實際效用的意義,而依然是審美的意義。任何可以被視作審美對象的形象都是人的意識形態下沉的結果。如果脫離社會本義而只單純觀照形象,人們便很難理解形象的意蘊,對形象美的感受也只能流于表面。
另一種方式則是參與式的。這也是從審美觀照中獲得高級體驗的一種途徑,即由形象觀照對審美對象產生情感并與之共鳴。審美作為一種認識,可以說是審美主體由形象感知獲得的對自我的認識。同時,審美主體在感知形象時還會將其視為一種非物體本身的空間意象,借著這一意象打破對象作為他者的屬性區別,與自我聯系起來。主體在直覺感受中化作飛鳥、化為青山,使眼前的形象不再是單純的線條、色彩、光影、明暗等形式的組合,而是與欣賞中的自我產生共情的另一個“我”。此時的審美觀照不僅觀照對象的形象,更觀照自我。
審美心理的這一反題呈現出人能夠于他事外物中尋回自我的特點。所以張若虛會將月亮與思婦的離愁別緒聯系在一起:“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妝鏡臺。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月亮本是無生命的,周轉運行是它的自然規律,何以有了情感意味的可憐與徘徊?原因就在于將婦人思念的情緒代入月亮這一形象上去了。浮云游動,光影莫測,月亮仿佛和自己一樣因難以入眠而踱步徘徊。所思之人遠在天邊,唯有這一輪明月能將二人聯系起來。月光無處不在,就像她的愁怨一樣卷不去、拂還來。此情此景正如喬治 桑在《印象和回憶》中所說的那樣:“我所棲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張出來的。”人在面對形象時之所以能感受到強烈的美,是因為人在形象中直觀了自身。審美共情源于人將審美對象的形象當作自己來看待,是將欣賞者的自我復現于所欣賞的形象之中而產生的情感。“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說的就是白居易在琵琶曲中感懷自身,并與之產生了審美共情,套用王陽明的話來說即是“此花不在我的心外”,無我心便無花開好顏色,無花便無我心樂開懷。在審美感受中,“我”與對象不可分隔,是合而為一的存在。這是人生閱歷所賦予人的審美能力,審美中的人可以在直接呈現的形象中觀照自己,實現自己的價值。這是第一階段難以達到的境界,這時的審美活動實際上是對人生的解說。真正的美感源于對人生的切實觀照,而審美趣味也由此多樣而大觀。

這一階段作為審美心理發展的反題,其內涵一方面在于帶著認識走進形象,透察事物內在本質,形成深刻的審美認知,另一方面則是打破“我”與物之間的隔閡,在審美體驗中觀照自身,并產生共鳴。所以,直覺中的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第二個階段中發生了變化,成為欣賞者性格和情趣的反照,這一變化源于主體審美境界的提升。對同一事物來說,每個人所感知到的形象都是不一樣的。直覺是突然間心里有了一個形象或意象,而這個形象或意象在第二階段被主體的認識和態度加以改造,使得美感經驗不僅是形象直覺,更是審美創造。但是如果一味地沉溺于對事物的理性認知或與自我的聯系之中,又將陷入超形象的概念意義中,或者與自身緊密貼切的現實關系里,而難以獲得審美感受。所以,如何能確保主體心理在審美范圍內活動的同時把握人生內涵,避免因過于傾向其中一方而使美感產生落差,最終體驗到更高級的美感,就是第三階段,即合題需要走的路。
三、合題——審美的距離
審美心理是否能發展完全,對象之美是否能被深刻感受,關鍵在于主體以何種態度來面對眼前的形象。也就是說,主體只有處理好直覺感知與人生觀照之間的矛盾,在綜合的基礎上吸取正反題中的積極因素,才能將自己的心理鍛造為真正成熟的審美心理。審美的境界恰如人生的境界。“看山是山”對等的是審美心理的正題。對形象的直覺是人的認知之始,是人當下瞬間的關注但缺乏對對象和人生本質的深度認識,所以雖然眼前看到了山的形象,但是腦海中只能浮現出作為形象的山。反題則不止于山的形象,因為人已有了理性與現實的思考,會將種種經驗與認知帶入對形象的觀照中。此刻眼前的山也不只是形象的存在,更是一種人生的投射,所以“看山不是山”,而是自我,但是如此往往又會因滑落到現實功用的泥沼中而導致審美感受的落差。合題則需要主體再次回到對山的形象的直覺中,不過此時的人帶著對宇宙、人生的深切觀照,同時又超然于現實功用,明確了審美應是一種關乎切身但又超脫實用地看待形象的精神活動,所以人“看山還是山”。合題就是在明晰對象意義的基礎上重新把目光聚焦于對象形象本身,帶著對宇宙、人生的認知,入乎其內又出乎其外,積極主動地創造由審美感受產生的心理距離。以飲酒為例,普通人飲酒是因為酒能刺激味覺感受,帶給人口腹層面的快感,但是以超脫實用的眼光來看,酒又可以令人忘卻苦悶,進入一個與現實人生頗有距離的理想世界中。“李白斗酒詩百篇”,酒對李白而言是一種媒介,可以帶他逃離現實,進入狂放浪漫的藝術世界,這就是一種審美的態度。飲酒能給人帶來美感,也能讓人擁有創造美的力量,這種超越現實擁抱理想的境界正是人以審美為目的而主動選擇的結果。
所以審美的距離不在于對對象本質意義的無知,也不是以現實功用的目光來看待對象的性質,而是在了解的基礎上主動選擇拋棄現實功利的部分,將對象的意義轉化為審美的前提,而不是審美內容本身。如果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距離太遠則不具備產生美感的可能性,距離太近又會陷入現實情緒中難以自拔,被迫與審美感受相分離。比如,當下一些都市倫理電視劇的創作特點之一就是,在劇中設定一個鮮明的“負面人物”,作為整個電視情節展開的矛盾集合點,其行為成為煽動觀眾現實情緒的導火索。這種情感的激動正是影視制作人想要達到的記憶點和爆款效果。但是他們也從創作的角度把觀眾和對象之間的距離拉得過近,以致很多觀眾越過了審美的界限而離開美感的世界,回到現實生活中。對藝術創作者來說,他將觀眾在生活中極感興趣的話題作為藝術表達的內容,但又不給予恰當的距離來保證美感的發生,完全以集中放大生活中的重大矛盾來觸動觀眾的情緒點。且不說這樣的作品在社會中所產生的影響如何,單就創作出發點來說,明顯就是將作品的成功寄希望于激發觀眾的現實情緒,而非藝術本身。這樣說的目的不在于反對藝術寫實的創作傾向,藝術理應來自客觀現實,但是如何處理現實生活和藝術創作之間的度,觀眾如何把握恰當的審美距離,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以審美為核心的藝術理想理應在適當的距離內,拉近觀眾與對象之間的距離,使觀眾更容易獲得美感,但也不應完全消滅二者間的距離,使美感被實際的欲望與情感所推翻。
當然,這些熱播劇引發的現象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即現實的審美活動往往比設定的應有模式要復雜得多,審美心理發展反題中的種種認知情感都會摻雜于之后的活動中,使主體難以準確界定現實和審美的概念。所以,這個時候從理論邏輯上對審美心理進行梳理與確定就顯得尤為必要了。成熟的審美心理或許有能力將自己從現實生活中適度地抽離出來,向高度相似于現實的對象投以非功利的審美眼光。他也會被對象打動,但仍有意識告訴自己,那是被“我”審美著的對象,而不是“我”所存在的現實,它只是與現實高度相似。所以最理想的審美心理活動是“我見青山多嫵媚”,只有“我”和青山之間有一定距離,才能更好地去觀照它。這個距離不能太遠,否則“我”會完全不知山為何物、不識山色為青。這個距離也不能太近,如果近到超越現實的界限,“我”就會因對其產生恐懼之感而喪失審美感受。這種距離是能夠讓人產生“嫵媚”之感的審美距離,不因山高而讓人想到有墜崖喪生的危險,不因海闊而讓人感到驚恐懼怕。當我們看到它的那一瞬間,只有我們的直覺在感受山與水的形象,不摻雜切身利害的想法,以往的人生經驗只會指引我們體味山川的高聳青翠和碧海藍波之美。
總而言之,一切高階美感的產生都離不開主體積極的審美態度與恰當的審美距離,它是隨著人的審美實踐經驗不斷發展、進化而來的。起初,人以純粹的直覺去觀照形象,進而體悟人生,感受由認知與共情帶來的美感體驗,最終明晰主體態度,找尋適度的審美距離,將審美化為一種積極主動的內在能力,這是審美心理走向成熟的應有命題。所謂成熟的審美心理是人能夠帶著探索人生的結論來觀照對象的形象,既合于現實又超越現實。真正的審美觀照是主客觀的統一,既有“我”又無“我”,既是物又非物。只有經歷“正”“反”兩個階段的修煉與進化,才能達到“合”的境界,終而超脫現實功利,回歸自然本心,把握審美之道。當然,之所以說“正反合”是審美心理走向成熟的應有命題而非必然命題,是因為在現實的審美實踐活動中主體心理雖應如此發展但并不是必然的,如人雖未與審美對象產生共情,但是依然可以獲得對審美形象美的感受,可是如果想要獲得更強烈而深刻的審美滿足,那這種共情就顯得很有必要了。現實中,人們往往難以把握好審美的距離,要么過于實用,要么因為認知不足而過于疏離,使人難以產生美感,更不必說獲得高級的審美感受了。所以,如何使人掌握適度的審美距離,如何培養成熟的審美心理也應成為我們開展審美教育的重要目標。
(孫繼黃/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學系)
注釋:
[1]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1.
[2]朱光潛.文藝心理學[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5.
[3]〔明〕王夫之.船山全書(第十三冊)[M].長沙:岳麓書社,1988:536.
[4]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28.
[5]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56-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