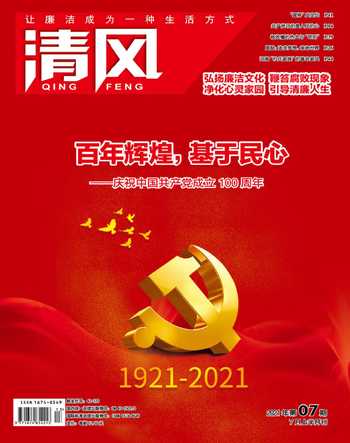圍獵的異變
張樹民
圍獵,自古有之。《周禮》載,君王四季田獵,分別稱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金史·宣帝紀上》云:“戊子,禁軍官圍獵。”最初,圍獵是人類謀生的手段和技能,僅為生存計;自周代至戰(zhàn)國時期,圍獵成為軍事大典,主要圍繞軍事綜合演練進行;兩漢及以后的一段時間,各朝君王將圍獵當作了消遣娛樂;唐代,復將仲冬季節(jié)舉行的圍獵,列為國之重典,屬軍禮之一。
當歷史走進清代后,由東北長白山麓起家的滿人,得益于狩獵練武而強悍,唯恐八旗子弟貪圖安逸,荒廢騎射之術,乾隆朝以前,恢復了狩獵閱軍制度。據(jù)《東華錄》記載,康熙開辟了熱河木蘭圍場,把木蘭秋狝定為年度大典;至乾隆朝,尚能保持“皆因田獵以講武事”,仍將圍獵視為練武之道。之后,木蘭圍場漸漸成為當時王公貴族的娛樂場,僅剩吃喝玩樂功能。而到了咸豐朝,面對英法聯(lián)軍的逼近,居然假木蘭秋狝之名,棄京城而逃,令國格顏面盡喪。
圍獵,無非是將禽獸四面合圍而獵之。或獵殺,或捕捉,剝其皮,褪其羽,食其肉,反正所獲之利,統(tǒng)統(tǒng)歸圍獵者。圍獵,因殺戮,而充滿血腥;被圍獵的禽獸,結局頗為悲慘。但禽獸畢竟是低級動物,不善思維,僅憑本能行事,往往身陷險境并不自知,確屬無奈。
俱往矣。隨著社會文明的進步,圍獵自然界的動物已被法律禁止,傳統(tǒng)的圍獵成為歷史。然而,不知從何時起,圍獵對象發(fā)生根本性異變,一種嶄新的、“更高級”的圍獵形態(tài)殺將出來——圍獵的目標,不再是禽獸,而是直指權力。這種圍獵,已然成為某些人的牟利手段,一旦圍獵權力得手,便可從中牟取到超額利益。
從表面看,圍獵的對象,是極少數(shù)關鍵權勢人物,而且,圍獵的手法往往溫情脈脈,百般殷勤,絲毫不見金戈鐵馬、強弩硬弓、殺戮血腥的影子。弄得被圍獵者也產(chǎn)生錯覺,以為是自身魅力四射,引得四方圍獵者拜服。其實,圍獵者瞪大紅眼緊緊盯著的,是你手里握著的公權力。權力在,有利用價值,則圍獵者聚;權力喪失,失去利用價值,則圍獵者散。善于思考的人類,面對重重誘惑,某些人的智商,變得似乎并不比禽獸高多少,正所謂利令智昏也。
花樣翻新的圍獵手段,招招式式,步步為營,仿若布下隱形的天羅地網(wǎng),倘若沒有強大的定力、堅定的信念,稍有疏忽,就會陷進“圍獵圈”中,甚至誤將“圍獵圈”當作“安樂窩”,在不知不覺間,走上了不歸路。
圍獵的招法,越發(fā)“妙”不可言,在下孤陋寡聞,試舉幾例“拋磚引玉”。
“以情圍獵”:所謂親情、鄉(xiāng)情、友情、愛情,皆能成為“涂蜜的圍獵之箭”,讓圍獵對象品嘗到甜甜的滋味——至親生病,聯(lián)系最好的醫(yī)院,請最好的醫(yī)生;晚輩上學,安排最好的學校;父母、妻子、子女生日,安排宴席,送上禮物;逢年過節(jié),“禮尚往來”等等。以“情”為旗號,讓人推卻不得。
“以利圍獵”:利益輸送,套上“隱形衣”,妙施“變臉術”,轉來繞去,去痕滅跡,“借”給你錢,“借”給你車,“借”給你房;請你試用、試吃、試喝;送“干股”記你指定人名下……表面上似乎入情入理,中規(guī)中矩。
“以權圍獵”:出錢出人出力,拉關系托門路,為圍獵對象升遷鋪路架橋,“搭天線”走捷徑,以獲取更大權力,最終成為圍獵者的代理人,此招的鼻祖乃大名鼎鼎的呂不韋。
“以色圍獵”:俗話說,“英雄難過美人關”,圍獵者利用自身姿色誘之,或借用、雇傭美色勾引圍獵對象,關系套牢,私利自來。
圍獵得手的標志,就是圍獵對象被圍獵者牽著鼻子,以公權力為其謀取私利,拿社會公共利益中飽私囊,以權易權,以權易錢,以權易色,以色易權,并成為常態(tài)化。圍獵者不僅徹底收回投其所好的成本,還會賺得盆滿缽滿。
新型圍獵的破壞性極強,被圍獵絞殺的那些人也甚為可悲。但是,被圍獵者拉下水的畢竟是極少數(shù)。也就是說,防止被圍獵完全可以做到,關鍵就在自身。規(guī)矩要守,底線莫破,破了底線,必墜深淵。切記“日三省乎己”,時刻默念公權力姓公,它的主人是人民,堅定信念,慎權行遠,濫權入監(jiān);切記“踏實做人,清白做官,干凈做事”的警言,并辨明虛情假意,“拒圍獵,永不貪”,踐行不輟,必能修成金剛不壞之身。當然,出重拳打擊圍獵者,也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