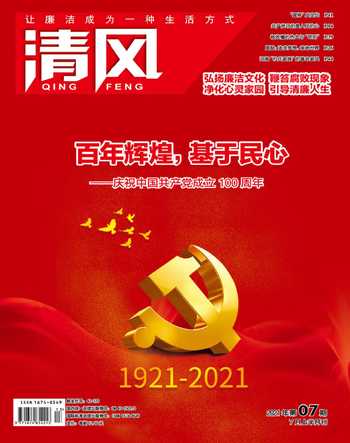須面對“紙面服刑”背后的層層拷問
黃磊

經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政法委、紀委監委等多個部門聯合調查,備受矚目的巴圖孟和“紙面服刑”案成因水落石出。目前紀檢監察機關已認定84名責任人,其中廳級干部8人,處級干部24人,科級干部33人,其他干部9人,已故10人;已給予黨紀政務處分54人,其中10人涉嫌違法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調查處理,給予誡勉談話等組織措施處理20人。
巴圖孟和“紙面服刑”案,最早是《半月談》于2020年9月3日曝光,案件一經曝光便引發社會高度關注:1993年,內蒙古呼倫貝爾男子巴圖孟和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有期徒刑15年;但他非但未服過一天刑,此后還當選嘎查達(即村主任)、旗人大代表,并蒙混入黨……離奇而難以理喻的種種疑問,經歷了28年方得到徹查。遲到的正義背后,我們更須正視“紙面服刑”背后的層層拷問。
其一,保外就醫緣何成為法外逍遙的通道?
保外就醫制度的初衷,是為患有嚴重疾病的罪犯提供人性化關懷,是人道主義和人性化司法的體現。由于是監外執行,對保外就醫條件要求更加嚴格。一方面疾病要較為嚴重,如短期內有死亡危險,或身體殘疾、生活難以自理,或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會可能;另一方面部分保外就醫有刑期要求,“原判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后減為無期徒刑的罪犯,從執行無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執行原判期限(已減刑的,按減刑后的刑期計算)三分之一以上(含減刑時間),患嚴重慢性疾病,長期醫治無效的”。然而,巴圖孟和親屬打通當地醫院、看守所、檢察院、政法委、公安局的關系,最終為巴圖孟和一路綠燈,縱虎為患。
其二,事后監管為何層層失控?
按照當時的《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等相關規定,保外就醫罪犯病情基本好轉,監獄應收監執行;經縣級以上醫院證明尚未好轉的,應由監獄提出意見,經省、自治區、直轄市勞改局批準才可以辦理延長保外就醫期限手續,并且要及時通知當地公安機關和人民檢察院。
而根據事后調查,巴圖孟和“保外就醫”期間,在陳旗巴彥庫仁鎮等地居住、生活。陳旗看守所未按規定向相關司法機關送達保外就醫相關法律文書,未履行保外就醫考察、續保、收監等職責。屬地派出所未履行重點人員管理職責,未采取監管、列管措施;陳旗檢察院未履行檢察監督職責;擔保人佟拉嘎、朝魯門未盡擔保人義務,導致巴圖孟和長期脫管漏管。
其三,豈能違規入黨當村官?
且不說巴圖孟和是一個背負故意殺人罪案底的人,就從尚在服刑的角度來說,無論是嘎查達的任職要求、人大代表的選舉要求還是共產黨員的發展要求,巴圖孟和都遠遠達不到標準。然而相應的組織程序、核查程序也成為擺設,以至于巴圖孟和未經黨支部培養考察、大會討論決議和蘇木黨委集體討論表決的情況下,違規辦理入黨手續,同時還違法當選人大代表、違規當選村主任,種種行為難免令人咋舌。
司法是社會最后的底線,倘若刑事審判結果流于紙面,不僅讓被害人家屬無法感受到公平正義,同時也讓當地的刑事司法體系顏面掃地,更因此在社會失去應有的公信力。同樣,制度的生命力在執行,當黨紀黨規成為擺設,甚至連犯有故意殺人罪、尚在服刑的人員都可以混入黨員隊伍,那基層組織的形象和權威無疑會因此大打折扣。
更令人深思的是,“紙面服刑”案并非私密行為,巴圖孟和的堂而皇之,被害人母親韓杰連續25年來的申訴無門,甚至被啐口水侮辱,這些以往的新聞細節無疑持續刺激公眾的神經,即便調查結果已經公布,卻依舊令人難以釋懷。
當然,隨著法治的進步,無論是檢察機關對刑罰執行和監管活動的監督,還是幾年來所陸續開展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專項活動等等,都在對以往司法執法中的漏洞進行彌補。所謂“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紙面服刑”案也讓我們更加深刻理解當前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深刻理解全面從嚴治黨的跨時代重大意義,并希望時刻銘記“紙面服刑”案的層層拷問,營造海晏河清的司法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