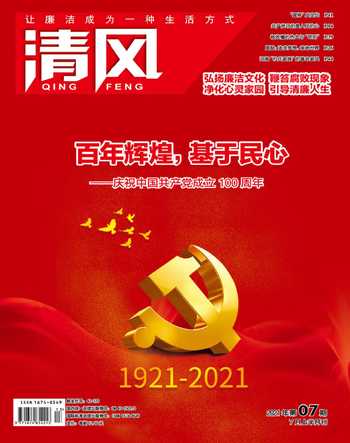為官力求“三不欺”
陳良
“三不欺”典故,出自《史記·滑稽列傳》,在記述西門豹故事之后,褚少孫評論道: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
中國古代官吏通常以實現民眾服從為施政目標。不欺,意即不欺騙,還包含信服、服從之意。所謂三不欺,也就是從三個維度或以三種方式令民眾信服、不欺騙。那么,子產、子賤和西門豹如何令民眾信服、不欺呢?
子產,春秋時期鄭國人,系鄭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先后輔佐鄭簡公,鄭定公。鄭簡公三十年(前536年),在子產主持下,“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公布法律,開創了中華成文法之先河。此前,周王朝及諸侯國雖有法律,但卻是秘密的,沒有公布于眾,意在“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子產讓法律公開透明,破除司法神秘化的傳統,既有利于國人知法守法,也有利于促進官員依法辦事、公正司法。
子產執政期間,積極推行諸多經濟改革措施,為民求生,為國理財。他選賢任能,知人善任,做到人盡其才。他集思廣益,妥善決策,所有公文或政令都經過草擬、征求意見、修改完善等程序把關方可出臺。最難能可貴的是,子產虛懷若谷,開放言路。鄭國人到鄉校休閑聚會,喜歡議論執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壞與得失。大夫然明建議把鄉校廢除。子產卻對然明說:“人們在早晚勞作之余到鄉校聚一聚,議論一下時政何嘗不可?他們認為好的就推行;他們所討厭的就改正。這是我們的老師,為什么要毀掉它呢?”子產開明豁達,能使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有錯必糾,有弊必除,老百姓心悅誠服,自然不能欺騙了。
子賤,春秋末期魯國人,是孔子的得意門生,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子賤注重修身,品德高尚。子賤曾經出仕,擔任魯國單父宰(地方官)。在任期間他很少走出公堂,成天悠閑自在,彈琴取樂,卻把單父治理得很好。同為孔子學生的巫馬期也曾擔任單父宰,任期內披星戴月,早出晚歸,事必躬親,日夜操勞,這樣才把單父治理好。巫馬期向子賤探詢為官心得,子賤坦言道:“我的辦法是借用眾人的力量,你的辦法是任用自己的力量。任用自己力量者必然勞苦,借用眾人力量者自然安逸。”子賤知道個人力量有限,所以,子賤授權予賢能者,借用這些外腦與外力打理政務,從而實現“鳴琴而治”。
西門豹,是戰國時期魏國人,擔任過魏國鄴縣縣令。上任伊始,西門豹會見當地年長者,詢問民間疾苦。了解得知,基層官吏與巫婆神漢勾結,假借“為河伯娶婦”騙取錢財坑害女子,致使百姓苦不堪言。于是西門豹將計就計,等到河伯娶妻的日子,西門豹以所嫁之女不美為借口,要向河伯請示,把巫婆神漢和鄉吏相繼扔進河里去稟報。扔進河里的人都沒有上來,在場官吏與民眾萬分驚恐。西門豹乘勢而為,頒布律令,禁止巫風,這個禍害百姓的陋習被一舉廢除。西門豹治鄴,快刀斬亂麻,以重典懲治歪風邪氣,興利除弊使民眾得實惠,故而百姓不敢欺騙他。
習近平總書記曾在瑞安市基層干部座談會上指出:西門豹治鄴是大家熟悉的故事。這個故事里面講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子產是春秋時人,他治理鄭國,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騙他。子賤是孔子的學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鳴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騙他。西門豹是戰國時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現,不站在百姓的對立面,順利革除“為河伯娶婦”的陋習,帶領百姓興修水利,用重典治亂世,百姓不敢欺騙他。這些道理對于我們加深理解干群關系,不斷改進工作方法不無裨益,應該好好體味。
總書記這番話言簡意賅、意味深長,黨政干部應當深入學習,融會貫通。現在看來,子產是善治與開明的典范,官民之間良性互動,就不至于相互欺騙。子賤是德治與委任的典范,關鍵在于他所選用賢能之人,施行仁政純化風俗,讓百姓不忍欺騙。西門豹是寬嚴相濟的典范,對待禍害一方的黑惡勢力嚴厲打擊,絕不心慈手軟,對于百姓則因勢利導,為他們興利除弊,百姓當然不敢欺騙他。
如果我們干部能夠借鑒“三不欺”的經驗,切實改進工作方法,必定能處理好干群關系,從而同心同德,同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