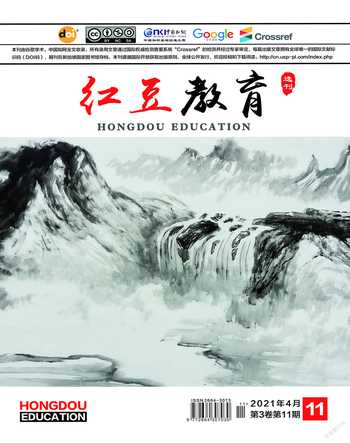動畫改編電影的表演風格探析
張洋
【摘要】本文以電影《花木蘭》為例,在表演風格的系譜這一大背景下,探討動畫改編電影的表演風格,并對該類型的電影表演風格進行反思。動畫改編真人電影的表演風格是具有一定的挑戰。這一方面是來源于動畫電影本身的特征所決定的,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動畫人物與真人演員對于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演員在把我人物時應該采用不同的方式,而非模仿或照搬動畫人物固有的視覺形象。
【關鍵詞】動畫改改編電影;表演風格;花木蘭
2020年迪士尼的動畫改編電影《花木蘭》,無論是視聽語言還是主題表達都非常的貼合當下的時代,然而電影的票房表現并不理想,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動畫改編電影對于演員表演的要求尤其的高。本來電影題材類型的不同對演員表演方式就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例如,在文藝電影中演員的表演要求含蓄、自然、貼近日常,而在類型電影中演員的表演卻要求展現充分的戲劇性。較前者而言更夸張、更具有表現力。更不用說在后現代主義戲仿、解構的電影作品中,演員表演會打破“第四道墻”直接與觀眾進行互動。這又是表演風格中另一個維度的展現。因此,某一電影類型與演員的表演風格應該高度協調。而在《花木蘭》中,這種形式與風格的錯位造成了電影在接受層面的不適。
一、表演風格的系譜
概括而言,最主要的表演風格分為兩大派系,一是強調沉浸效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流派,二是強調間離效果的布萊希特流派。前者強調演員對角色的沉浸式體驗,以此為基礎傳遞出自然、直接、透明的表演效果。這有利于加強觀眾的沉浸效果,尤其是在電影裝置理論的研究中,觀眾以想象的方式參與到熒幕中呈現的故事世界里。演員的表演越是自然、透明,觀眾的代入感與娛樂體驗就越是強烈。后者強調觀眾在鑒賞藝術作品的時候所產生的一種反思,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布萊希特認為,沉浸的文藝作品似乎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謊言掛鉤。他強調好的藝術應該給觀眾留有反思的空間,因此,他主張打破“第四面墻”。演員或人物不再假裝自己在一個純粹、孤立的空間中進行藝術創作。這兩種表演風格拉出了一道表演風格的系譜,他們分別居于系譜的兩端,而中間是各種各樣的混合形式。以現實主義題材的電影作品為例,演員通常是根據具體的情境,具體的人物心理狀態做出情緒反應。這傾向于沉浸一端,而如武俠片這種類型電影,表演風格上存在著固定的程式。人物的所思所感,讓步于類型程式的固有特征。具體而言,武俠片中的人物,有特定的肢體語言與面部表情來表達某一種情緒。而表演的狀態無非也是在喜怒哀樂這幾種典型的情緒中切換,不如現實主義題材那么細膩、豐富。
電影《花木蘭》屬于古裝武俠類型,其表演風格,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如傳統武俠片中主人公快意恩仇、忠肝義膽。所以其表演風格也有固定的模式,然而,這與動畫改編電影的表演風格又有一定的反差。
二、動畫改編電影的表演風格
動畫電影的優勢和長處便在于動畫能夠再現現實生活之中無法呈現的影像,他們要么是展現豐富的想象力,要么是展現夸張的喜劇效果或戲劇效果。《花木蘭》動畫電影即是如此,動畫人物的表情及其肢體動作都異常夸張,以求達到一種喜劇效果。
然而動畫電影的成功也給觀眾留下了既定的印象,即花木蘭這一文化符號在與社會的溝通中奠定了一個夸張而具有喜劇內核的形象。這給真人改編電影提出了一個難題。首先,面臨著電影本身的風格定位問題。《花木蘭》的主題講究的是一個忠孝之間的權衡故事,而非以喜劇、打鬧為主。但真人電影又不能像動畫電影一樣,通過肢體夸張的變形來制造喜劇的效果。這就給電影的核心表達帶來一個窘境,所以我們能看到《花木蘭》真人電影在忠孝主題的同時,與當下社會呼聲漸高的女性主義勾連。而沒有承接動畫電影的固有基調。這在觀眾的印象當中勢必會形成一定的反差。其次,真人改編電影與動畫改編電影不同之處,就是觀眾“假裝相信”的門檻不同。這跟戲曲與電影的對比類似。在戲曲中,主人公在舞臺上轉一圈能夠表達奔襲十萬八千里,而在電影中,這種程式化的程度要低很多,觀眾相信眼見為實。所以,《花木蘭》動畫電影中的戰爭場面能夠以幾個主要的人物形象代表一場數萬人的戰爭。而在真人改編電影中,這樣的場景呈現則顯得不太可信。這也是觀眾為什么詬病花木蘭的戰爭場景極其出戲的主要原因。最后,對演員的表演來講,動畫改編電影也十分難駕馭和把握。因為動畫原作的表演方式可以不受物理世界的束縛。觀眾在接受層面也傾向于相信,但當真人扮演動畫人物的時候,表演方式就不那么好拿捏了。一方面,如果以現實世界的情緒反應作為參照,那么觀眾會抱怨情緒不強,戲劇性不夠、喜劇效果不佳。但同時,如果以動畫人物的表情作為參照,則演員的表演又會顯得很僵硬、極不自然。演員劉亦菲作為花木蘭的扮演者,清秀的五官本來就缺少一份颯爽之氣,再加上動畫改編電影在表演上的困難之處,所以顯得該片看起來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三、動畫改編電影表演風格的在思考
近年來,動畫改編電影活躍在大眾的視線中。曼諾維奇認為,電影的原初形態就是動畫,他將電影的歷史追溯到前電影時期,手工藝人直接在膠片上作畫的情形,將當下無所不能的數字技術試做對動畫電影的回歸。的確,數字技術掙脫了影像再現現實的情況,能夠繪制出不同程度的想象。從這個角度而言,動畫電影才是電影的正統,而非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因此,動畫電影也呈現出其自身的某些特征。首先,動畫電影不是再現,而是表現,是創作者對現實世界的主觀呈現,是一種毫不掩飾的藝術加工。所以我們能看到,動畫電影呈現出夸張的特征,例如,人物的變形、時空的變形,甚至于事件邏輯的變形。它的目的并不是通過影像勾起觀眾的經驗,而是通過變形的處理手法帶來觀眾認知上的誤差,從而達到某種喜劇效果或戲劇效果。那么對于動畫改編電影的表演風格而言,演員則應該更多的發揮自身的表現力,而非一味的遵循動畫原作的夸張效果。況且,在真人電影中,情緒的強度與沖擊并不一定要靠表演的面部表情呈現。演員應該加深對動畫原作主題內核的理解,而非外在形式的模仿,以真人的方式,通過肢體語言、面部表情、眼神神態、精神氣質,以現實邏輯的方式呈現動畫原著的主題。
其次,動畫電影除了是對現實世界的變形以外,它還是對現實世界的某中簡化,影像與動畫不同,影像能夠無差別的呈現現實世界的所有細節,包括創作者有意或無意呈現的內容。而動畫電影則不同,動畫電影的畫面內容每一個部件都是創作者有意呈現的。但是,無論創作者多么仔細或還原現實,他都不如影像對畫面細節的極致還原。因此,動畫電影的現實主義是一種抽象的現實主義,是對現實的一種印象,是對現實的一種表現。從根本上講,真人改編電影比動畫原作應該具有更加豐富的工具和手段類似塑造人物形象。因為真人演員的細膩表情和瞬息萬變的神態變化是再先進的數字技術都無法企及的,所以,真人改編電影不必固步自封,從源頭上束縛自己的可能性,在表演風格上趨同于動畫人物。而應該用更加豐富的細節,豐滿動畫人物,使之更能夠觸及觀眾的情感經驗。
最后,動畫電影的主角不受現實邏輯的束縛。蒙太奇表現方面要豐富的多。因為動畫電影能夠實現在任意場景之間切換,而不受物理世界的時空束縛。電影蒙太奇某中程度上來說,也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但是這也是建立在觀眾對完整的時間、空間感受之基礎上的。動畫改編的真人電影創作上失去了這種任意連接的自由度,并不是一個不利的因素,反而能夠刺激演員專注于當下的情節脈絡,此時此地的情緒反應,更加聚焦于此情此感。
綜上所述,動畫改編真人電影的表演風格具有一定的挑戰。這一方面是來源于動畫電影本身的特征所決定的,而另一方面也在于動畫人物與真人演員對于故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應該采用不同的方式。動畫改編電影不應該模仿或照搬動畫人物固有的視覺形象,而應該發覺演員本身的情緒表達,以更好的幫助觀眾進行認知建構。如果說動畫原作與動畫改編電影放到表演體系里面,動畫原作的位置比較傾向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而動畫改編電影則可能處于中間地帶,創作者應該拿捏好這個度。
參考文獻:
[1]嫣然.從《花木蘭》看迪斯尼的真人電影生意經[N].經濟觀察報,2020-10-12(038).
[2]蘭超歌.跨文化傳播視角下中美電影《花木蘭》的敘事方法研究[J].戲劇之家,2020(33):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