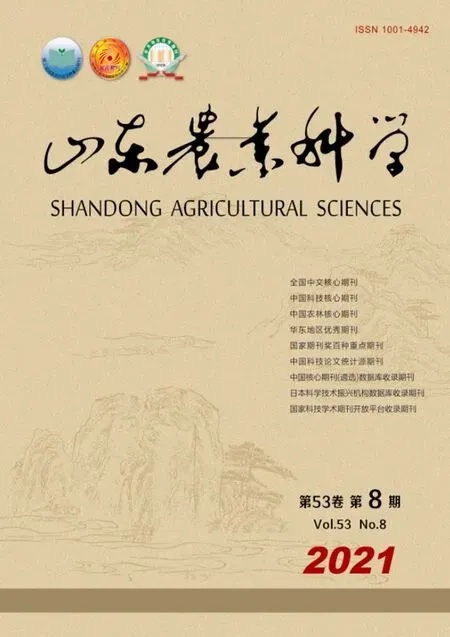阿特拉津脅迫對谷子種植區土壤真菌群落的影響
蔡穎慧,黃瀟,趙小珍
(1.山西省生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省科技資源與大型儀器開放共享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農藥的使用大幅減少了病蟲害的發生,但農藥的廣泛使用也是導致生態環境污染、土壤生物學質量退化的最重要人為因素之一。農藥污染不僅改變了土壤的理化性質,導致土壤酸化,而且對土壤微生物、土壤質量和可持續利用具有嚴重危害[1,2]。土壤真菌是土壤生態系統的重要組分之一,具有分解有機質、土壤酶釋放、抑制病原菌等重要作用,是土壤中氮、碳循環的必要動力。真菌可降解復雜化合物,與作物共生形成菌根,對促進植物生長、維持農業生態系統的穩定具有重要意義[3,4]。
阿特拉津又稱莠去津,是一種內吸選擇性苗前、苗后除草劑,可防除多種一年生禾本科和闊葉雜草,對某些多年生雜草也有一定抑制作用。由于阿特拉津殺草譜廣,價格低廉,使用效果好,在很多國家被廣泛應用于玉米、甘蔗、果樹及谷物類作物生產中,是世界產量最大的除草劑之一。阿特拉津的結構比較穩定,降解速度緩慢,其在土壤中的殘留半衰期為28~440 d。已有研究表明,阿特拉津可明顯降低土壤真菌的數量,對土壤真菌功能多樣性和遺傳多樣性產生影響[5-8]。近幾年來,高通量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大大拓寬了微生物的研究范圍。Illumina MiSeq第二代測序技術,可以更直接地檢測微生物類群,廣泛用于醫學、農學、食品等領域[9-11]。樣本的多樣性分析可反映微生物群落的豐富度和多樣性。
目前對阿拉特津的研究多集中在降解方面,關于其對土壤中真菌多樣性的影響少有研究。本試驗通過構建不同污染濃度的土壤模型,采用高通量測序技術,揭示阿特拉津對山西谷子種植區土壤真菌群落的影響,為進一步探討農藥對土壤真菌群落結構的影響提供基礎,對黃土高原谷子種植過程中阿拉特津用量及使用后土壤生態環境修復具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區概況
試驗地位于山西省陽曲縣定點試驗田,地勢平坦,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年平均氣溫6~9℃,年平均降水量為441.2 mm,無霜期為164 d左右。土壤類型為山西黃土,供試作物為谷子(Setaria italica)。
1.2 試驗方法
1.2.1 試驗設計 采用裂區試驗設計,共4個處理,每個處理重復3次,每個重復小區面積為33 m2。2017年6月上旬至7月上旬、谷子3~4葉期用38%阿特拉津水懸浮劑噴霧兩次,藥劑用量為2、5、8 L/hm2,對照處理噴施清水[12]。
1.2.2 土壤理化性質測定 2017年9月,采用五點取樣法采集2~20 cm表層土樣。過2 mm篩子,去除雜草、碎石等雜質,4℃保存待用。部分土樣自然風干,用于土壤基本理化性質測定。每個樣品3次重復。土壤pH測定采用酸度計法;含水量測定根據國家標準LY/T1213—1999(烘干法);有機質的測定采用重鉻酸鉀消煮-硫酸亞鐵滴定法;有機氮的測定采用Bremner酸解法;有效磷的測定采用浸提-鉬銻抗比色法;速效鉀的測定采用原子吸收火焰光度法[13]。
1.2.3 土壤DNA的提取及ITS基因測序 稱取0.5 g土壤樣品,采用基因組DNA快速抽提試劑盒[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提取土壤DNA;得到的DNA溶解于50~100μL TE Buffer中,-20℃保存。選擇ITS2可變區,以5~50 ng DNA為模板,PCR擴增真菌ITS rDNA。使用2%瓊脂糖凝膠進行PCR產物電泳檢測,膠回收試劑盒回收產物。構建DNA文庫,Qubit和實時定量PCR檢測合格后,通過Illumina MiSeq上機測序[14]。
1.3 數據分析
對高通量測得的序列進行聚類,以97%的相似度將序列歸為同一分類操作單元OTUs(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ITS rDNA進行比對(參考數據庫是Unit數據庫:https://unite.ut.ee/),然后對OTUs的代表序列進行物種注釋分析(Ribosomal Database Project),確定ITS2序列對應真菌,并分析不同物種分類水平下各樣本的群落組成。基于OTUs的分析結果,對樣本序列隨機抽樣,采用Qiime 1.9.1計算土壤真菌α多樣性指數(Chao1、Shannon、ACE等)。原始數據利用Galaxy平臺(http://mem.rcees.ac.cn:8080)進行分析,以獲得土壤微生物群落優勢類群的相對豐度[15]。
2 結果與分析
2.1 供試土壤理化性質
由表1可知,4種處理的土壤pH值無顯著差異;除5 L/hm2處理的速效鉀含量外,噴施阿特拉津的土壤含水量和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機氮含量均低于對照。

表1 供試土壤理化性質
2.2 土壤測序結果及真菌α多樣性分析
由表2可知,測序共獲得325 110個真菌有效序列,依據97%的相似度,真菌OTUs數為358~502。本次測序的覆蓋率均在99%以上,說明測序結果較好地反映了土壤樣本中真菌群落組成的真實情況。對照土壤獲得的OTUs數目最多,其次是2 L/hm2和5 L/hm2,8 L/hm2的最低。Chao1指數表現為對照>5 L/hm2>2 L/hm2>8 L/hm2,ACE指數表現為對照>2 L/hm2>8 L/hm2>5 L/hm2,結合Shannon指數和Simpson指數可知,隨著阿特拉津濃度的增加,土壤真菌多樣性降低,物種豐富度降低。

表2 不同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真菌α多樣性指數
利用Venn圖統計多個樣本中的OTUs數,可以直觀地顯示噴施不同濃度阿特拉津后土壤真菌組成的差異性和重疊程度。4種土壤樣本共有的OTUs數為138個,占各土壤樣本的27%~39%。4種土壤樣本特有的OTUs數目及其所占比例分別為對照86個(17.13%),2 L/hm268個(14.95%),5 L/hm249個(13.14%),8 L/hm221個(5.87%)(圖1)。這表明噴施不同濃度阿特拉津土壤間真菌群落組成相似,但仍存在部分差異。

圖1 不同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真菌Venn圖
2.3 不同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真菌群落組成
由圖2可以看出,土壤真菌主要門類為子囊菌門(Ascomycota)、接合菌門(Zygomycota)、擔子菌門(Basidiomycota)、壺菌門(Chytridiomycota)和球囊菌門(Glomeromycota),5個門的相對豐度分別為61.9%、12.5%、6.8%、1.9%和0.9%,未明確分類真菌(unidentified)也占有較高比例(16.2%)。阿特拉津處理組與對照組相比,接合菌門相對豐度變化不大;擔子菌門和球囊菌門的相對豐度在對照土壤中高于噴灑阿特拉津的土壤。在黃土高原谷子種植區,子囊菌為土壤真菌的優勢菌門。對照土壤以及噴灑濃度為2 L/hm2阿特拉津的土壤中子囊菌門相對豐度大于5 L/hm2和8 L/hm2的土壤;對照土壤中真菌多樣性更為豐富。未明確分類真菌中,相對豐度表現為對照<2 L/hm2<5 L/hm2<8 L/hm2。

圖2 土壤真菌門水平下優勢物種的相對豐度
為深入研究不同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真菌群落物種組成情況,進一步考察了樣品中土壤真菌在綱水平和屬水平的優勢物種相對豐度。如圖3所示,4種土壤樣品中真菌綱水平的優勢物種主要有傘菌綱(Agaricomycetes)、糞殼菌綱(Sordariomycetes)、座囊菌綱(Dothideomycetes)、錘舌菌綱(Leotiomycetes)、散囊菌綱(Eurotiomycetes)、絲孢綱(Hyphomycetes)和球囊菌綱(Glomeromycetes)。4種土壤樣品中,傘菌綱的相對豐度最高,占所有真菌綱的18.6%~27.7%;其次為糞殼菌綱,相對豐度占所有真菌綱的14.7%~19.1%;真菌綱水平下優勢物種相對豐度對照>2 L/hm2>5 L/hm2>8 L/hm2。

圖3 土壤真菌綱水平優勢物種的相對豐度
各土壤樣品中真菌優勢屬的相對豐度如表3所示。噴施不同濃度阿特拉津的土壤真菌屬水平的相對豐度差異顯著,10種優勢屬絕大部分屬于子囊菌門。4種土壤樣品中,青霉屬(Penicillium)、曲霉屬(Aspergillus)相對豐度最高,可達到11.71%~20.22%,其次是擬青霉屬(Paecilomyces)。土壤真菌優勢屬相對豐度均隨著阿特拉津濃度的增高而降低,但是在較低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中漆斑菌屬真菌相對豐度會有所提高,2 L/hm2阿特拉津脅迫下,土壤中漆斑菌屬真菌相對豐度可達1.86%,5 L/hm2條件下為1.06%,而對照組、8 L/hm2條件下分別為0.08%和0.05%。

表3 土壤真菌優勢屬的相對豐度 (%)
3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結果表明阿特拉津脅迫會導致土壤含水量、有機質、有效磷、速效鉀、有機氮等理化性質改變。目前相關研究已證實,除草劑的長期使用對速效磷、速效鉀、速效氮、有機質含量均有影響,而土壤理化性質改變又會進一步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16-18]。對照土壤真菌多樣性指數高,說明對照土壤中真菌多樣性更為豐富。分析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對照不噴灑阿特拉津,雜草生長相對旺盛,更具有多樣性。雜草是加強地上地下生態系統的密切聯系者,雜草多樣性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土壤碳氮比,從而進一步影響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19]。另一方面,由于避免了農藥的使用,本身降低了農藥對土壤部分真菌的毒害,使其能夠更好地利用土壤中易降解部分及養分,從而促進其增殖,同時間接影響其他土壤真菌[20]。
在低濃度阿特拉津脅迫下,谷子種植區土壤中漆斑菌屬真菌相對豐度有所提高。漆斑菌多寄生、腐生,能夠產生膽紅素氧化酶,在受到環境污染后可產生應急反應,導致活性增加。較低濃度的阿特拉津誘導漆斑菌活性的提高,從而提高了漆霉菌屬在土壤中的優勢度和生態位,增加了其相對豐度[21]。
在一定范圍內,阿特拉津噴灑濃度越高,土壤真菌豐度和多樣性越低;阿特拉津可導致土壤中真菌的豐富度和群落多樣性降低,但不會改變土壤中優勢真菌種類。本研究可為今后探討除草劑對土壤及真菌群落結構的影響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