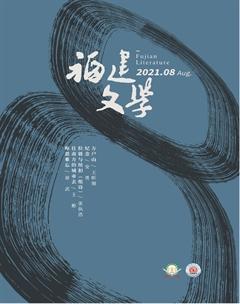卷首語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一個饒有意味的現象。對于每個月、每年新鮮出爐的成千上萬的當下小說(指嚴肅文學),評論家筆下的評價和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頗有一點南轅北轍、背道而馳的味道。同一個文學現場,卻被描述成讓人一驚一嘆的兩種眾生相:一面贊嘆“佳作連連”,一面抱怨“不堪卒讀”。孰是孰非?孰實孰虛?
翻開文學報刊的評論欄目,評論家的慣常話語我們耳熟能詳,比如:鄉土小說的史詩書寫、一部現實主義的力作、驚心動魄的命運交響、清新質樸的語言之美、日常生活的向善表達、用充沛的生活氣息打動人,等等,這些詞句勾勒出一幅小說創作的收獲勝景圖。而在普通讀者——真正的小說消費者——那里,傳來的卻是另一套話語:現在讀小說沒有快感、很多語言磕磕巴巴、故事及其走向基本爛大街、小說中世俗的非凡性沒有了更談不上神性、教條化的現代或后現代移植過來沒有高明之處和改造之新、沒有感覺到小說家對于人的溫度和小說對于現實的干預、純粹一個人的囈語,等等。兩類讀者,兩種截然相反、針鋒相對的評價。誠然,世界上的樹葉都沒有兩片相同的,何況人的觀點、看法呢。對于當下小說觀感的迥異實屬正常,或許兩種觀感的得出可能出于某種小概率閱讀的判斷,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哪一種看法更趨近真實?那些首肯的評論和那些否定的感受,從閱讀的純粹性和受眾面來說,我們以為后者的看法更值得我們反思和警惕:我們的小說寫作是否如普通讀者所說的那樣,正陷入內卷和疲態之中?
本期“重點推介”推出知名小說家王昕朋的中篇《萬戶山》,評論家曾攀認為《萬戶山》“談的是當代中國的社區治理問題,其中體現出敘事文本內外層面的群治關切”,小說“具體而微同時又客觀宏闊”。安勇的短篇《紀念》用簡練的敘述寫了一個內在復雜的故事:照顧生命即將到達終點的爺爺,爺爺死后房子留給孫子結婚,是希望爺爺快點死呢還是希望爺爺完成自己的夙愿?著名詩人張執浩亮相“詩歌頭題”,帶來佳作《拉鏈與紐扣》。從這期開始,新辟兩個新欄目,一是“百名詩人致敬百年華誕”,二是“《福建文學》70年”。兩個欄目均與兩個時間節點有關,前者為慶祝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后者為慶祝我們雜志創刊70周年。天地同慶,歌以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