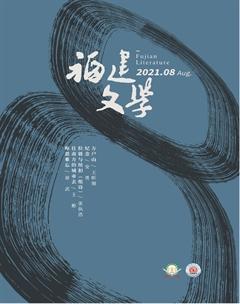無從理解,只可印證
陸源
深邃的真知灼見,往往難以理解,而只可印證。如今,歲月的流逝、多年的磨煉使我越來越確信,瞬間的靈感有賴于長期躬行踐履的不懈累積。幾天前,我剛把老布克哈特的兩句話選為座右銘,放置于書案上:“背景乃首要考慮之因素。它由文化史來提供,而這正是我想獻身的事業。”要解釋史學家此番言論需耗費太多唇舌,欲使庶眾抽象地認同它則更無指望。我們總在力圖領悟文字的真義。然而,最精微的思想盡管確實保存于詞句之間,卻很難無損地傳達到任意心靈的深處。進入本文主題之前,不妨再舉一例,容我援引另一位大家的句子。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于《散文理論》中寫道:“突轉——是忽然改變對正在發生的事物之態度。”當初,第一次讀到這個句子,我并無特殊感觸,甚至沒留下什么印象。時隔五年,我已經寫完一部長篇小說,回頭再看,聯想到其間吸收且運用的諸派方法、技藝,并與意義、形象和詞語共同經歷了遠航之后,才朝徹見獨,才終于敢說:“原來如此,我懂了。”
先是信任,繼而錘煉詩藝,期待最終的印證。一如我們在青年時代決定走上創作之路,那么為創作而學習,同樣要有足夠的機緣和耐心,它們屬于同一場莊嚴而殘酷的賭局。T.S.艾略特的《個人傳統與才能》《批評的功能》及《古典文學和文學家》等文論所闡發的觀念,揭示的技法,情形亦復如是。可能在大多數讀者眼里,它們過于冷峻,不食人間煙火。拋開當時英國批評界的復雜爭斗,拋開《個人傳統與才能》《批評的功能》試圖搭建的文學批評的形而上學,跳過《古典文學和文學家》關于批評之效力的喋喋不休,或許,將來有一天,某位讀者會興奮地發現,T.S.艾略特其實是在為他、為下一代作家和詩人而書寫。從本質上說,作者堪稱一位博大精深的教育家。他開宗明義,意圖昭然可見:“我不談文學教學,只談打算從事文學創作的人們,應如何學習文學。”所以關于他提到的“傳統”和“批評”,及其延伸出來的原則、推論,普通讀者怎樣看待它們都無關緊要,但對于矢志寫作之人而言,這是走向創作荊棘路的岔道,是體現不同文藝期待的斷然分野。
在《個人傳統與才能》里,艾略特寫道:“我的學說要求詩人具有達到荒謬程度的大量學問。”進而“一個藝術家的進步……意味著不斷的個性消滅”。又在《批評的功能》中展開說:“這樣的人方有余力進行協作、交流、做貢獻,他有如此多的東西要給予別人,以至于在作品中能夠忘掉他自己。”
聽起來頗為另類。毋庸諱言,艾略特建立了一套很容易招惹嫌怨的理論,如果不考慮他本人的詩名威望,初學者幾乎沒膽量予以相信。今天,我已不再糾結于應否以“創作美學”來稱呼它,不再急于為之辯解。但投身寫作十幾年后,我愈發懂得,即使艾略特的批評不是通往藝術的唯一途徑,也肯定是一條正路。當然,堅持走下去并不容易。
他號召作家去掌握各個時代的各方面知識。《古典文學和文學家》談道:“真正的文學頭腦可能成長得很慢,它需要更全面和更多樣的食糧:關于各種事實的更龐雜的知識,對于各種人物和各種思想更廣闊的經驗,文學頭腦比從事其他行業所要求的頭腦更急需上述這一切。”
巴勃羅·聶魯達則說:“我要繼續使用自己所擁有的素材,并以我本人為素材展開寫作。我是雜食動物,吞食感情、活人、書籍、事件和斗爭。我真想把整個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可否讓作品成為文學傳統與世間物象的交匯點?聰明人立刻想到,這么做得甘冒風險。創作者盡管初衷極好,依舊難免迷失在參差多態的現實和過去之中,而作品將淪為一些社會新聞或史料的大雜燴。于是,接下來,我們開始接觸到第一個神秘的概念“事實感”。《批評的功能》指出,批評家必須具有高度發達的事實感。不妨說,在艾略特的體系里,創作和批評實乃一體,創作的過程同時即為運用批評手段的過程,但我們姑且將論證放一放,先借用其成果,回到事實感的探討上來。“它絕不是一種微不足道的或常見的才能,也不是一種容易贏得大眾稱贊的才能。事實感是一個需要很長時間方可培養起來的東西。它的完美發展或許意味著文明的最高點。”那么,事實感究竟為何物?恐怕它同樣無法理解,而只需印證。僅從功效上觀察,大凡擁有事實感的作家,學問既不是障礙,更不是負擔,知識多寡皆宜,它們能自然融入作品。反之,若無事實感,材料將不受作家本人控制,會像奔涌的泥石流一般,把作品徹底搗毀。艾略特很喜歡拿莎士比亞作例子。《個人傳統與才能》有一個形象的譬喻:“莎士比亞從普魯塔克那里學到的歷史知識,比大多數人能夠從整個大英博物館學到的更為重要。”而《古典文學和文學家》講得更清楚:“關于莎士比亞,我們可以說,從來沒有任何人像他那樣給這么少的知識派上這么大的用場。”
布克哈特在其歷史講座中談道:“對于一心想豐富自己精神世界的人而言,巧妙地揀選少量的資料勝過名目繁多的資料,因為他可以在精讀這些少量文字的過程中學會在個性中尋找共性,從而做到舉一反三。”
所以,知識的數量、受教育的年限、考試的成績其實無關宏旨。《古典文學和文學家》認為,更關鍵的區分是,作家接受了什么類型的教育。在我國,作家如何實施自我教育,如何奪回自我教育權,事關他的作品的成敗高低。
接下來得問,作家需要怎樣的教育來培養事實感?它似乎區別于天才、穎悟,并非生而有之。T.S.艾略特開具了以古典文學為師、向傳統學習的處方。在《批評的功能》里他寫道:“真正的敗壞者是那些提供見解和空想之人。”
今天,傳媒和交流手段極其多元且如此有力,宣傳無孔不入,意見的教育已取代文學教育,持續指引一代又一代公民,趨勢似乎不可逆轉。也許對大多數人來說,這未必很糟糕,畢竟,他們在學生時代汲取知識的最主要非功利目標,往往就是形成觀念,增長分析力,以期面對紛繁多變的現象時,能迅速形成自己的判斷。當然,不同身份階層、社會經歷、天性好惡也將產生深遠影響。信息從四面八方涌至,生活節奏越來越快,人們已應接不暇。而所謂“意見領袖”,正是此情境下誕生的多目怪。判別黑白、擇選立場,以及評估每天眼花繚亂的事件之價值,大眾樂于向虛妄的意見專家、弄潮的學者請教或尋求認同。這些知識分子也確實令世人在消息的狂濤巨浪中暫獲安頓,他們一方面在具體意見上爭當領頭羊,言之鑿鑿,可是另一方面,又在偏好及口味上完全順服于蕓蕓眾生,非常明智地不去挑戰其短視的激憤惱怒。這對青年藝術家影響的結果必然是,鑒賞力和事實感無從培植、鞏固、壯大,天賦傷損,莫此為甚。
海量意見的泥沙沖來,美首先被拋棄,它們夾帶的社會新聞式素材,在事實感的淘洗篩選下,本該大放異彩。很可惜世間的流弊卻時時削弱,乃至消滅那看不見摸不著的事實感。身處意見和空想旋渦的作家,距離渾然天成的妙境越來越遠,文學煉金術并無進步,反倒日漸荒疏,因而不得不乞助于支離破碎的架構花樣、聳動的控訴式主題,并讓浮光掠影的意見或以之為核心的概念化虛構充斥作品內外。
T.S.艾略特要求學習者去讀經典原著,去熟悉本國歷史、世界歷史、藝術的歷史,盡量多掌握幾門外語,普遍吸收各學科的更多知識:“對一個有想象力的人,幾乎任何東西都能派上用場。”他進而比喻道:“隨便什么扔到他的磨里皆變成粉,他能吸收的知識愈多愈好。”
絕不能只跟同行交往,危害甚大。艾略特在《宗教與文學》里號召眾人皆應成為批評家。要做這樣一種人:“他把敏銳、持久的感受力和廣泛的、與日俱增而有辨別力的閱讀結合在一起。”閱讀的價值絕不僅止于獲取知識學問。廣泛閱讀,使人得以擺脫少數一兩個體系的宰制。海納百川,終成其大,首倡“總體藝術”的諾瓦利斯感慨,我們生活在一部波瀾壯闊的小說之中,而真正的詩人無所不曉。在彼此爭鳴的世界觀復調間實現平衡,是思想自由的標志,對于創世型作家而言,邁入這一兼容并包的境界尤其關鍵。
在《現代教育與古典文學》里,艾略特既反對現代功利主義教育,也反對處于另一極的“為閑暇而教育”。他近乎偏執地推崇拉丁文和希臘文教育,認定某些學科,比如經濟學,不適于用來充實大學初階的頭腦。依本人有限的閱歷經驗來看,這番議論或可以商榷。但我支持艾略特的下述觀點:現代教育鼓勵專門化的傾向,鼓勵人們去研究各自喜愛的學科,這類說法對于興趣在歷史和語言方面的靈魂,特別是對于懷揣作家夢的年輕人來說并不利。
“絕大多數將要受教育的人們并沒有十分強烈的專門化傾向,因為他們沒有明確的才能或愛好。那些具有更活躍更好奇的頭腦之人通常喜歡涉獵、淺嘗。”
真正的自由教育,而非自由主義教育,興許不得不依賴自我教育,畢竟,支撐小說家幻想世界的五大基柱,政治、宗教、經濟、文化、情感,或簡化版的三大基柱,生死關系、金錢關系和男女關系,關于它們的知識,無法從學校的課堂上充分完備地習得。如今我仰仗歷史哲學。對小說家而言,理解歷史為何如此發展,體會歷史環境的氛圍,大概比了解具體的歷史事件重要得多。
艾略特文論的第二個神秘概念是“批評”,它與“事實感”脈脈相通。創作本身便包含批評因素,這一因素有時更排在首位。
“的確,一個作家勞動的絕大部分或許是批評性質的:甄選、化合、構筑、刪除、修改、試驗等等。這些令人畏惕的艱辛,在同樣程度上,既是創造性的,也是批評性的。我甚至堅信,一個有修養的、熟練的作家運用在他自己作品上的批評,是最有活力的、最高一類批評,而且某些創造性的作家高于其他作家,僅僅因為他們的批評才能更高超。”實際上,作家的創造力高峰期,恰恰是他批評力最活躍的階段,但這股批評力凝聚向內,專一于自我完善,因此這也是他最容易客觀看待自己的時期。艾略特強調:“有些作家似乎需要通過多方面地鍛煉其批評能力,為他們的真正作品保持競技狀態。”
作者由此導出另一個結論,我們不妨留意:“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傾向于采取極端態度,即認為唯一值得一讀的批評家,是那些從事他們所談論的藝術門類的批評家,并且他們從事這門藝術的效果很理想。”同樣,大眾對批評的需求與之南轅北轍。《歐文·白璧德的人文主義》開篇指明:“當一個作者擅長于破壞性的批評,公眾對此感到滿意。如果作者沒有建設性的哲學思想,公眾也就不提這方面的要求;如果作者具有建設性思想,它往往被人忽視。”這樣的氛圍對青年作家不止無益,還阻礙他們的悟性在慣于低聲靜默的真理之中生長。艾略特總是不失時機地教導后人如何效法前賢。“一切偉大的詩歌都給人以錯覺,”他在《莎士比亞和塞內加斯多葛派哲學》里寫道,“以為它有一種人生觀。”而實際上,“對于詩人來說,只有斗爭才有生命——其目的就是把自我的、私人的痛苦轉化成更豐富、更不平凡的東西,轉化成普遍的、非個人的東西……”
要明白哪些學問應自修,要大力研究語言,收集詞匯。“作家的任務是用語言來交流;如果他通過想象進行創作,那么,他所從事的工作就是最困難的一種交流形式,其中準確性最為關鍵。”不過,艾略特所指的準確,跟人們整天掛在嘴邊的老生常談多么不同啊:“這種準確性不能事先規定下來,而是必須體現在每一個新詞語中。”又一次,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想沿著艾略特指引的道路破繭為作家何其不易!但回報也極豐厚。今天,我們要吸納的知識尤其紛繁,擺在我們面前的傳統尤其多樣復雜,至少分三類。其一是中國古典文學、哲學,以及諸多雅俗文化,其二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積累百余年的白話文傳統,其三是依賴翻譯家的辛勤勞作向我們敞開的西方文學世界。這一切又終將轉化為我們的巨大財富。
通過毫不挑食的學習、日復一日的創作,并對自己運用嚴苛的批評力,時時明道而集義,事實感覺醒了。《個人傳統與才能》將此后的過程描述為:“詩人把自己不斷地交給某件更有價值的東西,進步意味著不斷的自我犧牲。”艾略特花了許多段落去解說個性消滅和傳統意識之間的關系。人類的情感內核、共性,這些敘事學的重要定義呼之欲出,但作者始終未明確提及。“詩人的任務并不是去尋找新的情感,而是去運用普通的情感,去把它們綜合加工成為詩歌。”最后他大膽、堅定地判斷:“詩歌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個性的脫離。”顯然,真正的個性從來無可磨滅。至于現實,原本就充滿矛盾,故此費爾南·布羅代爾才會詰問:“辯護又有何益?”大凡他那樣的創造者,總是專誠于踐行己路,艱難而別有洞天的超常之路。所謂道無終窮,愈探愈深。
責任編輯陳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