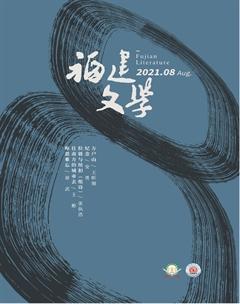林忠成的詩歌自覺道路
向以鮮
林忠成發來詩稿的同時,還發來了一段詩歌自傳:《林忠成創作歷程與詩歌風格變化內因》。按照我的寫作習慣,通常是不看這些帶有符號性的文字的,不想因作者的說辭而影響自己的判斷。但是,當我快速讀完這段文字時,內心竟然產生了輕微的震動。林忠成的簡介看似樸實無華,暗地里卻是浪潮洶涌——這段僅有500字的簡介,既是詩人的個人詩歌史,亦與中國當代詩歌發展的脈絡與波瀾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吻合。我一直以為個人史才是社會史最生動最富于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在林忠成極其私人化的個體詩史中,微妙地折射出時代的影子:
1989年開始詩歌寫作,狂熱喜歡海子,把《海子駱一禾作品集》《土地》等海子詩選背得滾瓜爛熟。20世紀90年代前期的詩歌受到海子語言的強烈影響,詩歌里大量出現月亮、村莊、少女、天堂、麥子、土地等農業文明的氣息。1994年開始,由于作品很難在公開刊物發表,加上90年代初期席卷全國的市場化浪潮,對海子為代表的神性寫作、終極價值追求、人文主義理想開始懷疑,內心極度絕望,對意象寫作、象征主義、隱喻等寫法開始反感。1994年至1999年,拋棄意象寫作,進行極端的口語詩歌寫作,對口語詩提倡的打倒一切價值、清算一切虛偽文化十分認同。這一時期的作品寫得很憤怒,對一切都看不慣,只在少量民刊刊發,大部分鎖在抽屜里。這些口語詩受到于堅、李亞偉、楊春光、伊沙等人的啟發。2000年前后思想再次產生波折,對形而下、身體寫作、口語同樣感到失望,認為這種寫作比意象寫作更誤入歧途,更加平庸,加速肉體墮落的同時導致靈魂支離破碎,寫作再次回到象征主義、隱喻等路徑,但是,已不完全相同于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風格,摻雜了敘事、復調、耗散結構等后現代的部分特色以及個人化經驗,吸取部分現實因素,也吸取了某些口語寫作的優勢。
我們讀到過太多的詩歌簡介或簡史,像林忠成這樣將自己的詩史置入時代的洪流,并且有著清晰明白的段落劃分,有著清醒的自我認知與判斷,這是需要勇氣、坦誠和眼光的。僅就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而言,在當代詩人中不能說沒有,但確實不是經常能夠見到的。我在寫杜甫的時候就曾深刻感受到,一個優秀的詩人和普通的詩人的區別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區別即在于:詩人寫作的自我覺醒意識。很多詩人雖然極富才華,也寫過一些好詩,但由于缺乏自我覺醒,在一種隨性和隨機的寫作中度過一生,最終成為一個糊涂的寫作者。這樣的寫作當然不可能產生真正杰出的作品,這樣的詩人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杰出的詩人。杜甫之所以最終成就其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甚至比李白還要偉大,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在于杜甫始終是一個清醒的寫作者。為什么要寫,寫什么,怎么寫,杜甫非常清楚,所以杜甫能做到“毫毛無遺憾,波瀾獨老成”。從文本、語言、結構到風格,杜甫都是一個有著高度覺醒意識的詩人。
林忠成將自己長達30年的寫作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1989年至1994年,5年的象征主義階段;1995年至1999年,5年的口語寫作階段;2000年至今:歷時20年的重返(象征)與復合(敘事或復調)寫作階段。與之相對應的生活經歷是:前20年為中學教師,近10年為地方新聞單位記者、編輯。
象征主義或意象寫作,可能是所有寫作者最容易進入的一個詩歌天國。象征主義滿足了詩人初期寫作的一切理想:神秘、突然、孤傲和不可言說。在這面大旗的召喚之下,確實產生了一代又一代大師。尤其是作為一個漢語詩人,漢字本身就是一座廣袤無邊的象征森林。每一個漢字,從造型、會意到發聲,都充滿了令人心動的象征色彩。幾千年的漢語詩歌史,說到底就是一部象征主義詩歌長卷。從《詩經》到漢樂府,從楚辭到唐詩,無處不回響著象征主義的清音。來看看詩人寫于1991年3月18日的那首《把愛情還給山腰上劈柴的妹妹》:
紅色沉悶的河流種子生下斧子/老虎生下斧子 白雪生下的斧子/你必須用音樂喂養它/把它交給山腰上劈柴的妹妹/你必須把種子和民謠交還她/野花纏繞妹妹的脖子/白云和馬生下的好女兒/你必須把豎琴和愛情還給她/野獸掛在妹妹的耳朵//
孤獨純潔/春天乳房上站立的妹呀/我流浪江湖騎著一支民謠/在民間與琵琶相依為命/山腰上快樂歌唱的妹呀/我是一位民間藝人/乘坐一支琵琶流向遠方//
斧子的嘴唇抓住春天/你被野花熏醉/云朵下劈柴的妹呀/我琵琶破碎兩手空空/白馬死在江湖/我是窗外被打斷腿的情種/野花的手掌 我的劍失于江湖//
妹妹,春天必須把愛情還給你/山腰上野獸流蕩/春天必須把河流和村莊還給你/我身在江湖,尋劍涉溪/陽光下妹妹的斧頭一閃一閃
我們可以很容易從中找到海子詩歌的痕跡,它顯然受到海子的《亞洲銅》或《春天》的啟發,里面的諸多意象如斧子、劈柴、白馬、妹妹或野花的手掌等,都有海子的詩歌的影子。重溫一下海子的《春天》(節選):
天空上的光明/你照亮我們/給我們溫暖的生命/但我們不是為你而活著/我們活著只為了自我/也只有短暫的一個春天的早晨/愿你將我寬恕/愿你在這原始的中心安寧而幸福地居住/你坐在太陽中央把斧子越磨越亮,放著光明/愿你在一個寧靜的早晨將我寬恕/將我收起在一個光明的中心/愿我在這個寧靜的早晨隨你而去
斧子在中國古典傳統中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意象,與父權、男性、砍伐和欲望緊密相關。最古老的斧子之歌來自夏代的孔甲,他曾為一個養子的腳為斧子所傷而作《破斧歌》。這首詩歌被稱為中國東方詩歌的初啼,與作為南音的《候人歌》齊名。盡管林忠成的早期詩作殘留著海子等人的影響,但詩人仍然表現出了不同尋常的自我抒寫能力。在海子的詩中,斧子是一個極其抽象的存在(“你坐在太陽中央把斧子越磨越亮,放著光明”),雖然明亮,卻近乎虛無;但在林忠成這兒,斧子被具象化了,成為一把可以握住可以撫摩的斧子。這把斧子不是從爐火中鍛打出來的,而是由種子、老虎或白雪生下來的,山腰上的妹妹可以用來劈柴。這個妹妹也不是一般的妹妹,她懂得播種,會唱民謠會彈豎琴,熱愛野花渴望愛情,擁有飽滿的春天的乳房,她是白云和馬生下的好女兒。最重要的是,她的耳墜是用“野獸”做成的。這個妹妹讓我想起楚辭中的山鬼。這把斧子的主人是詩人還是彈琵琶的民間藝人?那個“窗外被打斷腿的情種”忽然讓我想起被斧頭所傷的孔甲的養子。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末期,林忠成的詩風突變,進入一種他自己所描述的口語寫作時期。我個人一向認為,口語詩寫作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從語言史或詞匯史的角度來看,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口語與書面語之分——所有的書面語都來源于口語;幾乎所有的口語,都有書面語的根源。是否口語也與一首詩的成敗毫無關系:你用口語寫詩,寫出來的可能是一首卓越的詩,也可能是一首很爛的口水詩;你用典雅的書面寫詩,寫出來的可能是一首能流傳下去的詩,也可能是一首很糟糕的腐朽詩。決定一首詩的品質,或者決定一個詩人的內核,與他使用口語寫作還是書面語寫作,也沒有任何必然關聯。起決定性作用的,永遠是詩人的識見、情懷、天賦和風骨。總的來看,林忠成的口語寫作是一種不太成功的試驗性寫作。作為一個持續寫作的詩人來說,失敗有時比成功更重要,詩人必須從一次次失敗的陰影中走出來,才可能發現或抵達光明的彼岸。
《太遲了》是林忠成這一時期寫得比較有趣的一首:
全世界女人都在追趕我/餓狼般揮打舞棍/外星人快救我/快放下你們的飛艇//
我是地球上最后一個男人/連修女也對我動手動腳/遲一步人類就會絕種/那時總統也算不了啥/讓我當宇宙的宙長也威風不久/即使諾貝爾本人從墳中出來/把諾貝爾獎塞到我手里/我也不要
看起來很熱鬧,實際上深藏背后的是絕望、孤獨和無助,在自我調侃和自嘲中,揭示了世界和存在的某種荒誕性。這首詩最閃光的地方在于有趣味——趣味是詩歌的一個重要品質,可惜被很多人丟掉了。有部分詩人的詩歌好像寫得還不錯,甚至也有一些意蘊,但是毫無趣味,味同嚼蠟,讓人讀了一遍后就再也不想讀了,這樣的詩歌算不算一首成功的詩,還真的很難說。當然,我們不能狹隘地理解詩歌的趣味,這方面宋人嚴羽說得比較好:“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林忠成具有強烈的自省意識,他對自己幾年來的口語試驗性寫作并不滿意。過分的日常化或生活化的寫作、過分的不假雕飾,實際就是另一種故作姿態,必將把詩歌帶向歧途。進入21世紀以來,林忠成在重歸的基調上加入了更加多元的復調。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抒情的悠久詩歌傳統中,重新打撈敘事的潛力。我有一個比較偏執的看法,考量一個優秀詩人的一個重要手段,不是看他的抒情能力,而是看他的敘事能力。這種敘事能力又迥異于散文作家或小說家的敘事,必須是詩歌的敘事,詩人的敘事,有著獨立的敘事口吻和方法,像草蛇灰線一樣,存在于詩歌寫作的深處。
林忠成的一組關于現代交通工具的詩作引起我的注意:《波音客機從田間飛過》《自行車與波音飛機》和《拆自行車》。將工業文明尤其是現代或后工業文明帶入詩歌,是現代詩歌責無旁貸的天職,也是區別于古典詩歌的重要特質(古典詩歌的沃土是農業文明)。詩人一開始就將這兩種迥然不同的文明形態推向對立面:“波音客機以龐大的品質飛過天空/地上,兩個農民內心的陰影面積越來越大/逃往內心深處藏起來/遲了將被一股大質量的物體吞噬”。兩個完全沒有做好準備的農民面對文明的飛速進步,顯然是驚慌的,不斷擴大的內心的陰影面積,成了他們唯一的藏身之所。代表著新生力量的“孩子”們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螟蟲知道,一些卵將孵出”——一股旋渦從孩子們心里席卷而出!這是一首抒情詩嗎?當然是,但又不是;這是一首敘事詩嗎?當然是,但又不是。我幼年時代曾生活在大巴山腹地的一個名叫聶家巖的小村莊,親身經歷過類似的看飛機的場景,那確實是一種令人難忘的,混雜著驚奇與恐懼的場景。
林忠成用30年的時光,在詩歌的自覺道路上走了一大圈兒,最后,似乎真的走回來了(也可能是另一種出走)。瞧,他像那個“三條腿”的老王拆解自行車一樣,開始自我解構與重建——“藍汪汪的光籠罩全家/老王把一切都拆掉:語言結構、自行車、骨頭。”
責任編輯林東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