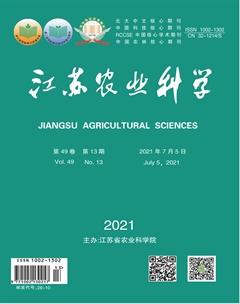二代測序技術(shù)和葉綠體基因組在菊花系統(tǒng)學(xué)分類和遺傳資源研究中的應(yīng)用綜述
夏涵涵 雷雪柔 黃臻齊 陳雪燕 杜一鳴 周厚高
摘要:快速發(fā)展的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適用于非模式植物的測序,成本較低、測序性能強(qiáng),目前被大量應(yīng)用于園藝植物鑒定和基因組輔助育種。而具有母系遺傳特征的葉綠體基因組,具有多拷貝、結(jié)構(gòu)保守等優(yōu)點(diǎn)。將葉綠體基因組與二代測序技術(shù)結(jié)合應(yīng)用,將成為植物遺傳資源研究的有效手段。本文綜述了二代測序技術(shù)和葉綠體基因組在包括菊花在內(nèi)的園藝植物種質(zhì)資源研究中的應(yīng)用,以期為菊花分類和遺傳資源研究提供理論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簡化基因組測序;葉綠體基因組;菊花系統(tǒng)學(xué)分類;基因組輔助育種;二代測序技術(shù);遺傳資源
中圖分類號(hào): S682.1+10.1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 ?文章編號(hào):1002-1302(2021)13-0025-04
菊花(Chrysanthemum×morifolium Ramat.),別稱鞠、黃花和秋菊,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菊花作為我國的傳統(tǒng)花卉,同時(shí)又是世界上四大切花之首,品種繁多,有著3 000余年的栽培史[1]。在唐朝,中國菊花傳到日本,日本人將其與野菊進(jìn)行雜交;明末清初時(shí)期,菊花又經(jīng)荷蘭商人引種至歐洲栽培,形成花色、花型各異的品種[1]。菊花具有極高的藥用和經(jīng)濟(jì)價(jià)值,用途多樣。藥菊如滁菊被研發(fā)成了滁菊蜜、 滁菊口含片等,還可利用其黃酮和揮發(fā)油等制作新產(chǎn)品[2]。又因其品種豐富,被許多藝術(shù)家用于雕塑、插花等藝術(shù)作品的制作。如今菊花在世界各地廣泛栽培,栽培技術(shù)和條件的提高,更是讓菊花的栽培和應(yīng)用具有更廣的前景[3]。
1 菊花分類研究進(jìn)展
1.1 傳統(tǒng)分類階段
菊花起源于中國,關(guān)于菊花最早的記載在《周禮》中,此外,周朝至春秋時(shí)期均有關(guān)于菊花的記載,在秦朝時(shí)甚至曾出現(xiàn)菊花銷售市場[4]。菊花具有極高的藥用價(jià)值,古人最早是以食用、藥用的目的來栽培菊花的,在我國關(guān)于菊花最早的分類在《本草經(jīng)》中,將其分為真菊和苦薏[5-6]。晉朝陶淵明獨(dú)愛菊,創(chuàng)作了許多贊美菊花的詩句,菊花被當(dāng)作觀賞植物開始廣泛栽培。宋朝是栽培菊花的盛期,隨著栽培技術(shù)的提高,出現(xiàn)了各種不同花色的菊花,人們開始以花色來對菊花進(jìn)行分類[5],宋朝各菊譜記載的品種也越來越多。明清時(shí)期還是按照宋朝的方法利用花色來對菊花進(jìn)行分類[5]。但是,由于古代技術(shù)的缺乏和局限,并未能對菊花進(jìn)行很詳細(xì)的記載和研究,菊花品種也沒有被科學(xué)系統(tǒng)地分類,僅記載了一些類別。
1.2 形態(tài)學(xué)系統(tǒng)分類整理階段
我國第1次對菊花進(jìn)行系統(tǒng)分類的是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李鴻漸教授,他經(jīng)研究整理后發(fā)現(xiàn)我國擁有 3 000 多個(gè)菊花品種[7]。形態(tài)學(xué)系統(tǒng)分類整理階段對菊花品種進(jìn)行分類的依據(jù)主要是花形、花色、瓣型等,各學(xué)者提出了不同的分類方案。湯忠皓提出將菊花分為22區(qū)、2花型、7瓣型和30個(gè)花型的四級(jí)方案[8],張樹林提出將菊花品種歸為2系、3瓣型、25花型的三級(jí)分類方案[9]。李鴻漸教授等發(fā)布了與全國菊花品種分類研討會(huì)相似的分類方案,將大菊品種分為5類、42型[10]。
1.3 現(xiàn)代綜合分類階段
現(xiàn)代的菊花分類依據(jù)除了形態(tài)學(xué)性狀之外,還有細(xì)胞學(xué)及分子生物學(xué)等性狀,可以對菊花進(jìn)行更深入、更細(xì)致的分類學(xué)研究。傅玉蘭對寒菊新品種進(jìn)行花粉形態(tài)研究,證實(shí)菊花外部形態(tài)特征與花粉形態(tài)的遺傳變異具有一定的相關(guān)性[11]。陳發(fā)棣等對幾種中國野生菊進(jìn)行減數(shù)分裂研究發(fā)現(xiàn),野菊為異源四倍體[12]。分子標(biāo)記技術(shù)在菊花種質(zhì)資源研究中的應(yīng)用為菊花的起源、菊屬植物種間的親緣關(guān)系、菊花品種的遺傳多樣性研究及菊花的品種分類和鑒定提供了豐富可靠的參考數(shù)據(jù)。不同的分子標(biāo)記技術(shù)[如隨機(jī)擴(kuò)增多態(tài)性DNA標(biāo)記(RAPD)、擴(kuò)增片段長度多態(tài)性(AFLP)和簡單重復(fù)序列間區(qū)(ISSR)等]對菊花品種分類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戴思蘭等曾用RAPD技術(shù)對菊花起源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野菊、毛華菊與栽培菊花的親緣關(guān)系最接近[13]。許多研究提出,瓣型在菊花起源中是一個(gè)重要的性狀,并可作為菊花分類的一個(gè)等級(jí)[14]。此外,這些標(biāo)記技術(shù)不僅可以將菊花的原始栽培品種區(qū)分開來,還可以區(qū)分從一個(gè)品種中衍生出來的突變體,這就為今后菊花品種鑒定和培育工作提供了技術(shù)支持。
1.4 存在的問題
前人雖然已經(jīng)在中國菊花品種形態(tài)分類和鑒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5-16],但是對于品種數(shù)量眾多的菊花來說,制定全面系統(tǒng)的分類鑒定方案非常困難,在品種分類和遺傳資源研究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足和局限。一是由于菊花品種間差異較小、遺傳復(fù)雜及高度的自交不育性,加大了菊花研究的難度。二是菊花品種收集和保存難度大,菊花品種繁多,易雜交產(chǎn)生新的變異,缺乏直接有利的生物分子信息[17]。三是菊花分類體系和鑒定手段不完善,目前主要仍以形態(tài)特征作為分類依據(jù),受自然環(huán)境的影響較大。尋找穩(wěn)定的遺傳標(biāo)記、有效地鑒定菊花品種是今后菊花品種資源研究的重要課題,應(yīng)重視分子生物學(xué)方向的研究,用不同的分子標(biāo)記技術(shù)進(jìn)行菊花品種研究。
2 葉綠體基因研究進(jìn)展
葉綠體是部分藻類及高等植物特有的、具有雙層膜結(jié)構(gòu)的半自主性細(xì)胞器,其最重要功能就是通過光合作用合成重要氨基酸類物質(zhì)并產(chǎn)生能量,是植物體重要的能量轉(zhuǎn)換器[18]。葉綠體基因組即葉綠體DNA(cpDNA),包含葉綠體中所有的DNA。自Shinozaki等成功獲取煙草(Nicotiana tabacum)的葉綠體基因組全序列以來,越來越多的植物葉綠體基因組序列被測定[19]。葉綠體基因組庫中含有同一個(gè)種的不同亞種葉綠體基因組序列,反映了它們之間存在進(jìn)化差異[20]。由于葉綠體基因組具有比較保守的環(huán)狀結(jié)構(gòu)、獨(dú)立的基因組及屬于母系遺傳,使得葉綠體轉(zhuǎn)化技術(shù)成為研究植物進(jìn)化研究的有效手段。
2.1 葉綠體基因組結(jié)構(gòu)
葉綠體基因組序列的基因組大小、結(jié)構(gòu)、種類的保守性都很強(qiáng),絕大部分葉綠體DNA為雙鏈閉合環(huán)狀分子,極少數(shù)是線狀,如傘藻(Acetabularia)和玉米(Zea mays)。葉綠體基因組的大小一般為 120~160 kb,也存在同一物種大小差異過大的情況,如綠藻的葉綠體DNA的差異很大,小的如某種寄生性綠藻(Simulium jonesii)的DNA大小只有 37 kb,而大的如傘藻的DNA大小則達(dá)2 000 kb[21]。cpDNA有4個(gè)基本組成部分,雖然不同植物的葉綠體DNA長度各不相同,但大部分植物葉綠體中均有1段大致為10~24 kb且呈反向重復(fù)的DNA序列(IRA、IRB)。除此以外,IRA和IRB之間發(fā)生重組形成了小單拷貝序列(small single copy region,簡稱SSC),剩下的部分就是大單拷貝序列(large single copy region,簡稱LSC)。IRA、IRB大小和方向的不同是造成cpDNA差異的主要原因,如被子植物豌豆(Pisum sativum)甚至已經(jīng)失去IR區(qū)間,而纖細(xì)裸藻(Euglena gracilis)含有3段方向相同的重復(fù)DNA序列,紫紅紫菜(Porphyra purpurea)的IR序列同向重復(fù)[20]。葉綠體基因組編碼的基因可大致分為3類,分別是光合系統(tǒng)基因(psaA、psaB、psaC、petA、petB、atpA等)、遺傳系統(tǒng)基因(rrn5、trnH、rpl2等)、生物合成基因(matK、cemA等)。
2.2 葉綠體基因組在園藝作物研究中的應(yīng)用
隨著基因組學(xué)的發(fā)展,葉綠體基因組憑其自身特點(diǎn)和優(yōu)勢已經(jīng)成為基因組測序的首要選擇,在植物的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中有巨大優(yōu)勢。如段義忠等通過葉綠體基因組對比分析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和小沙冬青(A. nanus)在蝶形花科中的系統(tǒng)進(jìn)化發(fā)育[22]。楊嘉鵬等對3種石豆蘭屬藥用植物葉綠體基因組進(jìn)行組裝注釋,為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和物種鑒定提供了理論依據(jù)[23]。趙惠恩對菊花的cpDNA基因序列中的trnT-trnL、trnL-trnF序列進(jìn)行研究,發(fā)現(xiàn)毛華菊(C. vestitum)和栽培菊花的序列差異較大,而栽培菊花和甘菊(C. lavandulifolium)的序列完全相同,由此可見,栽培菊花的母系祖先種可能是甘菊,并非毛華菊[24]。李世茂采用葉綠體基因間隔序列對比分析法探討研究栽培菊和野生近源種的系統(tǒng)學(xué),為栽培菊的起源提供了理論依據(jù)[25]。劉錫娟等在試驗(yàn)中通過用菊花Rubisco小亞基的啟動(dòng)子驅(qū)動(dòng),在基因的5′端加葉綠體定位信號(hào)肽,構(gòu)建了植物表達(dá)載體并進(jìn)行其他轉(zhuǎn)基因方面的試驗(yàn),獲得轉(zhuǎn)5-烯醇式丙酮酰莽草酸-3-磷酸合酶(EPSPS)基因抗草甘膦煙草和棉花[26]。何熠將菊屬、亞菊屬葉綠體DNA測序組裝后,分別進(jìn)行結(jié)構(gòu)分析,發(fā)現(xiàn)菊屬、亞菊屬不同物種之間的差異很小[27]。通過基因組大小比對,發(fā)現(xiàn)它們的葉綠體基因組長度十分相似,都在151 000 bp左右,表明該物種全含有相同的一套編碼基因。
3 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方法
3.1 二代測序技術(shù)
1977年Sanger等發(fā)明的雙脫氧鏈終止法(即第1代DNA測序技術(shù))是獲得植物全基因組最傳統(tǒng)的DNA測序技術(shù)[28]。Sanger測序法的測序程序是根據(jù)DNA復(fù)制和RNA反轉(zhuǎn)錄的原理來設(shè)計(jì)的。人們利用該技術(shù)第1次獲得了擬南芥的全基因序列[29]。基于Sanger測序發(fā)展起來的二代測序技術(shù)(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簡稱NGS)目前已被廣泛應(yīng)用于觀賞植物分子標(biāo)記、圖譜構(gòu)建等[30-31]。二代測序技術(shù)主要有Illumina公司的Solexa Genome Analyzer測序平臺(tái)、454測序技術(shù)、寡聚物連接檢測(SOLiD)測序技術(shù)、完整基因DNA測序方法(complete genomics)測序方法、半導(dǎo)體測序技術(shù)等5種測序技術(shù)。雖然Sanger測序法能夠高準(zhǔn)確性地完成大量測序工作,但其存在成本高、速度慢、通量低等不足,而二代測序技術(shù)則是一種低成本、高通量的測序技術(shù),1次可對成千上百萬條DNA分子同時(shí)進(jìn)行快速測序,故NGS逐漸取代Sanger測序法而被廣泛應(yīng)用。 如北美云杉(Picea sitchensis)的葉綠體基因組序列就是通過此方法獲得的[32],胡志剛利用454測序技術(shù)結(jié)合標(biāo)簽法獲得了菊科藥用植物的葉綠體基因組全序列[33]。隨著二代測序的運(yùn)用,發(fā)展出來的簡化基因組測序應(yīng)用更加廣泛,它是通過選擇一種限制性內(nèi)切酶進(jìn)行酶切,然后進(jìn)行文庫片段大小選擇,使用一定大小的酶切片段所對應(yīng)的序列作為整個(gè)基因組序列的部分代表來降低基因組的復(fù)雜性。對群體中不同基因型的個(gè)體采用相同的內(nèi)切酶進(jìn)行酶切,回收相同大小范圍的酶切片段建立文庫,然后進(jìn)行高通量測序。對于有參考基因組序列的物種,可進(jìn)行測序片段的比對;而對于沒有參考序列的物種,則先組裝序列然后進(jìn)行序列比對。通過簡化基因組測序和分析,可以準(zhǔn)確發(fā)現(xiàn)單核苷酸多態(tài)位點(diǎn)(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簡稱SNP)。王柏柯等利用簡化基因組測序?qū)?60個(gè)特定番茄樣本進(jìn)行測序和分析,共獲得8個(gè)與目標(biāo)基因相關(guān)的候選區(qū)域,對番茄雄性不育基因進(jìn)行初步定位,為雄性不育基因的克隆功能提供理論基礎(chǔ)[34]。張珊珊等對從24個(gè)天然的云南藍(lán)果樹樣本進(jìn)行基因測序中獲得6 309 個(gè)有效SNP位點(diǎn)進(jìn)行遺傳分析,得出了現(xiàn)存植株之間親緣關(guān)系較遠(yuǎn)的結(jié)論,認(rèn)為該品種的種質(zhì)資源具有很大的保存價(jià)值和研究價(jià)值[35]。由于全基因組測序?qū)τ谙窬栈ㄟ@樣大基因組的物種仍然很困難,而其他的一些遺傳簡化方法具有很高的偏差和限制[36],因此對于很多非模式的物種,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仍然是一種經(jīng)濟(jì)且有效的途徑來產(chǎn)生高密度的SNP,可以用來對園藝作物進(jìn)行鑒定和分類,完成基因組輔助育種。周春玲通過AFLP技術(shù)對菊屬12個(gè)分類群體進(jìn)行分析,結(jié)果表明,滁菊、毫菊2個(gè)品種可歸并為1個(gè)品種,且與毛華菊、野菊、甘菊的親緣關(guān)系較近[37]。洪亞輝等利用RAPD技術(shù)對5種菊花變異種后代進(jìn)行遺傳差異分析,從中發(fā)現(xiàn)6種引物的多態(tài)差異性明顯,結(jié)果表明,變異菊花在DNA水平上具多態(tài)差異性[38]。葉松選用99種菊花對其進(jìn)行高通量測序分析,得到簡單重復(fù)序列(simple sequence repeat,簡稱SSR)片段 32 863 條,隨機(jī)篩選的100對SSR引物中有16對SSR引物具有多態(tài)性,且擴(kuò)增條帶清晰[39],為分子標(biāo)記輔助育種在菊花的研究上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jù)。
4 展望
菊花的起源和系統(tǒng)學(xué)的研究已經(jīng)持續(xù)了很多年,但由于菊花品種繁多、品種差異較小和技術(shù)、歷史的局限性,并未能很好地解釋菊花分類及系統(tǒng)關(guān)系,存在較大的分歧。雖然前人已經(jīng)有進(jìn)行深入到DNA序列方向的研究,但目前有關(guān)于菊花葉綠體基因組序列的研究仍比較缺乏。葉綠體的基因?qū)儆谀感赃z傳,具有獨(dú)立的遺傳系統(tǒng)。與核基因組相比,其結(jié)構(gòu)和基因組成非常保守,具有多拷貝、進(jìn)化速率適中、在分子水平上具有明顯差異等優(yōu)點(diǎn)[40]。利用cpDNA對菊花品種的系統(tǒng)進(jìn)化研究具有很大的潛力,近年來測定葉綠體基因組序列也成為了系統(tǒng)進(jìn)化和物種分類強(qiáng)力有效的手段。但群體間存在雜交現(xiàn)象,而cpDNA屬單親遺傳,故其無法解釋全部的系統(tǒng)發(fā)育現(xiàn)象,也無法揭示完整的進(jìn)化過程。
隨著科技的發(fā)展,NGS憑借其測序性能強(qiáng)、周期短、無需參考基因組等優(yōu)點(diǎn),一躍成為探究植物全基因組序列、遺傳多樣性的有效技術(shù)。因此,結(jié)合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可獲取更多的遺傳信息和不同水平的區(qū)分特征,葉綠體基因組和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可更廣泛地運(yùn)用在園藝作物鑒定和分類上,輔助分子育種,對園藝作物進(jìn)行種質(zhì)創(chuàng)新和品種改良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xiàn):
[1]薛守紀(jì). 菊花栽培[M]. 北京:中國林業(yè)出版社,2004:3-4.
[2]王世福,龔建國,王 詔. 滁菊產(chǎn)業(yè)化發(fā)展綜述[J]. 安徽農(nóng)學(xué)通報(bào),2012,18(17):10,69-70.
[3]鐵 錚. 菊花起源之爭[N]. 北京日報(bào),2013-10-09(20).
[4]劉春迎,王蓮英. 菊花品種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Ⅰ)[J]. 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5,17(2):79-87.
[5]孫文松. 菊花品種起源及形態(tài)學(xué)分類研究[J]. 黑龍江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3(9):58-60.
[6]牟禮忠. 霜寒時(shí)節(jié)話菊花[J]. 廣西林業(yè),2004(1):75.
[7]李鴻漸,邵健文. 中國菊花品種資源的調(diào)查收集與分類[J]. 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1990,13(1):30-36.
[8]湯忠皓. 中國菊花品種分類的探討[J]. 園藝學(xué)報(bào),1963,2(4):441-418.
[9]張樹林. 菊花品種分類的研究[J]. 園藝學(xué)報(bào),1965,4(1):35-46.
[10]李鴻漸. 中國菊花[M]. 南京:江蘇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1993.
[11]傅玉蘭. 根據(jù)花粉形態(tài)探討寒菊新品種的遺傳特性[C]//中國風(fēng)景園林學(xué)會(huì),北京市園林局,中國菊花研究會(huì).中國菊花研究論文集(1997—2001). 2001:4.
[12]陳發(fā)棣,陳佩度,李鴻漸.幾種中國野生菊的染色體組分析及親緣關(guān)系初步研究[J]. 園藝學(xué)報(bào),1996(01):67-72.
[13]戴思蘭,陳俊愉,李文彬. 菊花起源的RAPD分析[J]. 植物學(xué)報(bào),1998,40(11):1053-1059.
[14]吳在生,李海龍,劉建輝,等. 65個(gè)菊花栽培品種遺傳多樣性的AFLP分析[J]. 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07,31(5):67-70.
[15]白新祥. 菊花花色形成的表型分析[D]. 北京: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2007.
[16]雒新艷. 大菊品種資源遺傳多樣性研究[D]. 北京: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2009.
[17]張莉俊,戴思蘭. 菊花種質(zhì)資源研究進(jìn)展[J]. 植物學(xué)報(bào),2009,44(5):526-535.
[18]Ahlert D,Ruf S,Bock R. Plastid protein synthesis is required for plant development in tobacco[J]. PNAS,2003,100(26):15730-15735.
[19]Shinozaki K,Ohme M,Tanaka M,et al. The complete nucleotide sequence of the tobacco chloroplast genome:its gene organization and expression[J]. The Embo Journal,1986,5(9):2043-2049.
[20]邢少辰,Liu C J . 葉綠體基因組研究進(jìn)展[J]. 生物化學(xué)與生物物理進(jìn)展,2008,35(1):21-28.
[21]Maier R M,Schmitz-Liuneweber C. Plastid genomes[M]//Daniell H,Chase C D. Molecular 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of the plant organelles:chloroplasts and mitochondria. Netherlands:Springer Netherlands,2004:115-150.
[22]段義忠,張 凱. 沙冬青屬植物葉綠體基因組對比和系統(tǒng)發(fā)育分析[J]. 西北植物學(xué)報(bào),2020(8):1323-1332.
[23]楊嘉鵬,朱紫樂,范雅娟,等. 三種石豆蘭屬藥用植物的葉綠體基因組比較分析及物種鑒定研究[J]. 藥學(xué)學(xué)報(bào),2020,55(11):2736-2745.
[24]趙惠恩. 菊屬基因庫的建立與菊花起源的研究及多功能地被菊育種[D]. 北京: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2000.
[25]李世茂. 基于葉綠體DNA基因間隔序列的菊花與近緣種親緣關(guān)系研究[D]. 武漢:華中農(nóng)業(yè)大學(xué),2010.
[26]劉錫娟,劉昱輝,王志興,等. 轉(zhuǎn)5-烯醇式丙酮酰莽草酸-3-磷酸合酶(EPSPS)基因抗草甘膦煙草和棉花的獲得[J]. 農(nóng)業(yè)生物技術(shù)學(xué)報(bào),2007,15(6):958-963.
[27]何 熠. 基于二代測序技術(shù)對SNP檢測軟件的比較研究[D]. 石河子:石河子大學(xué),2019.
[28]Sanger F,Nicklen S,Coulson A R. DNA sequencing with chain-terminating inhibitors[J]. Biotechnology,1977,24(12):104-108.
[29]Arabidopsis Genome Initiative. Analysis of the genome sequence of the flowering plant Arabidopsis thaliana[J]. Nature,2000,408(6814):796-815.
[30]熊 燕,張金柱,董 婕,等. 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在觀賞植物中的應(yīng)用研究進(jìn)展[J]. 園藝學(xué)報(bào),2020,47(6):1194-1202.
[31]趙 娜,苗艷梅,趙 敏. 未知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學(xué)檢測方法的研究現(xiàn)狀[J]. 江蘇農(nóng)業(yè)學(xué)報(bào),2019,35(1):224-228.
[32]白雪菲. 基于混合樣品高通量測序數(shù)據(jù)的植物葉綠體基因組拼接和分析[D]. 杭州:浙江大學(xué),2013.
[33]胡志剛. 菊科藥用植物DNA條形碼及葉綠體基因組研究[D]. 武漢:湖北中醫(yī)藥大學(xué),2012.
[34]王柏柯,李 寧,唐亞萍,等. 基于簡化基因組測序技術(shù)的番茄雄性不育基因定位[J]. 西北農(nóng)林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17,45(6):177-184.
[35]張珊珊,康洪梅,楊文忠. 基于簡化基因組技術(shù)的云南藍(lán)果樹群體遺傳分析[J]. 植物研究,2019,39(6):899-907.
[36]Catchen J M,Hohenlohe P A,Bernatchez L,et al. Unbroken:RADseq remains a powerful tool for understanding the genetics of adaptation in natural populations[J]. Molecular Ecology Resources,2017,17(3):362-365.
[37]周春玲,戴思蘭. 菊屬部分植物的AFLP分析[J]. 北京林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2(增刊1):72-76.
[38]洪亞輝,朱兆海,張學(xué)文,等. 運(yùn)用RAPD分析菊花輻射變異后代遺傳差異[J]. 湖南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自然科學(xué)版),2003,29(6):462-467.
[39]葉 松. 菊花表型性狀與SSR、SCoT分子標(biāo)記的關(guān)聯(lián)分析[D]. 鄭州:河南大學(xué),2017.
[40]田 欣,李德銖. DNA序列在植物系統(tǒng)學(xué)研究中的應(yīng)用[J]. 云南植物研究,2002,24(2):170-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