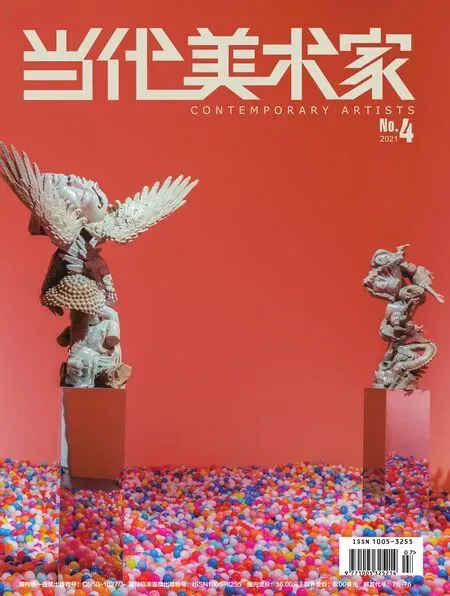博弈的圖像生產(chǎn)者——關(guān)于川美“新繪畫”一代的觀念、方法及實踐
張小濤

1張小濤潰爛的山水布面油畫300cmx200cm2006
景觀并非一個圖像集合,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社會關(guān)系,通過圖像的中介而建立的關(guān)系。景觀不能被理解為對某個視覺世界的濫用,即圖像大量傳播技術(shù)的產(chǎn)物,它更像是一種變得很有效的世界觀,通過物質(zhì)表達世界觀,這是一個客觀化的世界視覺。1
“新繪畫”是2000年以來中國當代藝術(shù)史中重要浪潮之一,一直到2008年“新繪畫”成為這個時期當代藝術(shù)現(xiàn)場的熱點,它們從20世紀90年代初當代藝術(shù)的社會學、政治化、符號學潮流的陷阱中逃離了出來,其圖像方法和觀念實踐成為那個時代美學與政治的某種縮影。一個時代的藝術(shù)家能夠拒絕當代藝術(shù)學術(shù)和市場主流的模式,這本身就是一種獨立的姿態(tài),瑞士獨立策展人格哈特 · 塞曼說:“當態(tài)度成為形式” ,此刻“圖像”便成為了“態(tài)度”。“新繪畫”的一代大多是實驗主義者,是拒絕被同質(zhì)化的新一代,對于他們來說圖像就是觀念,“圖像生產(chǎn)者”意味著繪畫是觀念化的思考與實踐,“圖像寫作”意味著題材不可重復,圖像的敘事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觀念性的繪畫成為一種實驗的方向,繪畫不再是符號化的批量生產(chǎn),這是“新繪畫”對當代藝術(shù)圖像方法上的重要貢獻,他們與上一代藝術(shù)家面臨的社會轉(zhuǎn)型時期的困境是不一樣的,如果說“85時期”和20世紀90年代初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是與歷史和社會的肉搏,那么“新繪畫”的一代一開始就面臨著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圖像泛濫的景觀社會的迅猛到來,他們的圖像方法一開始就帶有分析性、虛擬性和觀念性的成分,因為時代背景已經(jīng)徹底地變了,顯然他們的方法和工具也隨之而改變了,處在“景觀社會”和“圖像生產(chǎn)”的交鋒關(guān)系之中,像一群時間的賭徒充滿了不確定性……
20世紀80年代“宏大敘事”的現(xiàn)代主義訴求和90年代的符號化的政治神話的遠去,集體主義潮流的不復存在,發(fā)生了從集體主義經(jīng)驗到個人經(jīng)驗的轉(zhuǎn)換。生命的個體差異取代時代、國家、地域的“宏大敘事”的歷史經(jīng)驗。“大眾文化與微觀政治” 時代的來臨,誰也把握不住這個時代的整體,我們只是成為無數(shù)的碎片中的一環(huán)。“微觀敘事”的到來,剩下的是藝術(shù)家的個案,那些從現(xiàn)場里生長的具有普遍性的當代藝術(shù)經(jīng)驗和方法論,越來越具有國際性品質(zhì)。2
隨著當代藝術(shù)浪潮的流變,新媒體藝術(shù)成為未來的主流,“新繪畫”不再成為當代藝術(shù)的一個主要的現(xiàn)象,時至今日我們可以在一些展覽上看到“新繪畫”一代的一些消息,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的孤獨實驗,到2005-2008年市場的熱捧,到今日的沉寂,這也是一種變化的必然,是藝術(shù)史的規(guī)律,沒有任何人會一直在潮流之中,每一代人都有屬于自己的時刻表,就像是一場重要比賽已經(jīng)結(jié)束了,但是那些光榮與夢想的時刻卻被歷史所遺忘,塵埃落定時,我們可以冷靜理性地來討論和思考,“新繪畫”曾經(jīng)在當代藝術(shù)浪潮中做過什么,在觀念和方法上有什么樣的革新,他們在哪里?
我想通過討論“新繪畫”的展覽史、觀念與方法、空間中的實踐等來梳理這段塵封的往事,把“新繪畫”放在一個轉(zhuǎn)型期的歷史語境中去討論,讓他們曾經(jīng)的學術(shù)實踐能被后來者所知曉。今天當代繪畫的評價系統(tǒng),往往以拍賣價格作為最重要的參照系數(shù),所以“新繪畫”其實既不在學術(shù)的評價系統(tǒng)中,也不在商業(yè)拍賣的系統(tǒng)中,這是一個很尷尬的事實。我們?nèi)绾稳グl(fā)現(xiàn)那些隱秘的史實,如何重返20多年前“新繪畫”的觀念與實踐現(xiàn)場,去呈現(xiàn)他們的工作方法與學術(shù)價值,去討論“新繪畫”遇到的困境,這是我在本文中要討論的問題。
“新繪畫”展覽史1992-2008
A.1992-1996年
1992年“今日狀態(tài)· 1992” 參展藝術(shù)家:俸正杰、曾浩、余極,學術(shù)主持:王林,地址:四川美術(shù)學院陳列館;1993年“O 畫室作品展” 學術(shù)主持:王林,參展藝術(shù)家:劉文彬、秦朗、唐濤、何晉偉、謝南星,地址: 四川美術(shù)學院陳列館;1994年“陌生情景”策展人:王林,參展藝術(shù)家:郭偉、郭晉、忻海洲、張瀕,地址:四川美術(shù)學院陳列館;1994年“切片”參展藝術(shù)家:陳文波、封勝、杜峽、何森、尹睿林、趙能智,地址:重慶市中區(qū)教師進修學校;1996年“個人經(jīng)驗”,策展人:王林,參展藝術(shù)家:廖一百、楊冕、張小濤,地址:四川美術(shù)學院陳列館;
生活雖近猶遠,如果它只是皮相,藝術(shù)雖遠猶近,如果它回到人本。在都市成為當代文化中心,而都市中的人又在種種異化的文化力量前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們必須返回起點,從人的生命需要和精神需要出發(fā)去思考藝術(shù)的價值。3
四川新一代藝術(shù)家的崛起,以20世紀90年代初的沈曉彤、忻海洲等人為代表,與上一代的何多苓、張曉剛等人的作品相比,視點從肢解和拼接的超現(xiàn)實主義造型轉(zhuǎn)向作者自身的現(xiàn)實場景,內(nèi)涵從大文化轉(zhuǎn)向藝術(shù)家自身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4
以上是1992-1996年期間川美“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的一些重要展覽,其中“切片”與“陌生情景”展覽的藝術(shù)家們當時已經(jīng)畢業(yè)或者留校任教了,其余藝術(shù)家都是在畢業(yè)時做的展覽,這幾個展覽其實都有某種共性:1)關(guān)注身邊的日常經(jīng)驗,個人經(jīng)驗,去政治化傾向。2)都市人文主義傾向,關(guān)注消費主義盛行的流行文化和荒誕艷俗的現(xiàn)實。 3)注重一種繪畫的觀念性實驗,不是尋求符號化的繪畫。4)從現(xiàn)實世界轉(zhuǎn)向了虛擬的景觀社會,對繪畫語言進行陌生化、異樣化處理。我們可以把這些早期的實驗視為“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播下的一粒粒種子,在他們后來的觀念、語言實驗中,我們可以找到其來源,也可以看到當時四川美術(shù)學院青年教師的王林、張曉剛、朱小禾、陳衛(wèi)閩等身體力行的當代藝術(shù)實踐,為“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帶來了榜樣性的力量。
八九年以后,中國藝術(shù)在此基礎(chǔ)上發(fā)生一系列根本變化,外在原因是單純、沖動的理想主義在現(xiàn)實面前受阻,內(nèi)在原因是經(jīng)過冷靜反思新潮美術(shù)的過程,中國當代藝術(shù)開始進入自覺狀態(tài)。表現(xiàn)之一就是藝術(shù)對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活、精神生活的多種聯(lián)系兼存并容,不再僅以反批判性為結(jié)合部。表現(xiàn)之二就是在認同西方藝術(shù)文化的同時開始致力于建設(shè)獨立性的中國當代藝術(shù)文化,注重前衛(wèi)性和本土化的關(guān)系,切近中國人的生存經(jīng)驗和藝術(shù)經(jīng)驗,從不同的角度來呈現(xiàn)或揭示當代中國的文化問題和精神問題。5
1993年王林在四川省美術(shù)館為毛旭輝、王川、張曉剛、周春芽等策劃的“中國經(jīng)驗”展,可以視為20世紀90年代西南當代藝術(shù)運動中最重要的歷史節(jié)點,對歷史和當下的生存經(jīng)驗的深度表達,成為了西南當代藝術(shù)的特質(zhì),他們既是這個區(qū)域當代藝術(shù)杰出的參與者,也是推動者,“中國經(jīng)驗”展覽場刊成為“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私下學習當代藝術(shù)現(xiàn)場的重要文本,西南藝術(shù)中的歷史深度體驗與沉思,多年后在一些“新繪畫”藝術(shù)家的作品中依然保留著這種精神上的血緣關(guān)系,這也是四川當代藝術(shù)代代相傳的原因。年輕藝術(shù)家與上一代藝術(shù)家之間是一種“手遞手”的溫暖傳遞,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不是權(quán)利等級的劃分,也不是俄狄浦斯式的“弒父”,而是一種靜默的傳承。我們通過早期“新繪畫”的展覽史,也可以考察早期20世紀90年代西南當代藝術(shù)的嬗變,發(fā)現(xiàn)其實是有“一脈單傳”的暗線,甚至有些口傳心授的“地下黨”意味。
B.1999年
“視覺的力量——上河美術(shù)館學術(shù)邀請展”,學術(shù)主持:黃專,策展人:張曉剛,參展藝術(shù)家:陳文波、陳亮、郭晉、廖海瑛、何森、忻海洲、鐘飆、張小濤、趙能智,地址:成都上河美術(shù)館。
1996年張曉剛從重慶移居到成都玉林小區(qū),1996-1997年張小濤、謝南星、楊冕先后開始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學,1999年陳文波遷居北京,何森、趙能智遷居成都,而此時的上河美術(shù)館就成為了西南當代藝術(shù)的最前沿的實驗場,也是當年西南年輕一代藝術(shù)家走向全球化征途的“國際機場”。1999年上河美術(shù)館的學術(shù)邀請展就是一次“新繪畫”一代不同凡響的集體發(fā)聲,有不少的藝術(shù)家通過這個展覽的推薦走向了更加廣闊的國際當代藝術(shù)系統(tǒng),2000年之后其中一些藝術(shù)家陸續(xù)移居到北京生活與工作。此展張曉剛作為展覽的策展人,學術(shù)主持黃專寫了《視覺的力量》的文章。
在“視覺力量”這個題目下展出作品的12 位藝術(shù)家并不是因為他們在藝術(shù)問題、藝術(shù)目標和藝術(shù)趣味上存在什么共同點,恰恰相反,共同展出的理由倒是因為在他們的藝術(shù)中缺乏那種標本化的一致性,他們不反映任何潮流,任何時代性的精神,也沒有任何可以歸類的派別特征,如果說他們有什么共通的東西,那僅僅在于他們的作品都體現(xiàn)了某種視覺自治的要求。
20世紀90 年代以來的中國,藝術(shù)中視覺創(chuàng)造的獨立性正在被各種虛擬的藝術(shù)權(quán)力和偽造的命題所篡奪和侵蝕,當代藝術(shù)在文化上的積極意義也正在被它的相對主義、拜金主義和機會主義的消極后果所限制,對西方強權(quán)的身份依賴正使它墮入純粹策略性和犬儒性的陷阱。在今天,擺脫中國當代藝術(shù)圖解式的政治命題、社會命題和文化命題甚至成了它真正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命題、社會命題和文化命題的一個必要前提,而從當代藝術(shù)的自身邏輯出發(fā)設(shè)置自己的藝術(shù)問題,強調(diào)視覺創(chuàng)造的自治性和獨立品行自然地成為解決中國藝術(shù)問題的一種新方案。6
黃專稱這些“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的工作是一種“視覺自治”,他認為這些藝術(shù)家在擺脫一種犬儒主義的政治化、符號化的潮流,他們試圖以一種“圖像寫作”的方式來進行圖像生產(chǎn),從藝術(shù)自身的邏輯出發(fā)尋找自己的問題。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到來,與“景觀社會”不期而遇,圖像成為了20世紀90年代末每個人都遭遇到最嚴峻的現(xiàn)實,黃專有一種先知先覺的洞察力,他幾乎是早了十年判斷這些“新繪畫”的學術(shù)價值,只是這個時候,大家都還在一種自我實踐中,真正走向國際化的道路,還要在未來的時間中去檢驗。
C、2004年
“中國當代繪畫”,策展人:洛倫佐·薩索利·德比安基,參展藝術(shù)家:俸正杰、付泓、何森、李大方、李松松、石心寧、馬六明、鄔一名、魏光慶、王興偉、謝南星、楊千、曾梵志、曾浩、張曉剛、張小濤、周鐵海,地址:意大利博洛尼亞銀行基金會。
此次展覽由意大利博洛尼亞現(xiàn)代美術(shù)館館長洛倫佐·薩索利·德比安基博士策劃,部分“新繪畫”藝術(shù)家參加了這個展覽,展覽畫冊的出版與傳播為中國“新繪畫”在國際上獲得良好的學術(shù)影響力、尤其米蘭的《Flash Art》雜志與米蘭馬蕊娜畫廊的參與對“新繪畫”的學術(shù)和市場的推動起到了關(guān)鍵性的作用。此展覽早于2006年國際當代藝術(shù)市場對中國當代繪畫的嗅覺,博洛尼亞銀行基金會也收藏了該展覽全部作品,為“新繪畫”的國際傳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證明“新繪畫”的實踐得到了國際當代藝術(shù)機構(gòu)的廣泛關(guān)注。“新繪畫”與德國“萊比錫畫派”有相似的地方:既有國際化的視野,也有社會主義的美學特征與本土化的內(nèi)核,從繪畫的觀念和語言的角度上來講具有強烈的個人特征。
D、2007年
“從‘新具像’到‘新繪畫’”,策展人:呂澎,參展藝術(shù)家:陳文波、俸正杰、郭晉、郭偉、何森、李季、毛旭輝、潘德海、沈小彤、唐志剛、忻海洲、楊千、葉永青、曾浩、張曉剛、張小濤、趙能智、周春芽,地址:唐人當代藝術(shù)中心。
2007年由藝術(shù)史家呂澎在北京唐人當代藝術(shù)中心策劃的“從‘新具象’到‘新繪畫’”的展覽是一次關(guān)于“新繪畫”歷史脈絡(luò)的梳理,從“85時期”的“新具象”再到2007年“新繪畫”時代,其實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此時中國已經(jīng)加入WTO,市場經(jīng)濟在發(fā)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藝術(shù)市場的迅猛發(fā)展,此時“新繪畫”已經(jīng)成為藝術(shù)市場關(guān)注的熱點。
“新繪畫”的隊伍日益龐大,這不僅是當代藝術(shù)的勝利,“新繪畫”的合法化不是整體的。可是,這沒有影響它的具體成長。在兩個體制并行的情況下,“新繪畫”得到的是富于生命力的市場的支持。盡管“市場”對精神具有一般意義對毒素,可是,在那些對藝術(shù)有真正認識對藝術(shù)家來說,沒有什么比市場的發(fā)展更接近自己的目標,因為人類的所有健康的力量都是為著一個目的,通過對問題的不斷揭示而走向至善——早年“新具象”的成員和今天的“新繪畫”成員在這一點上完全是一致的。7
“85時期”的西南“新具象”繪畫充滿了哲學的意味與“生命流”的沖動,而此刻“新繪畫”面對的是全球化市場與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到來,他們沒有現(xiàn)代主義的沉重感,而是強調(diào)以一種肉身化的經(jīng)驗,冷峻理性的圖像化寫作來回應(yīng)巨變的時代,把這兩代藝術(shù)家的工作放在一起展覽,其實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對比,如果沒有“新具象”的歷史價值,也凸顯不出“新繪畫”在當下的意義,似乎他們之間就是精神上的“轉(zhuǎn)世”。
E、2008年
“革命依在繼續(xù):中國新藝術(shù)”,策展人:姜節(jié)弘 ,參展藝術(shù)家:蒼鑫、方力鈞、俸正杰、李青、李松松、李演、劉韡、繆曉春、彭禹、邱節(jié)、沈少民、石心寧、孫原、王廣義、吳山專、向京、尹朝暉、岳敏君、曾梵志、展望、張大力、張海鷹、張宏圖、張洹、張鵬、張曉剛、張小濤、張遠、鄭國谷,地址:英國薩奇畫廊。
此展可以視為國際美術(shù)館系統(tǒng)與藝術(shù)市場對中國當代繪畫的一次重要認證,也是國際當代藝術(shù)2008年的一次重要事件,20世紀90年代初薩奇畫廊在全球成功推出YBA(英國青年藝術(shù)家)一代,所以這個展覽讓人充滿了聯(lián)想。但是此展有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觀點,以政治化的視點解讀中國當代藝術(shù)一直被學術(shù)界廣泛的質(zhì)疑,這也是西方媒體對中國當代藝術(shù)解讀的一貫視點,他們不是從藝術(shù)自身的邏輯出發(fā),更關(guān)心的是作品的社會學意義,這也是一種把藝術(shù)作為政治工具的偏見,作為藝術(shù)的政治和作為政治的藝術(shù)是兩個系統(tǒng)。2008年10月美國雷曼兄弟次貸危機爆發(fā),國際藝術(shù)市場受到重挫,2009年薩奇畫廊在香港開始拋售中國當代藝術(shù)家作品,2011年比利時大收藏家尤倫斯在香港蘇富比拋售中國當代藝術(shù)作品37件,這也是當年國際藝術(shù)市場的一個重大事件,可見“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既參與了當代藝術(shù)的國際化的進程,趕上了全球藝術(shù)市場關(guān)注中國的黃金期,也經(jīng)歷了由于國際經(jīng)濟蕭條所導致的當代藝術(shù)市場的震蕩,這也是“新繪畫”走向國際化征途的必然遭遇。
繪畫的抗體
20世紀90年代末“新繪畫”面臨的最大的語境變化是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到來,媒體的激烈變革、消費時代“景觀社會”到來,每一位藝術(shù)家必須面對變動的時代,可以說“新繪畫”是在一個時代和媒體都在劇烈變革的雙重困境下突圍的,“新繪畫” 的實驗,一開始就是走向了“圖像生產(chǎn)”的觀念化思考,他們在“繪畫的死亡”的語境與全球新媒體浪潮“大兵壓境”下絕處逢生。
我想通過對今天中國當代“新繪畫”的語言表征來揭示和呈現(xiàn),在圖像和語言下的方法論和美學轉(zhuǎn)向,以及中國當代社會的精神癥候。“新繪畫”吸收了裝置、影像、多媒體、大眾傳媒等媒介的視覺經(jīng)驗,它們從社會學、歷史文脈、當代現(xiàn)場、像素圖像時代、網(wǎng)絡(luò)、動漫、卡通、流行文化等方面延伸,繪畫的邊界在打破,繪畫以他者的身份重新回到當代藝術(shù)的現(xiàn)場了。8
“知識譜系”與“圖像譜系”成為“新繪畫”藝術(shù)家強調(diào)的觀念和方法,他們的圖像不是來自于歷史經(jīng)驗和記憶,往往來自于現(xiàn)場與互聯(lián)網(wǎng)中的碎片化經(jīng)驗,如日常生活片段,他們追求的是“無意義、無敘事、無符號”的“零度寫作”,繪畫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繪畫的邏輯,這是2000年以來“新繪畫”藝術(shù)家的最大的變化,他們遠離了20世紀80年代的“宏大敘事”,90年代初的“日常敘事”,2000年以來他們更多的是一種“微觀敘事”,一開始就背離了政治化、符號化的繪畫,把繪畫作為一種圖像和觀念的通道。“新繪畫”與攝影和影像的關(guān)系更緊密,這與新媒體藝術(shù)的觀念和視覺的沖擊有關(guān),所以他們在自己的語言實驗中走向了上一代藝術(shù)家的反面。作為表征的語言,語言既是觀念,觀念也是語言,圖像修辭方法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們更注重工作方法,重建圖像與肉身的聯(lián)系,偏離了社會學意義的含義。“新繪畫”藝術(shù)家作品往往是一種肉身經(jīng)驗的表達,是燃燒的肉身,他們的圖像不是苦思冥想的觀念與點子,也不是從社會主義歷史記憶圖像的挖掘,比如“青春殘酷繪畫”就是對現(xiàn)場中人性的血淋淋刺痛表達,是一種碎片化的記錄和見證,他們把繪畫視為圖像寫作,媒介不重要,重要的圖像背后觀念與方法。
空間中的實踐
在全球化的時代,當代藝術(shù)實踐同時體現(xiàn)出審美與政治的雙重力量……9
“新繪畫”的成長得益于2001年中國加入WTO,隨之成為世界加工廠,因為經(jīng)濟的騰飛GDP高速增長,國際資本開始關(guān)注中國當代藝術(shù)市場,隨之中國的藝術(shù)空間與藝術(shù)市場也開始劇烈的變化。 2002年春藝術(shù)家黃銳帶領(lǐng)日本東京畫廊的田畑幸人來到了798(原為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lián)、東德援建的國營798廠等電子工業(yè)的老廠區(qū)所在地),打開廢棄的空車間時塵埃飛舞、滿地狼藉,2002年10月獨立策展人馮博一策劃的“北京浮世繪”展覽在北京東京藝術(shù)工程開展,該展是798歷史上第一個當代藝術(shù)展覽,打響了798成為一個國際藝術(shù)區(qū)的“第一槍”。最早進入798的藝術(shù)機構(gòu)所承擔的房租是0.65元/天/平米,陸陸續(xù)續(xù)“長征空間”、羅伯特 TIME ZONE8書店、“Art-caf锓料閣子藝術(shù)家工作室”“時態(tài)空間”“百年印象”等機構(gòu)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xiàn)出來。北京798最初的規(guī)劃是電子元件城,后來由人大代表清華美術(shù)學院教授李向群等人提議798作為社會主義工業(yè)歷史遺跡的重要性,798藝術(shù)區(qū)才得以保留。
2003年在SARS期間,馮博一與舒陽策劃的“藍天不設(shè)防”的觀念藝術(shù)活動標志了798藝術(shù)區(qū)完成了一次轉(zhuǎn)換和升華——藝術(shù)區(qū)與公共空間、與社區(qū)之間有了互動關(guān)系,并且藝術(shù)家也積極地應(yīng)對社會事件。早期進駐798的藝術(shù)家有:黃銳、徐勇、趙半狄、吳小軍、劉野、張小濤、馬樹青、石心寧、蒼鑫、付磊、毛栗子、陳文波、史勁淞、陳羚羊、孫原、彭禹、刑俊勤、李松松、隋建國等。早期798的藝術(shù)家們過著波西米亞式的集體生活,大家在一起AA制輪流聚會,講段子,從日常聚會再到日常生活都很有一種烏托邦的感覺,這是一幫逃脫體制來尋找理想的人。什么是江湖?就是無組織有紀律的生活。尤其非典期間藝術(shù)家之間不論是生活還是工作的聯(lián)系更為緊密,可以看作是藝術(shù)家對這個時代的回應(yīng)。非典期間的“藍天不設(shè)防”活動,2003年春時態(tài)空間的“再造798”,以及2003年北京雙年展期間,時態(tài)空間的“左手右手——中德當代藝術(shù)交流展”“水刀切割”、798料閣子藝術(shù)家的“摸也摸得也摸不得”工作室開放展等都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發(fā)現(xiàn)這與早期藝術(shù)家在圓明園藝術(shù)圈的地下活動有了本質(zhì)的變化,當代藝術(shù)和社會之間變得更加互動,并且社會和公眾也對當代藝術(shù)不那么持反對的態(tài)度,變得開放起來,寬容了許多。
2006紐約蘇富比春拍推出“亞洲當代藝術(shù)專場”是中國藝術(shù)市場升溫的巨大信號,張曉剛的作品拍賣價格高達97萬美金為中國藝術(shù)市場吹響了號角。這是一個急劇變革的全球化時代,空氣中到處充滿了銅臭味,用“狼煙四起”來形容此時798的藝術(shù)空間也不過分。尤倫斯、常青畫廊、北京公社、佩斯北京、林冠藝術(shù)中心、唐人藝術(shù)中心、伊比利亞當代藝術(shù)中心、意大利馬蕊娜畫廊、德國空白空間等大型機構(gòu)蜂擁而至,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蛋糕——全球化背景下中國藝術(shù)市場的未來。這是一場盛宴,如果我們把2005到2008這幾年瘋狂的中國藝術(shù)市場比作一個原始叢林,上演的全是大自然物競天擇的故事。
現(xiàn)在“全球”經(jīng)濟已成為我們生活中理所當然的事,跨國公司和跨國經(jīng)營是要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chǎn)效率,這種為追逐最高利潤而在全球范圍內(nèi)再次調(diào)整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方案,將重構(gòu)我們多少世紀以來熟悉的社會與文化。10
如果我們把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作為當代藝術(shù)市場的分水嶺,可以看到藝術(shù)區(qū)與藝術(shù)市場都開始變得理性,比如尤倫斯藝術(shù)中心、佩斯北京、常青畫廊、林冠藝術(shù)中心等機構(gòu)都帶來了高品質(zhì)的學術(shù)展覽。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國際展覽讓我們體會到了國際化已經(jīng)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9年全球Artprice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中國藝術(shù)品市場占到全球的18%,英國藝術(shù)市場占全球20%,美國藝術(shù)市場占全球的44%,通過數(shù)據(jù)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未來的藝術(shù)市場前景巨大。當然藝術(shù)市場更需要規(guī)范和理性的回歸,需要建構(gòu)理性的藝術(shù)生態(tài)和制度,這樣才有真正的未來。“新繪畫”的部分藝術(shù)家也是在798這個藝術(shù)空間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參與了這個“藝術(shù)市場神話”的崛起的歷史時刻,798作為社會主義工業(yè)廢墟,具有包豪斯風格,這對中國當代藝術(shù)來說是一個“激活的叢林”,藝術(shù)家既是這里的演員,也是觀眾,他們參與到這個時代的洪流之中,這也是“新繪畫”的意義,他們不只是“圖像生產(chǎn)”,而是“空間生產(chǎn)”。798藝術(shù)區(qū)現(xiàn)象是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重要見證,也是作為全球化市場與藝術(shù)區(qū)的縮影,2005-2008年中國當代藝術(shù)井噴現(xiàn)象也讓“新繪畫”進入到一個更加廣闊的國際流通與傳播系統(tǒng)中,這也是“新繪畫”一代從20世紀90年代處于地下的默默無聞,到2000年以來進入公眾視野,2008年經(jīng)歷藝術(shù)市場的巔峰,再到今日的沉寂,這個過程也是“新繪畫”介入當代社會現(xiàn)場實踐的證明。
“新繪畫”的啟示
今天我們回看20世紀90年代初期至2000年川美“新繪畫”一代,他們從 80年代的“宏大敘事”、90年代的“日常敘事”轉(zhuǎn)向了2000年以后的“微觀敘事”,這其實是一種“圖像自治”與美學轉(zhuǎn)向,是“微觀政治”與反符號化傾向的工作,雖然今天的“新繪畫”都不在權(quán)力系統(tǒng)與拍賣市場作的體系里,他們的工作是被遮蔽了的,2008年以后藝術(shù)市場受到重挫,加之,國際藝術(shù)市場的震蕩和國際大畫廊加入中國本土藝術(shù)市場的角逐,本土畫廊的力量顯得式微。雖然“新繪畫”藝術(shù)家們的工作還在持續(xù)推進之中,但是被學術(shù)界和市場的關(guān)注就變得少了起來,這是一個必然,然而事物都是在變化之中,我們可以“揀盡寒枝”梳理歷史,但是無法預(yù)知未來。他們作為歷史現(xiàn)場的回響,作為見證者、記錄者、參與者的工作有獨立性的價值,此刻“新繪畫”成為了社會現(xiàn)場與藝術(shù)空間的中介之物。
關(guān)系藝術(shù)是一種將人類互動及其社會脈絡(luò)所構(gòu)成的世界當成理論水平面的藝術(shù),而不限于只是宣稱某種自治或私密的象征時刻,這種藝術(shù)證實了對于現(xiàn)代藝術(shù)所操弄的美學、文化與政治目標進行徹底顛覆的可能性。為能從中描繪出一種社會學面貌,這種演變變更為根本地源自某種世界都市文化的誕生,以及該城市樣式朝向文化現(xiàn)象總體的延伸。11
川美“新繪畫”一代曾經(jīng)參與了中國當代藝術(shù)的進程,這些都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需要來重新去梳理和討論,他們的圖像方法、觀念和語言的變化有什么樣的貢獻,這些是值得后來者去思考和研究的。每一代人最終都會成為歷史的塵埃,但是傳奇是不朽的,我們?nèi)绾蜗蚝髞碚咧v述20多年前“新繪畫”的歷史,這是一種學術(shù)的良知。2021年3月藝術(shù)史家呂澎博士在四川美術(shù)學院美術(shù)館策劃的“川美:‘新繪畫’的一代”展覽、論壇及出版是一次重新發(fā)現(xiàn),目前“60后”“70后”“新繪畫”的實踐者們不在權(quán)力和資本的系統(tǒng)中,他們用自己持續(xù)的觀念與語言實驗?zāi)鼗貞?yīng)了一個時代的巨變。這次展覽既是關(guān)于“新繪畫”歷史的文獻梳理;也是重新發(fā)現(xiàn)被遮蔽的實驗的過程;此次展覽是對中國“新繪畫”的國際化、本土化、獨立性實踐的反思與總結(jié);是一次鉤沉“新繪畫”往事的“事件”;是與20多年前在巨變現(xiàn)場中博弈的“圖像生產(chǎn)者”的一次會面……
注釋:
1.[法國]居伊 · 德波,《景觀社會》,南京大學出版社,第一章第4頁。
2.張小濤,《繪畫的抗體》,《藝術(shù)當代》,2006年第2期,第68頁。
3.王林,《陌生情景與都市人文主義》,《陌生情景》展覽畫冊,1994年。
4.栗憲庭,《陌生情景——內(nèi)心意象化的現(xiàn)實》,《陌生情景》展覽畫冊,1994年。
5.王林,《精神批判在當代的意義——“中國經(jīng)驗”畫展序言》,《中國經(jīng)驗》展覽畫冊,1994年,第11頁。
6.黃專,《視覺的力量》,《上河美術(shù)館99學術(shù)邀請展》展覽畫冊,1999年,第3頁。
7.呂澎,《從“新具象”到“新繪畫”的歷史》,《從“新具象”到“新繪畫” 》,湖南美術(shù)出版社,第39頁,2007年。
8.[法]卡特琳娜· 達維特,《第十屆文獻展歷史概述》,《卡塞爾文獻展50年——移動的檔案館》畫冊,2005年英、德語版,第344頁。
9.同注2。
10.[日]三好將夫,《全球經(jīng)濟中的抵制場》,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先鋒譯叢6《全球化癥候》,第2頁。
11.[法國]尼古拉斯·伯瑞奧德,黃建宏譯,《關(guān)系美學》,金城出版社,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