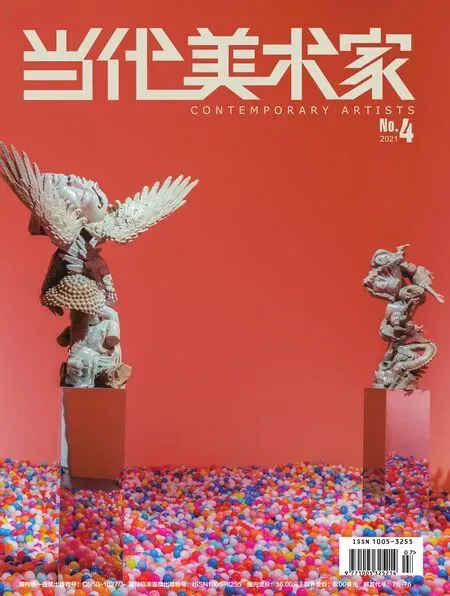藝術與哲學是相互要求的1
孫周興
《當代美術家》(以下簡稱“當”):通常大家認為科學代表理性,藝術代表感性,您作為哲學學者,又特別關注當代藝術和當代藝術理論,可以說在藝術與哲學之間游走,您認為哲學是理性的還是感性的呢?還有,藝術與哲學的關系如何?
孫周興(以下簡稱“孫”):哲學當然是偏理性的,這是哲學的基本特質所要求的。哲學需要給世界提供一個合理性的說明和論證,包括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對我們自身的行為做出合理的論證或辯護。這是哲學的基本任務。簡單來說,哲學就是講道理,講道理需要論證,要說出一二三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肯定是理性的。但是我們也看到,在19世紀中期以來,在歐洲出現了另外一種哲學,反對二千年來的理性主義哲學傳統,甚至主張非理性、轉向感性。不過,這依然沒有消除哲學的理性本質,它的講道理的特點。再說了,感性與理性之分也是傳統哲學的習慣,是歐洲的分析傳統,但這種區分本身是不確當的,其實哪里區分得清楚?
哲學為什么必定是偏重理性的呢?因為哲學說到底就是“觀念構成”方式,是“觀念構成”的主要方式。“觀念”(idea)是普遍的和形式的,所以傳統哲學的主體是“普遍主義”的。傳統哲學的基本方法是邏輯論證,是要努力推脫所謂“感性”層面的;但即使是后來出現的“反哲學的哲學”,也必須堅持“論證”,雖然論證的邏輯性大大減弱了。要說區別,我認為自尼采以來的現代哲學,與傳統哲學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就是邏輯性大大減弱了,也不太講論證了——我稱之為“弱論證”。哲學必須有論證,哪怕是“弱論證”,不然就失去了哲學的本分,就不能叫哲學了。
這種情況也表明,藝術與哲學之間的關系已經發在了根本變化。除了邏輯推論和論證,哲學也開始用藝術方式來表達自己了,也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藝術性,典型的人物還是尼采和海德格爾等。盡管如此,哲學不必干脆變成文學和藝術。在20世紀的人類文化格局中,我們看到藝術與哲學關系的一次重構,我稱之為“藝術哲學化”與“哲學藝術化”。“哲學藝術化”我們講了一點,所謂“藝術哲學化”也是很明顯的,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當代藝術中尤為明顯,不然我們如何理解“觀念藝術”呢?
一句話,情況變了,在今天,藝術與哲學是相互要求的。
當:藝術的發展與科技關系密切。在科技使日常生活發生巨變的今天,有的藝術家選擇以原始美術、部落美術作為出發點進行創作。原始美術有著我們在今天無法參透的意義,也是觀念的、抽象的。您覺得藝術的發展會不會形成輪回呢?
孫:原始美術這個說法恐怕不是特別適當。我的意思是,原始藝術不光是美術,美術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在早期希臘,有建筑、雕塑,當然也有繪畫,但已經消失了,沒能流傳下來。更主要的是,早期藝術更多的是說唱藝術,諸如傳說、史詩之類,主題內容是神話,每一個古老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神話體系,而且主要是借助于早期藝術來形成的。
19世紀中期以來,隨著現代文明和技術工業的推進,歐洲藝術中重新出現了所謂的“原始藝術”。一方面是因為當時歐洲接觸到許多非歐洲的民族和原始部落的文化,另一方面是因為有一些先知先覺的藝術家和哲學家發現技術工業把自然人類原本的生活世界破壞了,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所以要回歸原始藝術,所以藝術大師理查德·瓦格納的口號是:通過藝術重建神話,主張通過藝術神話來抵抗技術工業的高度透明化、高度理性化、高度規則化傾向。之后在藝術領域里一直有一股很重要的勢力,一些藝術家努力使藝術回歸神秘、回歸原始、回歸神話。這種思想的基本假設很簡單,他們認為技術工業把我們自然人類的生活世界搞得越來越規則,越來越理性,越來越無聊,越來越無趣了。瓦格納認為一個沒有神話的世界是無法忍受的,是無趣的。當然這里的神話是廣義的,不是過去時,而是當下生成的,是指我們生活世界里不可消除的神秘性。總的來講,從19世紀中期到今天,一百六七十年的現代文明進程中,尤其是德國,這種傾向發展成了主流藝術的一種,包括表現主義、新表現主義,特別是在戰后德國當代藝術中,好些藝術家主張這種神話性和神秘性,試圖用非科學和非技術的方式來理解這個世界。這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我把它叫做當代藝術對技術工業世界的抵抗。
中國當代藝術也存在這個現象,有很多藝術家試圖對我們的古代神話進行再造和重建,比如《山海經》。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意識到我前面講的歐洲19世紀中期的思想背景。倒不是說一定要回歸早期的原始藝術,相反,著眼點仍然在當代,是要追問:徹底技術化、加速技術化的生活還對頭嗎?
當:當代藝術創作的觀念性越來越強,當代觀念藝術的意義到底在哪里?還有,藝術創作甚至成為團隊型的工作:藝術家提出理念,由一個團隊共同完成。藝術創作的技術,在今天這一概念發生了什么變化?
孫:今天我們面臨著文明的巨大變化,從自然的人類生活向技術的人類生活過渡,這是一個基本趨勢,似乎已經無法挽回了。我稱之為“技術統治”。然而藝術家的工作主要是要完成對“技術統治”這個基本趨勢的抵抗,在此意義上藝術一直是有意義的,而且變得更加重要了。這里包含著兩面性,一方面,我們要努力保護自然人類的手工性和身體性,另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技術工業的統治是無法遏制的,這大概是人類的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現代技術加速發展,雖然它是人類的產品,但已經脫離了人類的控制。可以說技術已經不是人類可以掌控的東西了,它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主調。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得承認,藝術只是給出一個必要的抵抗姿態。
我一直要強調藝術的根本特征是創造奇異的東西,也可以說是奇奇怪怪的東西,不是我們日常同質化的東西,而是新奇的東西,我把它稱作“奇異性”。我說人類未來文明越來越需要藝術,為什么呢?我的邏輯很簡單:技術工業根本上是一種同質化的力量,要把一切都變成一樣的,周邊的技術物是一式的,人也變得越來越一樣了。技術和媒體正在全方位地改造人類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樣子。今天我們還處在人的自然性和技術性兩種關系交織的時刻,但技術性的成分越來越加強了。可能我們看起來還是自然人,但實際上已經大打折扣。現在技術工業已經把我們的身體包括體質都改變過了,特別是通過化工、醫藥,把我們的身體改造得七零八落。我們的自然能力,包括生殖能力都大幅度下降,甚至加速下降。我們需要一種力量來保護人的自然性,這個保護本身就是對技術同質化力量的抵抗。我想未來最好的狀態是自然性和技術性之間取得某種平衡。
如果當代藝術有了這樣一種新使命,那么它就必須突破傳統藝術概念。傳統藝術是手工性的,是自然人類的手工勞動,我們把手工勞動產品的姣姣者稱為“藝術作品”。但今天不一樣了,今天我們處身于技術工業世界中,手工勞動漸失意義,觀念的創新變得更為重要了。但這里必須對“觀念”做一種新的理解。“觀念”就是行動,或者說心動就是身動。這是現象學哲學的一個新見,特別有意義。
今天焦興濤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現在的藝術變成了一種行動的藝術。藝術家提出一個奇異觀念,但不只是通過他一個人來完成。現在許多藝術行為都是集體完成的,尤其是行為藝術。藝術首先是觀念藝術,但這個觀念是行動的觀念,是介入性的觀念,是博伊斯所謂“社會雕塑”意義上的。如果藝術不能改變生活、改變社會,還有什么意義?他認為每個個體都是創造性的個體,都是社會改造的力量,如果沒有這些,藝術的意義也就沒有了。博伊斯對藝術有很高的要求,那就是行動的要求;此前以及同時的存在主義(實存哲學)也對哲學提出了同樣的要求。我們必須要有力量去改造,通過藝術和哲學改造社會。就此而言,我們又回到了前面的話題:藝術與哲學是相互要求的。
當:您曾說過哲學家很無趣,但同時您又詬病當下的年輕人不愛讀哲學。您主張年輕人和創業者需要多讀哲學嗎?哲學對藝術和創新的作用是什么?
孫:你肯定誤解我了,我絕對不會埋怨現在的年輕人不愛讀哲學,為什么一定要讀哲學呢?我在中學里做過幾個報告,其中一個報告談到這個問題,你大概看了這個報告的記錄稿,但你誤解了我的意思。我去中學里講哲學,根本不是要勸年輕人學哲學。相反,我認為年輕人是不適合學哲學的。尤其是傳統意義上的哲學,總的來說是一門高冷的學問,與生活本身有隔膜,其基本方式是反思和批判。年輕人朝氣蓬勃,富有想象和創造力,還沒到反思和批判的時候。再說了,現在是商業時代,掙錢要緊,活下來要緊,而在所有行業中,哲學應該是離商業最遠的一個行業,沒有之一吧?這個時候,我能勸告學生學哲學么?
這些年也有一些成功人士來學哲學,我自己就招收過好幾位五十多歲的博士生,特別好,有的已經順利畢業了。也有的成功人士聲稱:我事業這么發達,主要是因為學了哲學。這是有可能的。因為哲學是大尺度的思維,學哲學的想問題比較開闊,這對于做大事者應該有所幫助。但我仍舊愿意認為,少數的成功案例還不足以表明通過哲學可以謀生。對大部分年輕人來說,先掌握謀生手段是第一件事,是當務之急。以后如果事業有成,再來學點哲學也不遲。學習是終身的,哲學更是終身的。
于是大家就可以理解,現在我們大學哲學系本科-碩士-博士招生往往是一種“倒掛”的局面:本科最難招生,我們經常招不滿;碩士考生會多很多,但許多不是哲學專業的畢業生;博士生招生最熱鬧,各個年齡段的公民都有,要考上難度很大,我所在的哲學博士點經常是七八個考生中錄取一名。這實在是太難了。但我認為這樣很好,很正常。你什么時候開始學哲學都不遲,對年輕人來說,當下的生活是第一位的。要記住,讀書是為了生活更美好,如果說生活是為了讀書,那就差矣。
我還想說,對于生活的創造來說,藝術可能是更有用的。這也是當代藝術概念提供給我們的啟示:生活就是創造,就是革命,就是解放,就是藝術。我記得這是博伊斯給出的一個等式。不過我們依然要明白,正如藝術是無所不在的,哲學也是普全的觀念構成方式,只要我們一思想,只要我們一說話,我們就開始哲學了。
注釋:
1.2021年4月18日參加四川美術學院“技術世界與多維未來——第四屆哲學·藝術·科學論壇”時接受《當代美術家》雜志的采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