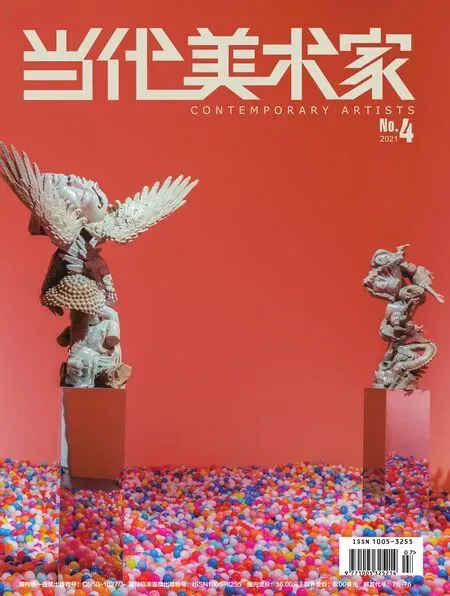藝科交叉·設計責任
呂曦
1974年愛因斯坦提出了相對論,而畢加索在討論立體運動,兩位大師一位用數學定義,一位用繪畫和雕塑,從不同的視角討論時間和空間的問題。從創造性上來講,科學家和藝術家沒有本質區別。龐茂琨教授的《第二次觸摸》畫作中,將文藝復興時期卡拉瓦喬的《圣徒托馬斯的懷疑》的局部人物替換成機器人,反映出數字化、智能化時代里,我們對人機關系的好奇、困惑和焦慮。近些年,關于人工智能與藝術實驗探討越來越多。“下一個倫勃朗”項目中利用人工智能對364張倫勃朗畫作中的人物性別、衣領、胡須、年齡、帽子、面部向右等特征進行識別和運算,生成并且推斷了下一張作品可能的面貌。關于這件AI創建的作品,網絡上有人開玩笑說,難道這是一個通用藝術模仿器?
在新的時代語境下,設計的內涵與外延已經完全超出了傳統專業目錄的描述。生物設計、體驗設計、組織設計、響應式設計、思辨設計、計算設計……從這些描述來看,設計對象越來越復雜,設計的邊界也呈現出越來越多交叉融合的模糊性。從1959年到2015年,對于“設計”的定義、目標甚至設計組織名稱的變化上,可以看到大設計理念的發展變化。設計學院圍繞社會主題型設計教育,希望構建從一個微觀到中觀到宏觀的教學體系,將民生經濟、社會問題、行業趨勢和產業技術等融入到各個不同階段的課程中,在社會主題命題下喚醒和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設計和數據。DIKW是在信息科學和知識管理方面非常經典的模型,而這個模型第一次出現卻是在1934年艾略特的詩歌《The Rock》中:“我們在哪里丟失了知識中的智慧,我們又在哪里丟失了信息中的知識”。有意思的是,美國20世紀60年代搖滾音樂先鋒人物弗蘭克·扎帕也在歌曲中提到“信息不是知識,知識不是智慧”。娜塔莉·米巴赫收集了大量的氣象和天文數據,并將這些抽象數據詮釋成色彩斑斕的三維編織作品,隨后與音樂家合作改編成了樂譜進行音樂演奏。瑞典統計學家漢斯·羅斯林以200年中200個國家的公共衛生數據,動態展示了全球經濟與國民生活質量的變化,用生動的數據來講述世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發展。不同的學者對抽象數據的復雜性呈現了不一樣的思考和表達。對于藝術院校來說,我們通過各種課題訓練讓學生感受和理解數據、信息、知識與現實社會生活的聯系。
設計和智能交互。這個智能手環設計案例是用傳感器和手機應用來實現小朋友的想象力。他們只要帶上手環,通過藍牙連接智能手機,傳感器就能分析孩子們的動作,讓家里的每樣東西發出與他們的動作相匹配的虛擬音效,變成有趣的玩具。我們可以設想數字智能產品如何豐富人與人的交流,如何建構新型的關系。我們的設計課題里會聚焦到工作和生活場景來建立對技術的認知,所思考的不完全是技術本身,更希望去建立完整的設計思維,去探查人的行為和需求,讓創意和技術能夠很好地貼合起來。在和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智慧出行”校企聯合課程中,我們共同去理解社會、經濟、技術以及文化對整個人類生產和生活方式產生的影響,從廣義交互的理念探索人、車、路、網的關系,以此來發現更多的未來設計可能性,這也是華為公司當時和我們合作中特別贊賞的一點。
設計和AI。在達利博物館的沉浸式項目案例中,最有價值的可能不是如何訓練AI的算法來學習和模擬達利,而是這些技術產品嵌入了真實生活后給人們帶來的驚喜。對于中國文化傳承的標志之一的漢字,我們也進行了AI+創意實驗式探索。在中國傳統書法書寫中,即便同一個字也有不一樣的形態和情緒,因此呈現出令人沉浸的藝術之美。我們嘗試用對抗式生成神經網絡算法,將AI作為一種協同工具進行字體創意設計。機器學習會呈現出具有算法特點的特征結構與形態,我們會利用設計師進行篩選后再設計,在此基礎上再進行計算生成。
關于社會責任。這些年團隊開展了為安全而設計、醫療健康設計等課題研究。我們嘗試去了解醫療服務的特點,從醫護全流程去理解醫患雙方的行為與需求。在整個過程中,設計需要在真實場景里從任務、目標及人的行為等整體交互關系當中探討設計原則和設計方案。在關于殯葬服務設計的研究中,內地殯葬服務無論是服務形式還是商業模式都顯得非常的邊緣化和滯后,面對這樣一個錯綜復雜的系統性問題,我們設想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來搭建一個合法、合理、合情的第三方整合式服務平臺,用暢通的渠道和可選擇的服務來平衡多方利益關系,最終的核心還是問題意識的培養、同理心的建構以及社會責任意識的提升以重新審視設計的價值。
在老年智慧康養的課題研究中可以看到,很多可穿戴設備、慣性傳感器、VR+EEQ+tDCS等都可以應用在相關疾病治療上,一些高校也正在進行新技術的探索。很多老人生理上退化,被孤獨環繞,失去活力,失去認知,到最后失去尊嚴,現實場景里的很多問題卻并不是簡單用技術能去解決的。很多設計在源頭上并不是以尊嚴和體驗為中心,我們需要反思究竟什么是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設計不光要考慮個人的即時體驗,還應該考慮更長遠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建構。在這樣的理念下,我們希望將醫患雙方體驗置于設計過程的中心,并與臨床目標和過程保持一致,最終能夠使雙方獲得更多的尊嚴感和獲得感,從而回歸醫學本質,提升醫學人文溫度,創造出更多人本的、人性的設計改良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