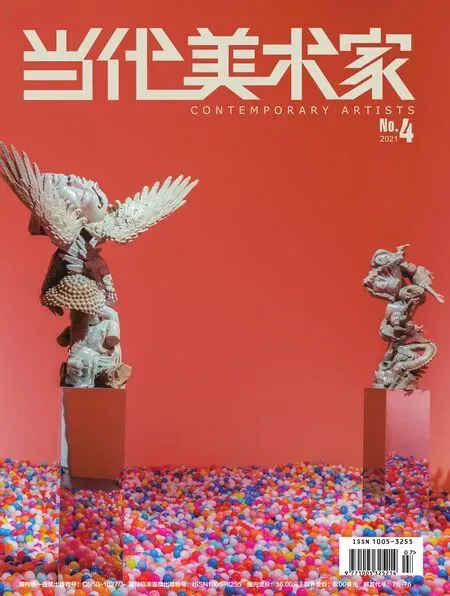水——對話蘇珊·維克多
蘇珊·維克多 韓晶

1蘇珊·維克多(Suzann Victor)擊打2021“水”(Of Water)新加坡泰勒版畫院( STPI -Creative Workshop & Gallery,Singapore)展覽現場圖片經新加坡泰勒版畫院惠允
水
2021年4月25日—5月9日
展覽地點:新加坡泰勒版畫院畫廊
(STPI Gallery)
韓晶(以下簡稱“韓”):您的藝術生涯長達20多年,從抽象派畫家到成為新加坡第一位參加49屆威尼斯雙年展的女性藝術家。您認為您20多年的藝術創作生涯可以劃分為具有代表性的不同階段嗎?
蘇珊·維克多(以下簡稱“蘇”):謝謝您的問題。雖然我可能不是有意認識到這點,但是回顧我迄今為止的職業旅程,我能看到我的藝術實踐確實呈現出了不同的創作階段,它們與主題表達的內驅力、意圖有關,由此我發明了新的技法,或是將資源“重新物化”為新的創作方式。 話雖如此,但我的藝術實踐可以,并且仍然應該被視為一個連續體。
韓:您對水這一創作媒介表現出了持續的興趣,水的哪些特質吸引了您?請結合具體作品談談水的特點與作品表達主題的聯系。
蘇:是的,對我來說,水的實踐可以說是一個超鏈接,在我的藝術實踐中引導我們完成了一串連續的標志性藝術作品。它是一種情感材料,因此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藝術創作手段,能夠帶來令人驚異的變形和深刻的意義。但同時它也很危險,比如我在新加坡泰勒版畫院用水和酸作畫時創作的“啐-噬系列”(Spit-Bite Series)以及《靜水(在 1995 年的疏遠與和解之間)》(Still Waters),以此來展示我在新加坡美術館下水道空間中進行的行為藝術,因為當時對行為藝術表演的禁令仍然存在。正如《靜水》展示的那樣,它是一項沉浸在專業和創造性風險中的社會實踐行為,利用水和新加坡美術館的建筑來批判自身,尤其是她作為新興區域的藝術權威角色與當時新加坡藝術形態之間的緊張關系。對我來說,鑒于邊界的短暫特性,無論它們是個人、社區或國家的,《靜水》回應了(并希望有助于糾正)藝術與文化生產作為應對公共危機和動蕩時期的一種手段的相關重要問題。
沒想到,21年后,也就是2019年,《靜水》被評選為新加坡M1藝穗節的主題,吸引了國際戲劇從業者用自己的作品為當今觀眾詮釋原創表演——可能公眾并不一定認識到當時政治對行為藝術產生的影響。M1藝穗節不僅認可了該作品的歷史意義,而且還承認了它與新一代的相關性,這讓我感到自己的渺小。 因此,在這樣的情形下,它似乎告訴我們,一件作品會隨著它的觀眾或公眾的變化而發生變化,改變自身的意義和相關性。

2蘇珊·維克多(Suzann Victor)&馬丁· 柯克伍德(MartinKirkwood)水中火焰2021“水”(Of Water)新加坡泰勒版畫院( STPI -Creative Workshop & Gallery,Singapore)展覽現場圖片經新加坡泰勒版畫院惠允
另一件作品可能與我的藝術實踐使用水的方式形成對比,那就是《彩虹圈》,它是為 2013 年新加坡雙年展委托創作的。在這件作品中,我使用水來創作無對象的藝術——一件能產生雙彩虹弧出現的氣象裝置,這件裝置作品位于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圓形大廳的封閉式殖民建筑內,而不是彩虹通常出現的開放景觀空間。這件作品試圖通過想象一個已經過去的未來來回應雙年展的主題——“如果世界改變了”。氣候變化威脅著彩虹這一自然現象的持續存在,所以,在這件作品中,彩虹出現在博物館的背景中,與這些文物并置在一起,成為眾多歷史文物之一。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那將是災難性的。
韓:您以實驗的方式回應和顛覆了傳統版畫,創造了表現物質和思想的新方法。 除了水之外,您還嘗試使用其他材料或媒介進行創作嗎?
蘇:謝謝!這是一個很棒的問題。是的,我一直在探索使用菲涅爾透鏡,首次使用是1997年第六屆哈瓦那雙年展上展出的《第三世界特級原始之夢》; 2015年再次使用菲涅爾透鏡來創作 《2015 和平血統》(為新加坡美術館舉辦的五星級展覽委任創作),這是一條由 11500 個鏡頭組成的40 米長的被子,每個鏡頭中都有一滴人血。
血液能賦予生命,因為它實際上是活的。作為有生命的物質,它在被提取和收集時充滿了各種細胞物質。鮮血也是生命的力量,當它被野蠻和侵略、暴力或沖突、死亡甚至戰爭的力量拖拽時,就會流淌而出。然而,免費獻血可以挽救親人,甚至是有緣陌生人的生命。作為一種犧牲生命的行為,流血的深刻性是一個人可以為同胞和國家做出的最高犧牲,這似乎是實現和平的一種方式。我認為和平是一種很珍貴的狀態,只能由缺席來定義——沖突、戰爭和流血的缺席。在這樣的情形下,可以說《和平血統》最初是一件有生命的藝術品,一份鮮活的生物遺物,因為血液是可以單獨存活一段時間的。為這件作品獻上的鮮血之禮來自一些重要群體的代表性個體,通過集體合作,在新加坡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的50周年之際,他們表達了和平狀態的脆弱與珍貴。這份珍貴的體液還包含了個體捐贈者的細胞和DNA樣本,這些材料現在由美術館保存。

3蘇珊·維克多(Suzann Victor)彩虹圈——捕捉的自然現象水、陽光、管道、日光反射鏡、太陽能電池板尺寸可變2013年新加坡雙年展展出作品新加坡國家博物館圓形大廳圖片攝影:馬丁· 柯克伍德(Martin Kirkwood)
最近,我用這些透鏡為在東京國立藝術中心和森美術館舉辦的展覽“太陽雨”(Sunshower) 創作了《面紗——像離經叛道者一般觀看》(2017),這件作品截取了立體視覺,通過對這種材料的感知效果來進行觀看和感受,并以此質疑我們的主觀性習慣。這種材料就像那些植入的慣例化語境一樣放大、撕碎、扭曲了展覽周邊的內容。隨后,福岡亞洲藝術博物館授予我此次展覽的“特別駐地獎”,并委任我創作作品作為東南亞藝術家對福岡的回應。為此,我呈示了兩件戶外作品——在有著一千年歷史的凈天寺展出的《千空》(2017) 和福岡城遺址展出的《升起的太陽》(2018),它們對菲涅爾透鏡進行了更深入的運用。這兩件作品為觀眾提供了一種迷人的觀看、感知自然環境的方式。
當年,我得知我的密友意外(也是創傷性地)了解到她祖母在十幾歲時曾是被日本軍隊脅迫的慰安婦,我創作了一系列作品來紀念她。用圓形透鏡放大她祖母的人類精神、尊嚴和韌性的壯麗,這不僅是面對強加的恥辱、禁忌,在自我放逐或其他情況下喚起的深刻的生存勇氣,而且證明了她精神與勇氣的連續傳承。她的孫女就是最好的例證,她告訴了我這些,并且還向我們揭示了委婉表達的“慰安婦”一詞是修正主義敘事在平庸的舒適和感知的距離中產生的,有謬誤和不準確之處。但事實上她可以離我們很近,很有可能就是我們的熟人、鄰居、同事、親戚、朋友、家人——比你想象的更近。她不是別人的問題,她就是我們的問題。
韓:此次展覽展出的關于水的三件作品之間有著怎樣的聯系?它們表達了怎樣的理念?
蘇:受國際項目“畫廊——策劃RHE”委任,展覽“水”由馬克·格洛德 (Marc Gloede) 策劃。展覽中的兩件新作《擊打》(2021)、《水中火焰》(2021)和早期作品 《波特酒——包含羅曼史》(2015)通過想象的水的特質與聲音特點在概念和體驗上是相互聯系的,而水的這些特質與我們作為觀眾的感知與感知存在深度、復雜性是聯系在一起的。通感,即激活一種感覺通路,同時會不由自主觸發另一種感覺通路的感知現象,它在本次展覽的概念中非常突出。也就是說,人們在觀看《波特酒——包含羅曼史》的二維圖像時會“聽到”聲音,而在聽《水中火焰》的錄音時會受到圖像的沖擊,這是一個將機構空間轉變為共鳴室的裝置。從產生的可見來源中提取的聲音能夠激發聯想的想象力,以此完成一幅神秘或平凡的畫面。在這件作品中,我與藝術家馬丁· 柯克伍德(Martin Kirkwood)一起合作,呈現了大型木材燃燒的立體聲錄音,我們使用了兩個接觸式麥克風,避開篝火粘在了木材的兩側。與捕捉空氣振動的傳統麥克風相比,接觸式麥克風呈現了聲音在物質中移動時的振動。就像醫生用聽診器聽心臟跳動一樣,深入研究物質和竊聽為聽者打開了物體的內部。對于協同運作的眼睛和耳朵的門戶來說 ,感知上的混淆也許很明顯,從背景中,其實是從光(看)和空氣(聽)中移除的聲音,會讓人聯想到不可思議的事物。我們被燃燒木材的聲音所喚起的、與之對立的聲音的深度和廣度所吸引、震撼,例如:舒緩的水的聲音;小瀑布撞擊巖石,音色變成了流動的溪流之聲;小雨敲打著鐵皮屋頂。在這里,離火如此之近來提取未曾聽過的猛烈吞噬木材的音景,這樣的潛在危險與平靜水聲的感官幻覺形成對比,造成概念上的不和諧。這種通過聲音和聲音中的顯著視覺元素的預期呈現的自動召喚,可能會強調一種基本性質,即我們一元化的感官感知、確定的我們共同生活或想象的現實的真實特質。這里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盲點——《水中火焰》表現了感知和現象的可變性。一陣隱秘的聲音正在發生蛻變。
在聲波流中,我們盲目地來到物質內部——由纖維素和木脂素制成的木材,它們已經老化、衰落,距離死亡只一步之遙,排空了最重要的元素——水。 現在,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森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遭遇嚴重的火災,并且,這種火災的破壞性和災難性越來越大。無論因為氣候變化而引發的野火,還是刀耕火種的農業實踐,原始森林被破壞的速度驚人,并且前所未有。因此,就像燃燒的木材一樣,目睹和想象下雨和水流的聆聽行為被木頭原子分裂和爆炸的聲響打斷,我們也許會認為我們的森林是維持降水循環、吸收二氧化碳,以及生成氧氣的關鍵,但是它也可能是一個正在燃燒的世界。
韓:此次展出的部分包括了邀請觀眾進行沉浸式體驗的裝置藝術,您會預設觀眾對作品做出的行為反應嗎?您怎樣看待作品與觀眾之間的關系?
蘇:從視覺轉向聽覺,《擊打》(2021)將新加坡泰勒版畫院的主畫廊轉變為觀眾的聲學游樂場,充滿了機遇的活力與隨機性。這里的視覺特權給觀眾的聲音表演/激活讓位,就像在這個空間中聆聽聲音的細微差別一樣。這件裝置呈現了一個舞臺,在那里,觀眾的表演是作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聲音和類似聲音的元素讓整件作品栩栩如生。“觀眾”這個詞的拉丁語詞根意思是“聆聽的行為”,但是,在這一情境中,同樣的觀眾和表演者參與反饋循環,產生聲音的表演者和聽眾都處于同一件作品中,作品是由250個玻璃容器組成的透明群島裝置,它們以廣闊、有機分布的方式在地上擴散開來。
在這里,僅僅觀看是不夠的。構成《擊打》的250個玻璃容器需要觀眾的參與和互動,這些線條挺直的容器數目繁多、形態各異,有的甚至高到及腰位置,有的還裝滿了水,以此來控制音調和音高,它們將觀眾包圍在其中,邀請觀眾與藝術家一起共同創作。作品中間的空間是一個空隙社區,這樣的間隔為新聲音的產生提供了空間,而這一空間剛好讓特制的亞克力“擊打者們”可以被快速拉拽和釋放,對未經編排的揮桿擊打玻璃產生拉力,釋放出一種類似加美蘭(以一種打擊樂器為主組成的樂隊表演形式,是印度尼西亞最富代表性的、廣泛流行于爪哇島和巴厘島的音樂)的雜音,在整個空間中產生共鳴。作品每一次被激活時都會引發獨特的聲學事件。這樣的過程不僅揭示了聲學現象的起源,它讓觀眾成為了能量轉移的發射器和接收器,同時也可以觀看運動過程中聲音的存在。
對我來說,《擊打》 同時也是用聲音繪制的線條、波浪和弧線的現場圖畫,是有關動力學的內容。作品被構建為在運動中被看到和聽到——擊打器引導觀眾的眼睛從一個點看向另一個點,從一陣聲音到另一陣聲音,從一個音符到另一個音符。當它們撞擊玻璃的時候會在空氣中產生聲波振動,因為可以同時釋放1組3件擊打器或10組30件擊打器,所以,有時產生孤立的音調,然后又聚集在一起,復雜又重疊。
韓:“畫廊——策展RHE”項目發起的初衷是在疫情期間,世界各地的畫廊能相互支持、共渡難關,在線上和線下策劃了21場展覽,激發各個畫廊之間的動態對話。作為項目的一部分,此次展覽是否對疫情進行了回應?
蘇:是的,此次展覽對我們與新冠疫情共處的非常時期進行了回應。 “只能用眼觸摸” 等同于藝術法令——“不要觸摸藝術品”,這是我們在參觀博物館和畫廊展覽時所遵守的規定,同時也反映了在疫情期間我們須保持1.5米強制社交距離的情形。《擊打》是一件需要觀眾參與來激活的聲音作品,它為公眾提供了一種緩解壓力的方式,邀請他們與美術館中的藝術品“玩耍”,這不僅讓我們自己(以及藝術創作的過程)不再沉迷于控制,而且致力于讓展覽從成為感官剝奪的方式中解脫出來。因此,與觀眾合作的風險雖然沒有中介物,但十分自由、開放,通過傳播,它激活了原本安靜而靜態的作品,然后將觀眾的手的力量轉化為聲樂“解構”——與建筑的墻壁、地板、天花板、柱子和周圍其他物體一起,像音場一樣產生回響。
韓:您的作品在世界各國著名美術館展出,活躍于各大雙年展、藝術節,在擁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和參展經歷之后,這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呢?
蘇:雖然我觀察并見識了各種各樣的人類行為,從保守主義到知性、藝術方面發人深省的行為,讓我深入了解了決策和領導力的危險和回報。然而,我一直以來都最看重幕后技術人員和助手們的工作,他們為實現和呈現藝術家的概念和愿景付出了巨大努力。我永遠都會尊重和贊賞他們的努力和付出。
韓:請談談您接下來的藝術活動和創作計劃。
蘇:對我來說,現在和未來的重要軌跡之一就是組織和保存檔案材料,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作品和研究,從而為我們地區的藝術史做出貢獻。 并且我相信,像中國這樣歷史文化豐富、古老而有趣的民族和文明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
韓:您是否還有更多分享的內容?
蘇:我想我已經分享了很多的作品和概念。非常感謝您提出的有趣問題,我很享受思考和回答這些問題。我希望大家在 2021年平安、健康,希望我們能更加珍惜彼此之間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