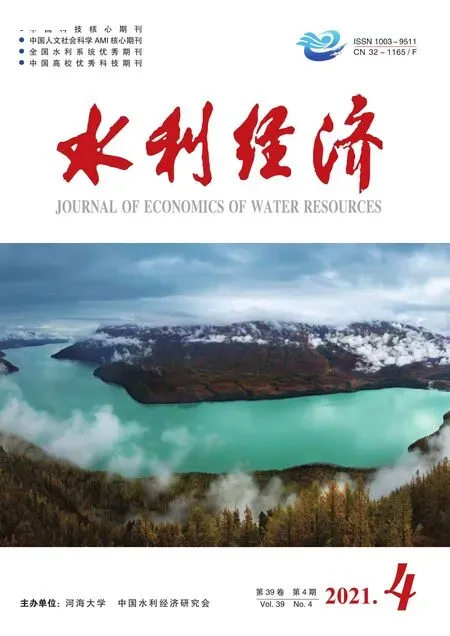長三角城市群環(huán)境規(guī)制與水資源利用效率
童紀(jì)新,趙崔妍
(河海大學(xué)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00)
水資源作為重要的自然資源和經(jīng)濟(jì)資源,不僅關(guān)乎日常生活,還關(guān)乎社會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綜合競爭力。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加快生態(tài)文明體制改革,建設(shè)美麗中國”,把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納入新時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把水利擺在九大基礎(chǔ)設(shè)施網(wǎng)絡(luò)建設(shè)之首,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優(yōu)化水資源配置,推進(jìn)綠色發(fā)展成為一項新的挑戰(zhàn)。長三角地區(qū)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平臺,該地區(qū)區(qū)位條件優(yōu)越,經(jīng)濟(jì)基礎(chǔ)雄厚,作為“一帶一路”與長江經(jīng)濟(jì)帶的交匯處,長三角城市群是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引擎,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增長和市場空間由南向北、由東向西拓展、協(xié)調(diào)區(qū)域發(fā)展方面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雖然長三角地區(qū)河網(wǎng)密布,但就人均水資源而言,依然十分緊缺,水環(huán)境承載力整體形勢嚴(yán)峻[1],合理配置水資源成為必然選擇[2]。長江經(jīng)濟(jì)帶作為中國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區(qū)域,而長三角城市群又是長江經(jīng)濟(jì)帶的龍頭,分析長三角城市群的水資源利用效率在當(dāng)下十分必要。加之,面對環(huán)境污染問題關(guān)注度的提高以及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需要,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強(qiáng)度和規(guī)模在大多數(shù)地區(qū)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擴(kuò)大。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wù)院印發(fā)的《長江三角洲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對長三角城市群的環(huán)境發(fā)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指出了要扎實推進(jìn)水污染防治、水生態(tài)修復(fù)、水資源保護(hù),促進(jìn)跨界水體水質(zhì)明顯改善,并提出生態(tài)環(huán)境質(zhì)量總體改善,跨界河流斷面水質(zhì)達(dá)標(biāo)率達(dá)到80%的發(fā)展目標(biāo)。在此背景下,環(huán)境規(guī)制對于水資源利用效率具有怎樣的影響,以及環(huán)境規(guī)制在不同強(qiáng)度下,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作用是否相同,也值得探究。
1 文獻(xiàn)綜述
1.1 水資源利用效率
水資源利用效率一直是學(xué)術(shù)界有關(guān)水資源管理的熱點研究問題,并且研究方法多樣。
在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法(DEA)[3]方面,吳瓊等[4]采用傳統(tǒng)B2C模型,基于2003—2015年全國31個省(區(qū)、市)數(shù)據(jù)分析水資源利用效率,并進(jìn)行Q型聚類將研究區(qū)域劃分為3種類型,具體闡述各地區(qū)用水效率差異的原因。江麗麗等[5]基于江蘇省2010—2017年生產(chǎn)用水?dāng)?shù)據(jù),采用三階段DEA法研究江蘇省生產(chǎn)用水效率。該方法在傳統(tǒng)DEA方法中加入了隨機(jī)前沿分析,剔除了影響因素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作用。傳統(tǒng)DEA模型只能計算出評價對象的相對有效性,無法評價已經(jīng)實現(xiàn)相對有效的評價對象的優(yōu)劣,而超效率DEA模型可以進(jìn)一步分析有效決策單元。基于此,任俊霖等[6]等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測度長江經(jīng)濟(jì)帶11個省會城市2011—2013年用水效率,并用Tobit模型檢驗其影響因素。Lombardi等[7]采用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通過對意大利自來水公司效率的計算來評估國家水行業(yè)系統(tǒng)的技術(shù)和環(huán)境效率。
在其他研究方法方面,陳思源等[8]采用隨機(jī)前沿生產(chǎn)函數(shù)法構(gòu)建農(nóng)業(yè)水資源利用效率理論模型,分析廣西農(nóng)業(yè)水資源利用效率的變動狀況以及耦合關(guān)系。管新建等[9]采用條件廣義方差極小法從指標(biāo)基本集中選取6個指標(biāo),并用熵權(quán)模型計算出綜合指數(shù),對黃河流域水資源利用效率進(jìn)行評估。鄧益斌等[10]運用泰爾指數(shù)分解法研究2004—2013年中國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區(qū)域差異,該方法在空間意義上將泰爾指數(shù)分解為組間差異和組內(nèi)差異,更易挖掘區(qū)域差異的內(nèi)在因素。Li等[11]提出AIC變量選擇法,考慮了投入產(chǎn)出間的所有變量組合,剔除了投入產(chǎn)出內(nèi)部信息冗余的變量,其結(jié)果具有穩(wěn)定性與有效性。郭利丹等[12]運用萬元GDP水生態(tài)足跡衡量出江蘇省水資源利用效率。
從研究區(qū)域來看:①研究省際和某一流域的用水效率的較多。武繼堯等[13]、鐘麗雯等[14]、張云寧[15]分別對遼寧省、廣西壯族自治區(qū)和江蘇省水資源利用效率進(jìn)行評價。鞏燦娟等[16]對黃河中下游沿線城市水資源利用效率進(jìn)行測算,并分析時空演變趨勢。Qi等[17]對長江經(jīng)濟(jì)帶水資源利用效率進(jìn)行評價并分析影響因素。②研究某一行業(yè)用水效率的也較多。孫付華等[18]基于DEA和Malmquist(全要素生產(chǎn)率)構(gòu)建農(nóng)業(yè)水資源利用效率評價模型,測算我國31個省(區(qū)、市)農(nóng)業(yè)用水效率并分析空間和時間異質(zhì)性。岳書敬等[19]運用投入產(chǎn)出法對長三角地區(qū)整體用水、三大產(chǎn)業(yè)用水和制造業(yè)二分位行業(yè)用水進(jìn)行差異分析。
關(guān)于長三角地區(qū)的研究,大多將長三角地區(qū)作為長江經(jīng)濟(jì)帶一部分研究,或?qū)⑺Y源利用作為生態(tài)評估的一部分來研究。張瑋等[20]通過建立EBM模型評價2006—2015年長江經(jīng)濟(jì)帶沿線省市綠色水資源利用效率。萬正芬等[21]通過DPSIR模型對長三角地區(qū)生態(tài)安全進(jìn)行評估,指出區(qū)域用水難以有效支撐產(chǎn)業(yè)發(fā)展和人口集聚帶來的水資源消耗,用水效率有待提高。朱智洺等[22]利用灰水足跡測度研究長三角地區(qū)水質(zhì)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長三角地區(qū)整體水質(zhì)上升,水資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1.2 環(huán)境規(guī)制與水資源利用效率
關(guān)于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效率的影響,現(xiàn)有文獻(xiàn)主要是從農(nóng)業(yè)用水效率、工業(yè)用水效率和水資源綜合利用效率3個層面進(jìn)行評價,此外,較多研究將環(huán)境規(guī)制納入眾多影響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因素中,僅分析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是正向還是負(fù)向影響。楊騫等[23]運用DEA和Bootstrap斷尾回歸模型實證檢驗,研究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規(guī)制可以顯著提升農(nóng)業(yè)水資源利用效率。汪克亮等[24]基于EBM-Tobit模型的兩階段分析,發(fā)現(xiàn)政府環(huán)境規(guī)制對長江經(jīng)濟(jì)帶工業(yè)綠色水資源效率沒有促進(jìn)作用,回歸系數(shù)為負(fù),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有較少研究表明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門檻效應(yīng),例如,徐承紅等[25]基于異質(zhì)性環(huán)境規(guī)制視角實證研究發(fā)現(xiàn)環(huán)境規(guī)制對綠色水資源效率存在門檻效應(yīng),并且不同類型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空間異質(zhì)性。
現(xiàn)有文獻(xiàn)雖然對于水資源利用效率的研究十分豐富,但仍存在一些拓展空間。一是,目前將長三角城市群作為獨立個體利用超效率SBM模型研究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文獻(xiàn)有待拓展,并且模型以及相關(guān)指標(biāo)選取的不同也會影響結(jié)論的差異。二是現(xiàn)有文獻(xiàn)大多局限于運用Tobit回歸模型研究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多種影響因素,僅大體研究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是正向還是負(fù)向影響,關(guān)于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門檻效應(yīng)的研究有待補(bǔ)充,環(huán)境規(guī)制達(dá)到何種力度才能有效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需要加以驗證。對于具有戰(zhàn)略地位的長三角地區(qū)來說,環(huán)境規(guī)制與水資源利用效率二者之間是否存在非線性關(guān)系、表現(xiàn)形式如何需要進(jìn)一步證實。因此,本文以長江經(jīng)濟(jì)帶的龍頭——長三角城市群為研究對象,利用超效率SBM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數(shù)分解法對各城市水資源利用效率及各項指數(shù)進(jìn)行分析,并運用面板門檻回歸模型探究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作用。該研究對長三角地區(qū)乃至長江經(jīng)濟(jì)帶的水資源管理具有一定的指導(dǎo)作用。
2 水資源利用現(xiàn)狀及研究方法
2.1 水資源利用現(xiàn)狀
2016年5月11日,國務(wù)院常務(wù)會議通過《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規(guī)劃中包含26個城市,長三角城市群以上海市為中心,輻射江蘇省9市:南京、無錫、常州、蘇州、南通、鹽城、揚州、鎮(zhèn)江、泰州;浙江省9市:杭州、寧波、溫州、嘉興、湖州、紹興、金華、舟山、臺州;安徽省8市:合肥、蕪湖、馬鞍山、銅陵、安慶、滁州、池州、宣城。2019年12月1日,《長江三角洲區(qū)域一體化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中新增浙江省溫州市。
圖1顯示: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農(nóng)業(yè)、工業(yè)和生活用水總量呈現(xiàn)波動下降的變化趨勢。2013年用水量出現(xiàn)高峰后陡然下降,原因是2013年國務(wù)院發(fā)布《實行最嚴(yán)格水資源管理制度考核辦法》,約束全國用水。2014—2016年緩慢上升,但總體上升幅度不大。隨后2016—2018年出現(xiàn)大幅度下降,原因是《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fā)展規(guī)劃2015—2030》和《“十三五”水資源消耗總量和強(qiáng)度雙控行動方案》的提出,以及習(xí)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了推動長江經(jīng)濟(jì)帶發(fā)展座談會,指出把修復(fù)長江生態(tài)環(huán)境擺在壓倒性位置,“共抓大保護(hù),不搞大開發(fā)”,對長三角的水資源利用以及生態(tài)保護(hù)提出了更高要求。

圖1 長三角城市群用水量變化
圖2與圖3顯示:農(nóng)業(yè)用水量長期占居用水量首位,基本處于45%左右,近7年呈現(xiàn)波動下降趨勢,但所占總用水量比重變化幅度不明顯,主要是因為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仍以農(nóng)業(yè)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農(nóng)業(yè)用水比重大。工業(yè)用水量呈波動下降趨勢,其所占總用水量比重近七年有所下降,但仍處于40%以上,主要是因為長三角地區(qū)雖然在節(jié)能減排技術(shù)的提高和環(huán)保措施的加強(qiáng)上有所進(jìn)步,但其作為長江經(jīng)濟(jì)帶的龍頭,工業(yè)發(fā)展具有一定的規(guī)模,所以工業(yè)用水比例無法做到較大幅度的下降。生活用水量所占比重逐年穩(wěn)定增加,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應(yīng)導(dǎo)致用水需求增加。

圖2 長三角城市群各項用水量變化

圖3 長三角城市群各項用水比重
2.2 研究方法
2.2.1超效率SBM模型
數(shù)據(jù)包絡(luò)分析(DEA)方法是一種評價決策單元投入產(chǎn)出效率的方法,由于不需要事先確定投入和產(chǎn)出之間的函數(shù)關(guān)系,避免主觀因素影響,被廣泛應(yīng)用于各領(lǐng)域的績效評價。
DEA的分析模型種類較多,為避免傳統(tǒng)DEA模型對于多個同時有效決策單元無法做出進(jìn)一步比較的缺陷和徑向、角度選擇帶來的偏差,筆者運用非角度、非徑向超效率SBM模型對長三角城市群的27個城市2012—2018年水資源利用效率進(jìn)行評價。該模型測出的效率值可以大于1,便于對DEA有效的城市進(jìn)行對比分析。
2.2.2Malmquist指數(shù)
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Malmquist)用來衡量生產(chǎn)效率的變化,Malmquist指數(shù)(M)可以拆分為技術(shù)進(jìn)步(CT)和技術(shù)效率(CE),而技術(shù)效率(CE)又可以拆分為純技術(shù)效率(CPE)和規(guī)模效率(CSE),即M=CTCPECSE。當(dāng)M>1時,表明生產(chǎn)率水平提高,反之即為降低;CT>1時,表示技術(shù)進(jìn)步;CE表示技術(shù)效率的變化程度,CE>1,表示技術(shù)效率提高;CPE>1,表示管理的改善使得效率得以改進(jìn);CSE>1,表示從長遠(yuǎn)來看,決策單元向最優(yōu)規(guī)模靠近。
2.2.3面板門檻回歸模型
現(xiàn)有文獻(xiàn)表明,環(huán)境規(guī)制可能對水資源利用效率存在門檻效應(yīng),為具體驗證這一關(guān)系,借鑒Hansen[26]的門檻回歸模型構(gòu)建以下模型:
Wi,t=β0+β1Ei,tI(qi,t≤ri)+
β2Ei,tI(qi,t≤ri)+βiCi,t+εi,t
(1)
式中:Wi,t為水資源利用效率;Ei,t為環(huán)境規(guī)制強(qiáng)度;q為門檻變量;ri為門檻值;I為示性函數(shù);C為影響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控制變量。當(dāng)滿足括號內(nèi)條件時取1,否則取0。當(dāng)變量系數(shù)β1與β2不相等時,則表示存在門檻。
3 變量選取和數(shù)據(jù)來源
3.1 超效率SBM模型的投入產(chǎn)出變量
筆者沒有籠統(tǒng)地選取供水總量作為投入指標(biāo),而是參照用水結(jié)構(gòu)劃分,選取農(nóng)業(yè)用水量、工業(yè)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作為水資源的投入指標(biāo),選取就業(yè)人口作為人力投入指標(biāo),全年固定資產(chǎn)總額作為資本投入指標(biāo),為全面評價水資源利用效率,采用反映經(jīng)濟(jì)綜合產(chǎn)出的GDP作為產(chǎn)出指標(biāo)。
全年固定資產(chǎn)投資總額用固定資產(chǎn)投資價格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歷年GDP用GDP平減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處理,已統(tǒng)一調(diào)整至以2006年為基準(zhǔn)的可比價格水平。
3.2 面板門檻模型的變量選擇
由于影響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因素較多,本文研究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門檻效應(yīng),選取環(huán)境規(guī)制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和門檻變量,水資源利用效率作為被解釋變量,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水資源稟賦、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人口密度和科技進(jìn)步作為控制變量。
3.2.1環(huán)境規(guī)制度量
學(xué)術(shù)界對于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度量方法較多,張翼等[27]將度量方式概括為3種,一是政府管理視角,二是成本視角,三是污染物密度視角。以往研究中有些采用單一變量指標(biāo)衡量環(huán)境規(guī)制,缺乏綜合考慮。本文研究水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考慮水環(huán)境規(guī)制的特殊性以及實證數(shù)據(jù)的可得性,選取廢水中化學(xué)需氧量排放總量、氨氮排放總量、工業(yè)廢水排放量和用水量作為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度量指標(biāo)。作為廢水中主要污染物,化學(xué)需氧量與氨氮排放總量能夠較好地衡量環(huán)境規(guī)制效果;工業(yè)廢水排放量與人口相關(guān)度較小[28],減少了人口因素的影響,也能較好衡量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下水環(huán)境規(guī)制的力度;此外,選取農(nóng)業(yè)、工業(yè)和生活用水量總量作為度量指標(biāo)之一,用水量越大,節(jié)水意識越不明顯,環(huán)境規(guī)制強(qiáng)度越弱。利用熵值法[29]對4個指標(biāo)進(jìn)行無量綱化處理和權(quán)重確定,最終確定一個綜合評價指標(biāo)。熵值法主要過程如下:
a.對數(shù)據(jù)進(jìn)行無量綱化處理:
(2)
b.確定第i年份第j項指標(biāo)的比重:
(3)
c.計算指標(biāo)熵值:
(4)
d.計算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
(5)
e.計算綜合指數(shù):
E=∑Xjθj(j=1,2,3,4)
(6)
最終,熵值法計算出的各項指標(biāo)權(quán)重如表1所示。

表1 2012—2018年環(huán)境規(guī)制指標(biāo)權(quán)重
3.2.2控制變量
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通常用人均GDP表示,有學(xué)者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的快速發(fā)展會加劇經(jīng)濟(jì)增長與水資源利用之間的矛盾,也有一些學(xué)者認(rèn)為發(fā)達(dá)地區(qū)對水資源利用更易產(chǎn)生規(guī)模效應(yīng)。控制變量中的人均GDP用GDP平減指數(shù)進(jìn)行平減處理,統(tǒng)一調(diào)整至以2006年為基準(zhǔn)的可比價格水平。
水資源稟賦用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來衡量,有學(xué)者認(rèn)為人均水資源擁有量高會降低水資源利用效率,即“資源詛咒”假說。也有一些學(xué)者證明水資源豐富地區(qū)能夠吸引投資與相關(guān)人才,從而減少資源支出。
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用第三產(chǎn)業(yè)增加值占GDP比重來表示,我國三大產(chǎn)業(yè)中第一產(chǎn)業(yè)耗水量最多,尤其是農(nóng)業(yè),加之農(nóng)業(yè)用水技術(shù)不夠先進(jìn),水資源浪費較嚴(yán)重,利用效率不高。而第三產(chǎn)業(yè)耗水較少,適當(dāng)增加第三產(chǎn)業(yè)比重會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
人口密度反映一個地區(qū)的緊湊程度,用各市歷年總?cè)丝跀?shù)與土地面積的比值來確定。人口密度高的城市更緊湊,資源分配更協(xié)調(diào),有利于降低資源消耗,增加利用效率。
科技支出以地方一般財政科技支出的數(shù)據(jù)表示,一般來說,科技支出金額越多,技術(shù)更加先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更高。
3.3 數(shù)據(jù)來源
投入產(chǎn)出項中各用水量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各市水資源公報,其余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各市統(tǒng)計年鑒、國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發(fā)展統(tǒng)計公報。化學(xué)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工業(yè)廢水排放量以及用水量數(shù)據(jù)來源于各市環(huán)境狀況公報。數(shù)據(jù)縱向覆蓋7年(2012—2018年),橫向覆蓋長三角城市群27個城市,共計189個決策單元。
4 超效率SBM和Malmquist指數(shù)評價結(jié)果
4.1 超效率SBM評價結(jié)果
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長三角城市群27個城市2012—2018年水資源利用效率,所用軟件為MaxDEA pro,計算結(jié)果見表2。

表2 2012—2018年長三角城市群各市水資源利用效率
從整體水資源利用水平來看,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水資源利用效率均值為0.766,水資源利用率良好,但仍有較大提升空間。7年間總體水資源利用效率呈波動上升狀態(tài),2018年總體水資源利用效率最高,達(dá)到0.798,整體態(tài)勢偏好。
從各市歷年水資源利用效率來看,始終保持在較前沿面的有無錫市、寧波市、金華市、舟山市、池州市和上海市,這幾個城市在2012—2018年間每年始終保持DEA有效。無錫市7年間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平均只有484 m3,上海市7年間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在長三角城市群里一直處于末位,如2018年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有159.67 m3,無錫和上海水資源利用率較高的原因是區(qū)位優(yōu)越,技術(shù)水平較高。池州市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始終處于長三角城市群中領(lǐng)先地位,2016年人均水資源擁有量達(dá)8 638.6 m3,是同年上海的34倍,但開發(fā)利用程度低,資本與勞動力配置較好,所以水資源利用率較高。寧波市、金華市和舟山市的歷年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在長三角城市群中處于中上水平,加之依靠嚴(yán)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實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資源節(jié)約同步提升。
蕪湖市、馬鞍山市、安慶市、滁州市和宣城市水資源利用效率一直處于較低水平,2012—2018年間水資源利用效率均在0.5以下,這些城市集中在安徽省,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以農(nóng)業(yè)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并且目前農(nóng)業(yè)用水技術(shù)較為落后,粗放式的農(nóng)業(yè)用水方式導(dǎo)致用水效率較低。
4.2 Malmquist指數(shù)評價結(jié)果
4.2.1分年份的Malmquist指數(shù)
由Malmquist指數(shù)模型及MaxDEA pro軟件,計算出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各市的水資源利用Malmquist指數(shù)及各項指數(shù)分解值(表3)。
表3顯示:從時間序列來看,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Malmquist指數(shù)均值(1.100)大于1,總體全要素生產(chǎn)率實現(xiàn)增長,只有2017年M<1,但并不影響整體提升的趨勢。此外,2012—2018年CE均值(1.019)、CT均值(1.079)和CPE均值(1.025)均大于1,而CSE均值(0.998)小于1,說明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期間,水資源利用的技術(shù)方面的改善起積極作用,而規(guī)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長三角城市群水資源效率的提高。

表3 不同年份Malmquist指數(shù)
從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來看,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間平均CT為1.079,并且各年CT均大于1,表明長三角地區(qū)技術(shù)進(jìn)步優(yōu)越,應(yīng)繼續(xù)保持對技術(shù)的重視,發(fā)揮節(jié)水技術(shù)的優(yōu)勢,引進(jìn)節(jié)水技術(shù)人才。
從技術(shù)效率指數(shù)來看,2012—2018年的CE均值為1.019,說明整體上管理水平有所提升,從技術(shù)效率指數(shù)的分解來看,純技術(shù)效率均值為1.025,但7年間呈現(xiàn)波動狀態(tài),應(yīng)警惕出現(xiàn)下降趨勢;規(guī)模效率均值為0.998,并且也呈現(xiàn)波動狀態(tài),規(guī)模效率有待重視和改善,應(yīng)合理配置資源,調(diào)整水資源投入規(guī)模,健全水資源管理制度。
4.2.2分地區(qū)的Malmquist指數(shù)
表4顯示:從全要素生產(chǎn)率來看,2012年以來,長三角城市群中,只有銅陵市的M<1,呈負(fù)增長,增長率達(dá)-3.8%。其他城市M均大于1,均呈正向增長。其中,南通市(1.205)和鎮(zhèn)江市(1.280)的M最高,全要素生產(chǎn)率增長最快,分別達(dá)20.5%和28%。南京、無錫、蘇州、鹽城、揚州、泰州、杭州、溫州、湖州、紹興、臺州、合肥和安慶的M也較高,均在1.1以上,增長率都在10%以上。長三角城市群絕大部分城市的全要素生產(chǎn)率都在提高。

表4 不同地區(qū)Malmquist指數(shù)
從技術(shù)效率指數(shù)來看,寧波、嘉興、金華、舟山、銅陵、滁州、池州和上海的CE<1,表明技術(shù)效率下降。寧波、嘉興、金華和銅陵是由于純技術(shù)效率出現(xiàn)負(fù)增長,這些城市應(yīng)加大“軟”技術(shù)方面的投入與改進(jìn)。舟山、滁州、池州和上海是由于規(guī)模效率呈現(xiàn)負(fù)增長,應(yīng)當(dāng)提高水資源與其他要素的匹配程度。此外,長三角城市群中只有不足40%的城市達(dá)到規(guī)模效率有效,說明并未實現(xiàn)規(guī)模效應(yīng),長三角城市群應(yīng)當(dāng)進(jìn)一步合理規(guī)劃各要素投入。
從技術(shù)進(jìn)步指數(shù)來看,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平均增長7.9%,說明技術(shù)引進(jìn)、產(chǎn)品研發(fā)這類“硬”技術(shù)發(fā)揮重要作用,這與長三角地區(qū)資源優(yōu)勢相關(guān),長三角地區(qū)匯集眾多科研院校,人才儲備豐富,并且對人才吸引力大。
5 面板門檻回歸分析
運用stata15.0對面板門檻模型進(jìn)行檢驗,先后確定門檻效應(yīng)是否存在以及門檻數(shù)量。并依次估算單門檻,雙門檻和三門檻模型,所測出的F值和P值如表5所示。
根據(jù)表5結(jié)果可知,單一門檻值為0.494,P值為0.007,在1%水平上顯著。而雙重門檻P值和三重門檻P值均不顯著。這說明以環(huán)境規(guī)制為核心變量和門檻變量時,門檻效應(yīng)存在,且表現(xiàn)為單門檻效應(yīng)。環(huán)境規(guī)制與水資源利用效率之間呈現(xiàn)非線性關(guān)系。

表5 門檻效應(yīng)檢驗
表6的結(jié)果顯示,當(dāng)門檻值小于或等于0.494時,環(huán)境規(guī)制系數(shù)為0.607 4,P值大于0.1,不顯著。當(dāng)門檻值大于0.494時,環(huán)境規(guī)制系數(shù)為1.983 4,P值小于0.1,并通過顯著性檢驗。即表明,當(dāng)長三角城市群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小于或等于0.494時,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有正向作用,但作用不顯著;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大于0.494時,環(huán)境規(guī)制可以顯著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每增加1%的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水資源利用效率增加1.983 4%。回歸結(jié)果表明,在長三角城市群中,只有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達(dá)到門檻值時,環(huán)境規(guī)制才能顯著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表6 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回歸結(jié)果
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的系數(shù)為0.733 7,并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可以顯著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系數(shù)為0.986 2,并且通過顯著性檢驗,表明第三產(chǎn)業(yè)所占比重越大,水資源利用效率越高;水資源稟賦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有顯著正向作用,這與“資源詛咒”假說相悖,表明水資源豐富的地區(qū),浪費和不合理利用水資源的現(xiàn)象得到了一定控制;人口密度和科技支出對水資源利用效均呈現(xiàn)正向作用,但影響作用不明顯。
6 結(jié)論與建議
6.1 結(jié)論
本文基于長三角城市群2012—2018年面板數(shù)據(jù),運用超效率SBM模型測算長三角城市群水資源利用效率,并分析全要素生產(chǎn)率指數(shù)變動情況,最后構(gòu)建以環(huán)境規(guī)制為門檻變量的面板門檻模型,實證檢驗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作用,主要研究結(jié)論如下:①長三角城市群水資源利用效率良好,有較大提升空間,全要素生產(chǎn)率整體呈波動上升趨勢;②長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間水資源利用效率有顯著差異;③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影響存在單一門檻效應(yīng),不存在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效應(yīng)。當(dāng)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低于門檻值0.494時,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有促進(jìn)作用,但不顯著,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高于門檻值0.494時,才能顯著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
6.2 建議
為了推進(jìn)長三角城市群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并更好地發(fā)揮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促進(jìn)作用,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a.長三角城市群整體水資源利用效率良好,但各市水資源利用現(xiàn)狀不同,成因也各異。各市應(yīng)當(dāng)結(jié)合水資源利用水平和全要素生產(chǎn)率各項指數(shù)情況,著眼成因,針對性地調(diào)整,做到有的放矢,從不同著力點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
b.長三角城市群應(yīng)當(dāng)繼續(xù)保持技術(shù)進(jìn)步的優(yōu)勢,推進(jìn)技術(shù)創(chuàng)新,提升技術(shù)手段,發(fā)揮技術(shù)進(jìn)步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積極調(diào)整規(guī)模效率,合理規(guī)劃各要素,改善水資源投入的結(jié)構(gòu)與規(guī)模水平。
c.重視環(huán)境規(guī)制對水資源利用效率的促進(jìn)作用,繼續(xù)加強(qiáng)各城市對水環(huán)境問題的重視,把握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完善環(huán)境規(guī)制政策,貫穿綠色發(fā)展理念。長三角各市政府要加以引導(dǎo),具體評估各地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對于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不足的城市,要合理加大環(huán)境政策實施力度,提升環(huán)境規(guī)制的效果,確保環(huán)境規(guī)制能夠有效顯著促進(jìn)水資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對于環(huán)境規(guī)制力度過大的城市,應(yīng)合理調(diào)配相關(guān)人力、物力資源,不應(yīng)造成相關(guān)資源浪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