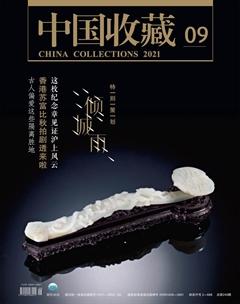珍貴信札喚醒一場重要展覽
王羊羽
在今年杭州的藝術品春拍上,筆者得見翁萬戈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往來書信20多通。其中,19通是翁萬戈致王世襄書信,另外5通王世襄致翁萬戈書信大多是寄信者自留底稿。這批書信資料寫于1982年至1998年間,長達16年之久,且內容豐富,大多是探討中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涉獵較廣。

一拍即合辦展覽
眾所周知,文博大家王世襄先生出身名門望族。除了收藏和研究明式家具,他涉獵很廣,包括音樂、漆器、書畫、烹飪、竹刻等方面都著述頗豐。翁萬戈先生是翁同龢的五世孫,畢生守護翁氏家族六代收藏的古書畫和宋元以來的珍稀古籍善本。按翁先生自己的話說:“自幼入私塾,長游海外,賴先人余蔭得機出而賞觀名跡,歸而鉆研群書,如此環境,豈能浪費流華,不做菲薄貢獻?以是盡心力而為之。”(見1998年7月6日翁萬戈致王世襄信。)
實際上,除了美籍華人大收藏家的身份,翁萬戈先生還是著名學者、導演和社會活動家,其拍攝的《中國佛教》紀錄片曾獲1973年亞特蘭大國際電影節金獎。上世紀40年代開始,他就致力于在美國推廣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82年初,他出任華美協進社美術委員會主席,同年8月就職華美協進社社長。華美協進社坐落在美國紐約曼哈頓,1926年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著名教育學家約翰·杜威、孟祿與中國著名學者胡適、郭秉文等共同創建,旨在介紹中國的文化與文明。

1998年7月6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當中提到自己“豈能浪費流華,不做菲薄貢獻?”。
筆者此次看到的這批書信中,1982年年初至1983年,兩人書信往來里有一件事貫穿其中,那就是由翁萬戈提議,兩人一拍即合,決定協力在華美協進社的平臺上舉辦首個中國竹刻展覽。王世襄先生的二舅金東溪和四舅金西厓是民國時期的竹刻大家,尤其金西厓被公認為近代刻竹第一家,著有《刻竹小言》,后由王世襄整理編校出版。因此舉辦竹刻展,翁先生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王世襄先生。這是首次在海外舉行的宣傳中國獨特傳統竹刻藝術的展覽,意義可謂十分重大。
籌備過程“臺前臺后”
關于這批書信中提及的展覽前后一些細節過程,筆者進行了整理節錄并釋文,在此按照信函的時間順序分享給諸位,這也正是書信文獻價值的重要體現。
1982年1月27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今秋華美協進社,由弟提議舉行竹刻展覽,其中將精選此間中國竹刻五十件,附以明清畫竹六七幅,想可以成為歐美歷年來初次竹刻展!弟又提議請我兄寫一序文,約合一萬字左右,以冠目錄之首。文以中文即可,弟毛遂自薦,代為半翻半編,不知兄意如何?……文中如談及技術方面,最好請附工作照片,黑白清楚即可,如留青,如深淺刻等,皆須有圖表示……關于攝影費用請示知,自當奉還。”
1982年2月24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徐秉方先生合作極佳!示范最好用畫,不用書法,因為洋人不能全部欣賞書法也。拍照費用如100不足,弟可酌加,請勿因此而減少應有的各種角度,報酬之事可面談……總之此展覽可以為此間開目,希望可為我國竹刻藝術在海外宣揚!”
1982年3月12日,王世襄回信翁萬戈:“文物局在承德舉辦讀書班,調全國博物館工作者分批參加,四月下旬要我去講課,因此考慮到序文一拖便可能交不了卷,可以現在已經動手寫了約四分之一了。如無其他感擾,月底當可寄奉。覺得目前的想法(即大綱)有必要告訴你一下,包括選圖,此外還想告訴你一些參考書。當然兄或早已知道,但饒舌似亦無妨。萬一你那里沒有,還可復制寄上。下分條陳述:
序文想分以下幾段(當然可能會有變動):1、歷史。簡述明以前,下分明、清前、清后、近現代,論四百年的消長;2、技法(徐刻入此);3、如何欣賞及保存竹刻。大約一萬字;3、當然是為外國人寫的,兄可據拙稿再發揮。
為兄計,應準備以下各書:有的可參考,有的從中翻印照片。1、金元鈺《竹人錄》。2、褚德彝《竹人續錄》。3、《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74年文物出版社圖版86竹雕勺。4、《中國竹刻藝術》香港葉義醫生編著chinese banboo carving。襄擬用其中兩件NO2.朱小松蟾蜍,NO99.潘西鳳壽星臂擱。當寫信請葉把照片逕寄我兄,估計他會同意,只怕他離港出游。還有該書彩色22鄧渭白菜筆筒,葉玉虎舊藏,現在甘城,可從甘城索到,此次應入展。它可作為陷地深刻的例子……

得知翁萬戈先生想在海外舉辦首個中國竹刻展覽,王世襄先生大力支持,前后細節兩人一直在用書信往來溝通。

1982年3月12日王世襄致信翁萬戈,建議并列出了為展覽所需準備的書籍資料。
徐秉方有信來,他特意去上海請唐云、喬木兩畫師畫了兩塊臂擱,即動手刻,并分過程拍照,弟建議他五月底以前將照片寄來。現再寄信聯系,看能否提前一些更好。或請他由常州逕寄,以免郵程耽擱……弟意唐云畫不適合竹刻,不如用喬木的一件,還有與其刻兩件太促迫,不如集中力量刻一件,此意已寫信告徐。至于原刻件只有請他五月間寄京,由兄自己帶回參加展覽,否則郵寄甚費事也。現在擔心的是常州拍照條件差,效果不一定好。”
1982年3月25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葉恭綽老先生之女julia cheng今春回國,弟已作介紹信,愿與我兄一聚。她的竹刻收藏現在nelson galley寄存,即葉老先生之遺物。我們打算用個十來件,聽說甚精,惜樣式太少了(葉醫生亦如是說)……當今此展為我國特殊藝術作西方的初次介紹,我兄貢獻占領導地位,能附驥尾,幸甚幸甚。”
1982年5月9日,王世襄致信翁萬戈:“徐秉方先生最近刻成的臂擱三方,煩費慰梅夫人帶致,使首次在美舉辦之竹刻展覽,亦有當代人作品,對這一在國外少有人知,國內又日見衰落的傳統藝術,或能起振興宣揚作用。兄既大力創辦,襄敢不大力贊助。因時間迫促,徐先生表示刻得并不滿意,請鑒原。刻潤已由襄承擔,祈勿念。三件均為非賣品,下次歸國乞帶回為感。國外如有購者,可逕與江蘇武進縣工藝美術公司聯系。該公司如接到國外定件,對徐先生當刮目相待。藝人清苦,倘因此對徐先生有所重視,亦弟之愿也。”

1982年5月9日王世襄致信翁萬戈,提到徐秉方已為展覽刻成三方臂擱。
1982年8月28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關于竹刻展覽,已決定于1983年三月中開始,展期至五月底為止,然后七月初至kansas city之nelson Gallery約至九月中,然后去舊金山之亞洲美術館,自九月底或十月初至年底。如此中國竹刻可以在美國全國(東岸、中部及西岸)三大主要地點向大眾介紹矣!”
1983年3月25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1月28日大札亦早奉悉,知范堯卿之為農民,可喜可奇,徐秉方、劉萬琪兩位作品極得收藏家之注意……展覽會場開幕前,忙得四腳朝天(如滾馬圖一般),以是遲覆,現在3/16預展,3/17社中會員開幕展,3/18對公眾開幕展之后,又有葉義講演,一切成功,博得好評,為我國竹刻在海外宣揚,可以告慰……”
為傳承不遺余力
在籌備展覽的通信中,兩位先生交流的內容還涉及到對當代竹刻創作的助力。
1983年4月24日,王世襄致信翁萬戈:“范堯卿已通信多次……他能精制鳥籠及竹編等,實在是一位巧手。我建議他用一個較雅的號‘遙青,兄看如何?韓愈詩:‘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我認為他是一介草民,一位普通農民,但能刻竹。常州本地無人知道,并不出名,但北京、香港、紐約卻有人重視。所謂‘草色遙看近卻無也。他欣然愿用此號,并對弟有知己之感。我們實素昧平生也。”
1983年7月9日,翁萬戈致信王世襄,對介紹刻竹家徐秉方與劉萬琪的作品并積極幫助代售提議:“1、華美協進社出面代理,保證美術家與收藏家雙方愉快的來往,華美當與美術家的單位或美術家直接連系,負責通信付款等事;2、潤例目前為每件三百至五百元,以作品的質量為定(美術家本人可以在此范圍內指定,華美當然尊重其意見);3、為避免收藏家的誤會,作品在未寄來之前,先寄照片,得收藏家首肯后,即匯款與正式定單,由國內寄至華美。”
可見,翁萬戈先生借助華美協進社的平臺,不僅極力宣傳推廣中國竹刻藝術,還積極聯系海外藏家購買中國竹刻家作品。
屈指一算,這個展覽已經過去了30余年。其實當時國內的竹刻藝術并不受重視,更談不上市場;當時優秀的竹刻藝人很少,且生活清貧。通過這批往來書信我們可知,兩位先生在這一重要的竹刻展上花費了大量心血,展品的來源除了美國的博物館館藏外,還有重要私人藏家,如葉恭綽舊藏、香港葉義醫生藏品,以及王世襄先生力薦的當代竹刻家徐秉方、劉萬琪、范堯卿的作品。
這也不難看出,對于竹刻這個當時比較冷門的藝術門類,王世襄先生看得很遠,他認為只有做好傳承,才有未來。信中提到的徐秉方是名門之后、刻竹名家徐素白之子,特別擅長“留青”技法,系當代竹刻大家;劉萬琪畢業于四川美院,當時在貴州群眾藝術館工作,后任貴州大學藝術學院教授,是學院派竹刻藝術的代表人物;而范堯卿在當時寂寂無名,王世襄先生將他從民間發掘出來,為他取雅號,還收為弟子,親自指導,如今也成為了常州留青竹刻傳承人。
從信札中我們還可以了解到,兩位先生不遺余力宣傳竹刻藝術,王世襄先生撰寫序文、準備相關學術資料及圖片,找竹刻家為展覽專門進行創作并配上雕刻流程系列照片;翁萬戈先生代表的華美協進社提供資金贊助,出版相關英文圖冊,在美國多地巡展,并無私地幫助竹刻家在海外做市場推廣。今天,藝術家的創作條件、生活水平和藝術市場與當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筆者認為,行業的發展離不開前輩余蔭,他們為文化傳承所做的重要貢獻與執著精神不能忘記。

1983年4月24日王世襄致信翁萬戈,說到自己為范遙卿取雅號“遙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