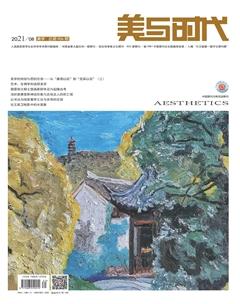以書法為線索看李之儀與米芾的交游
龐迪



摘要:李之儀與米芾同為北宋著名文人,且都對書法有所偏好。考察吳芾《姑溪居士全集·序》和周紫芝《太倉米集》,筆者發現,所謂《姑溪居士全集》的體量只是李之儀詩詞、文章、題記屢遭戰火,焚毀散佚后碩果僅存的冰山一角。透過這些僅有的記載可以發現,李之儀與米芾在各自所生活的年代有所交際,而這在相關研究中幾無涉及。本文試圖通過考察二人的交往軌跡,還原李米之間友誼的橋梁。
關鍵詞:書法;李之儀;米芾;交游
李之儀(1048-1128),字端叔,號姑溪居士,祖籍滄州無棣(今屬山東),居楚州山陽(今江蘇淮安)。其父李頎,嘗任太常博士;母親田氏,沈括曾為其作墓志銘。李之儀少年得志,為治平四年(1068)進士,后因與蘇軾、折可適交往,仕途蹭蹬。至徽宗朝又為范純仁做遺表,忤蔡京,坐元祐黨籍,進而被除名編管當涂。后遇赦復官,再因楊姝事勒停,后再次遇赦,領成都玉局觀。于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去世。
吳芾在《姑溪居士前集序》中說道:“昔二蘇于文章少許可,尤稱重端叔,殆與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秦少游輩頡頏于時,今觀其文,信可知已。”[1]1蘇軾在《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詩百余首讀至夜半書其后》中把李之儀與孟浩然相較,并有“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轍參禪”[1]83的贊揚;《宋史》也有“之儀能為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2]之語;王明清《揮塵錄》亦記載:“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才學聞于世。……端叔于尺牘尤工,東坡先生稱之,以為得發遣三昧。……值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之余,稱賞不已,欲召用之。”[3]從諸如此類的記載可知,李之儀擅文之譽實至名歸,而關于李之儀能書之事卻鮮有人知。
李氏主要生活在北宋后期,一生經歷七朝,一方面,李之儀與蘇軾、黃庭堅、米芾交往密切,相互酬答,而且留下許多有關書法的記載論述;另一方面,從北宋書法遺存的橫向比較結果來看,既有作品傳世,又有書論遺存的書家,除了蘇軾、黃庭堅、米芾,當首推李之儀。也正因為李之儀好溺書法,故而能與米芾志趣相投、時有交際,也才能為后人留下數量可觀的書論,為我們具體了解北宋的書法生態多有助益。
一、李之儀與米芾的交際考略
米芾(1051-1107),字元章,號海岳外史,祖籍太原,后遷襄陽,長居丹徒(今屬江蘇鎮江),著有《寶晉英光集》等。米氏最善書法,用筆爽利,筆勢奇絕,蘇軾評之為“風檣陣馬,沉著痛快”,李之儀也評價道:“元章行筆為一時之冠,推而上之,柳誠懸、徐繼海俱在下風。”[1]327有關李米二人的交游僅見于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西園雅集除外),米芾《寶晉英光集》竟無記錄二人交往的只言片語,實在可惜,故尤顯李之儀遺存資料之珍貴。
從留存資料來看,李米二人的第一次見面當在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二人一同出席了駙馬王詵舉行的西園雅集。米芾在《西園雅集圖記》中自述:“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4]
二人第二次會面當在宋哲宗紹圣五年(1094)。據魏平柱《米芾年譜簡編》考證,米芾出任漣水(今江蘇淮安漣水縣)是在紹圣四年(1097)和紹圣五年(1098)[5]。在此期間李之儀給米芾寫了四通手簡,在《姑溪居士全集》中皆命名為《與米元章》。第一封手簡言:
八月八日,某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游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間,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1]163
李之儀在信中對米芾陳述久違之意,并對米芾的政績予以肯定。由文中“到京交游尚未遍”可知李之儀曾與米芾相遇并游于京師開封。再由“伏自拜違,行四年矣”的記載,并結合宋代的磨勘制度,考察二人行跡:哲宗元祐九年(1094),李之儀從蘇軾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幕府回京,米芾于此年在雍丘縣(今河南杞縣)任滿三年回京述職,兩人回京時間正好相符。于是可以斷定二人的第二次有記載的會面當在元祐九年(1094),而該通手簡當寫于米芾任漣水軍使任上的第二年,即宋哲宗紹圣五年(1098)。
二、李之儀與米芾的通信考察
李米二人的交游除有行跡可考外,李之儀的四封手簡,也可為二人的過往提供線索。正如曾棗莊在《宋文通論》中言:“李之儀以書簡、題跋聞名,其簡札的突出特點,是信筆隨意,而又行文曲折,婉轉多姿。”[6]在四通手簡中,李之儀時而攀親念舊,時而索書聚餐,若非關系緊密,斷不能如此。《與米元章》后三通手簡有言:
某上啟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遽,當已塵浼,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1]163
某啟,末路間關,獨得于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于我而然也?近見子魯曾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挽之不斷,企仰何及。漣漪古郡,距我松楸才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輩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1]163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降問,兼辱元暉下顧,敦敘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晚集,敬當只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次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1]164
李之儀在前兩封手簡中除了寒暄,還大力贊揚米芾政績可觀,而對米芾渴望回京述職的心情,則以“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進行安慰。在第三封手簡中,李之儀先是以“末路間關,獨得于公為多”說明在窮頓困苦時米芾給予自己了很多安慰;話鋒一轉,以“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于我而然也”,表達自己對米芾書信不繼的不滿;進而情緒再次轉換,借曾子魯之口贊揚米芾政事可觀;最后說米芾上任之地,與自己祖上的長眠之所毗鄰,風俗浸漬,移風易俗,自己也成為米芾管轄的子民了,并因未能攜父老親自到米芾“麾下”拜訪而耿耿于懷。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李之儀的幽默風趣,更見二人關系不一般。
第四封手簡則主要講述米芾索書一事:先前向米芾索字成功后,李之儀到米芾處拿取,不想之后“變本加厲”地“輒欲更求十數幅字”,且自帶書紙,若不合用,則請米芾“先告示及,當攜往也”。如此生活化的場景,足見米芾書名顯于一時,更反映出李之儀對米芾書法的激賞。
三、李之儀對米芾的其他關照
李之儀被貶潁昌(今河南許昌),曾作《與成德余》手簡十封,第八封有言:“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1]210從其中“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可以看出李之儀對米芾書法的尊崇,與上文第四封信件的主旨相呼應。對于此信寫作的具體時間,筆者也做了一番考證,在《與成德余》的第九封手簡中李之儀曾有“貶所褊陋,略無與意等者”[1]210之語,考查李之儀一生三次仕途失意,只有元符二年(1099)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貶官。是年,李之儀本應“監內府香藥庫”,卻因“之儀既為奸臣心腹之黨”而“令有司放罷”[7]。其余兩次均為較為嚴重的編管和除名,故所居之地不能稱為“貶所”,由此可知此事只能發生在貶謫后的元符三年(1100)。
崇寧五年(1106),李之儀曾作《跋米元章與術人劉思道帖》,此后李之儀又有三首詩以示懷念。其中《次韻圣源無求兼懷元章》有“門限踏穿行復爾,靈丹救活信能奇”[1]47之語,透露出李之儀對智永和鐘繇書事的關注,更間接贊揚了米芾的書藝高妙。其中第二首《次韻子椿同關圣源、吳思道贈董無求,有懷米元章》曰:“海岳仙人不我期,碧云幽恨獨心知。坐間優孟已難別,筆下羊欣更出奇。自是人才空立異,當知臣叔本非癡。重輕到了存公議,揮扇何勞強執葵?”[1]46詩中李之儀以優孟穿著孫叔敖的衣服向楚懷王進諫為比喻,說明米芾喜穿唐裝,行為乖僻;而在書法上李之儀認為米芾比“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中羊欣的書法更為奇妙。第三首《次韻米元章》曰:“蹭蹬生涯可否間,強扶衰緒欲觀瀾。篷生雖托麻方直,器就寧嗟木是蟠。晚寄鄉閭端有謂,時容雞黍其論歡。連城未薦誰非璞,莫與堅珉一眼看。”[1]48詩中李之儀將米芾比喻為是璞玉,勸米芾不要自暴自棄,從詩中亦可看出二人時常宴飲,惺惺相惜。
此外,李之儀對米芾書法的題跋有《跋米元章書儲子椿墨梅詩》《跋米元章所收荊公書》《跋元章書》和《跋黃米書》,四則題跋均載于《姑溪居士全集》卷三十九,足見李之儀對米芾書法之關切。
四、結語
通過考察二人的交際、通信及李之儀對米芾的其他關照,可以看出二人常有噓寒問暖、風趣玩笑之舉——或過問政事,或納紙求書,或應邀聚餐,足見二人關系之親密。但進一步考察,筆者發現二人的交往有幾個特點:一、二人的交游是以書法為主線連接起來的,且李之儀對米芾的書法表現出激賞和崇拜的態度;二、從遺存的資料來看,李之儀與米芾的交游多是單向的,二人交游僅見于吳芾所編《姑溪居士全集》,米芾《寶晉英光集》幾乎不曾提及;三、李之儀對米芾的慰藉多是開導和勸勉式的。李之儀較米芾大9歲,但二人登上仕途大概在同一時期,在李之儀僅有的四封手簡中,就有三封言及米芾政績可觀,交口贊譽,此舉或能給米芾失落的心緒帶去些許安慰。
參考文獻:
[1]李之儀.姑溪居士全集[C]//王云五.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2]脫脫,等.宋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5:10941.
[3]王明清.揮塵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700.
[4]米芾.寶晉英光集·補遺[M].北京:中華書局,1985:76.
[5]魏平柱.米芾年譜簡編[J].襄樊學院學報,2004(1):85-96.
[6]曾棗莊.宋文通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825.
[7]曾棗莊,舒大剛.北宋文學家年譜[M].臺灣:文津出版社,1999:362-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