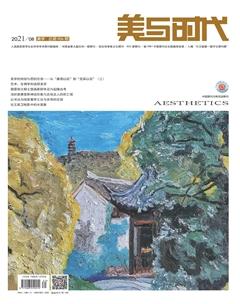論老舍《文博士》中的諷刺藝術
郭朝文
摘要:在小說《文博士》中,老舍繼承了魯迅的諷刺基調,并延續諷刺中含帶幽默的一貫筆法,淋漓刻畫了文博士此類留洋派知識分子的丑惡嘴臉,深刻批判了濟南上流社會成員“錢本位官本位”的腐朽思想。小說巧妙設置了唐振華和楊家六小姐、文博士與唐先生兩組對比,在深刻的對比中達成諷刺效果,表達了老舍的善惡價值評判。敘事上,隱含作者的態度與敘述者相對立,使敘述者及他所敘述的對象都成為隱含作者所要諷刺的對象,敘述者“文博士”既是諷刺的主體,又是諷刺的對象,構建出文本諷刺的巨大張力。
關鍵詞:老舍;文博士;諷刺藝術
《文博士》最初題名為《選名》,1936年以連載的形式發表在雜志《論語》第98期到第115期上(第110期、113期除外),但僅連載至十六期,嚴格意義上來說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小說主要講述一位留美博士文志強回國謀事,四處奔波又四處碰壁,并怪罪于“不知好歹”的中國社會認不清他的博士價值,因而選擇投奔有錢有勢靠給青年學生提供便利來進一步穩固壯大自身勢力的焦委員,又經由同樣卑瑣勢力的唐先生,成功攀附上了富商楊家,討得楊家六姑娘麗琳歡心,實現了自己的“事業”。小說成功塑造了文博士這樣一位不學無術、精于鉆營、滿腦財權的留學生形象,同時抨擊了上世紀30年代濟南文政界的種種亂象,并以戲謔嘲諷的筆鋒鞭撻了那些蠅營狗茍、腐朽卑劣的文痞政客。
一、幽默諷刺
一般來說,作者按照自身對善與惡道德判斷的思考,以及對當前現實生活中的腐朽與丑惡所持的敵對態度,訴諸文學便形成了諷刺。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一大批愛國作家自覺用文學承擔起啟發民智的重任,辛辣的諷刺文學成為了他們手中的利刃,一切腐朽落后的東西都成為應當被否定棄除的糟粕,那些世俗丑陋的社會現象和世態人情成為他們無情批判和抨擊的對象。作為中國現代諷刺小說的代表作家之一,老舍繼承了魯迅的諷刺基調,并且在批判諷刺中引入了幽默的態度和效果,不僅沒有走向油滑或是無意義的插科打諢,反而在褒貶是非、夸張嘲謔中深刻地剖析了社會弊病。
《文博士》中的文博士是一個不學無術、精于權術又十分有野心的留美博士,在國外時就一心只為自己的事業開拓門路。當他歸國半年仍沒能找到滿意的工作時,卻將原因歸結于自己沒有打進任何一個團體或者派系,于是轉頭抓到了焦委員這一根救命稻草。文博士的所作所為從始至終都是為了升官發財,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卑瑣勢力的小人,最后竟也如愿弄到了一個委員的頭銜,娶到了富商小姐。小說中寫到文博士“粗眉,圓眼,鼻子橫寬,嘴很厚”,長相不甚體面卻自鳴得意,“最得意的是臉色,黃白,不暗,老像是剛用熱毛巾擦完,撲上了點粉那樣。這個臉色他帶出些書氣”。神態表情十分矯揉造作,聽人說話時“嘴角用力下垂”;自己開頭說話則“圓眼會很媚的左右撩動”;說得意了還要“微微吐出點舌頭,‘啼!迸出些星沫”。老舍在小說中對文博士的肖像、心理等都進行了夸張的描寫與變形,刻畫出文博士一副惺惺作態的丑惡嘴臉。老舍曾說:“幽默諷刺的文學藝術并不是老老實實的文字排列,而是帶有各種招笑技巧的文字組合,其在給讀者帶來啼笑皆非的感受之時還能夠對其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1]老舍用平易通俗的文字組合出幽默詼諧的效果,在引人發笑之余達成了對人物丑陋嘴臉的直觀揭示。
文博士心無點墨卻還自視清高,剛回國被安排到條件差的“齊魯文化學會”時,他竟還兀自產生“鮮花插在牛糞”上的煩惱。出門走上骯臟的街道讓他覺得惡心,名勝名泉剛讓他陶醉的忘乎所以,下一秒臟臭的中國人又讓他怨聲載道,于是苦悶到想要迷信地去占一卦,道士的好話又瞬間讓他心中痛快。這一路情緒的一波三折,滑稽而可笑。從中也能夠看出,文博士雖然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熏陶,對國內的社會現狀深感不滿,骨子里卻依舊埋藏著封建主義的幽魂。他是中國封建主義與外國資本主義的混血兒,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下的特殊產物。這一點也相當深刻地體現在他思想和行為的矛盾性上:人雖已回到國內,卻還是用著“美國帶回來的皮拖鞋與紅地黑花的浴衫”,穿洋服、吃西餐;支票要全英文的,簽名也要花里胡哨看起來像個洋人;安置房屋,要把從美國帶回來的“級旗”釘在墻上,再配上兩張在美國照的相片。他請唐先生在西餐廳吃飯,也要處處顯出“西洋紳士”的氣派。他在那些能象征“美國精神”的行為舉止中尋找優越感與慰藉,卻反襯出自己學識的淺薄和內心的空虛。他處處標榜美國的規矩和方法,但不僅留學讀博是抱著封建的“中狀元”心態,回國后更是一心靠著舊中國腐朽落后的關系網、裙帶風,靠攀附權勢來一步步往上爬。這些洋不洋中不中的矛盾思想及行為,在幽默之余,表達了老舍對西方留學帶回的不是先進的文化和思想,反讓物質文化滲透至中國已然枯槁的肌體現象的諷刺。
文博士的事業全靠拉攏關系以及投黨結營,在成功找上楊家之前,他并不是沒有碰過壁。他拿焦委員給的名單找上的頭家是商會副會長盧平福,但這人同樣是個利益熏心、成天想著吸人血的商人,見文博士沒用根本無心幫他。這一次的失敗讓文博士憤怒異常,但他不僅沒有檢討自己的學問,反而覺得是自己缺乏經驗,為什么在去之前沒有打聽情報,乃至將罪過推到老唐身上,“他覺得自己還是堂堂的博士,并沒有什么毛病”。之后從唐振華那得知盧平福也是留學生,立馬心情舒暢,“怪不得說不過他呢,原來這家伙也有學位”,且都是留學生,“那么誰說得過誰也就沒大關系了,在盧家的那一場滿可以一筆勾銷了”,活脫脫就是那挨了打卻還自我寬慰是兒子打老子以維護自己那點可憐的自尊的阿Q的形象。可以說,《文博士》延續了老舍諷刺中含帶幽默的一貫筆法,淋漓刻畫了文博士此類留洋派知識分子的丑惡嘴臉,對濟南上流社會成員“錢本位、官本位”的腐朽思想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二、對比諷刺
善與惡、理想與現實、光明與黑暗,老舍的小說十分善于設置對比,或將人物的言語、行動,人物前后表情、態度的變化進行對比,或將人物所作的事件及造成的不同結果進行對比,從而在沖突對比之中使情節完整,人物形象也在對比中完善,達成鮮明的諷刺批判效果。
在《文博士》中,老舍成功塑造了一正一反兩個女性形象。首先是正面角色唐振華,也是小說中唯一的一位正面角色。她雖相貌平平,但態度平和,舉止端莊,“像一朵秋天的花,清秀,自然”。作為小學教員的她,識大體,顧大局,見地深遠,雖身處一個“老的東西不放手,又不肯徹底的取納新的”的陳舊家庭,卻仍然不卑不亢,不與自己虛偽的父兄同伍,拒絕父親讓她嫁給文博士的安排,有著自己的尊嚴與思想。她大方地勸解文博士,不要想著不勞而獲,自居上等人,“工作的本身就是最高的報酬,勞力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也不要將婚姻作為向上爬的工具,只為有錢,而不為找個真正能幫助自己的。話語一針見血,有力量有態度,又借著家人和自己來說事,不正面攻擊,善良且溫柔。更為可貴的是,在文博士并沒有接受她的好心相勸時,她也好心地告知了父親刻意隱瞞的有關楊家的消息,沒有算計亦沒有怨懟。
在老舍的筆下,受人尊重令人喜愛的女性形象有很多,即便是有所沉淪的,他也表示了同情及憐惜,如《駱駝祥子》中的虎妞、小福子等,而對《文博士》中的楊家六姑娘,他雖沒有直言褒貶,但在與唐振華的隱性對比中,透出犀利深刻的諷刺。作為富商楊家六姑娘,楊麗琳早在奢靡的家庭風氣中墮落,明明在生命正發展的時期卻似乎厭煩了生命,失去了精神與自我。對她來說,生活只是一種游戲,她只需從游戲中找到快樂和榮譽,“她的理想、虛榮、急躁、標準、貞純、污濁、天真、老辣、青春、欲望、嬌貴、輕狂凝在一起,組成一個極細密的網”。這張網起初網住了那個大學還沒畢業的朱先生,楊麗琳不久就有了身孕,但她并不喜歡朱先生,也看不起一個大學資格,所以墮了胎并打發走了朱先生。這一次網終于網住了一個“博士”,她的虛榮心和期盼得到了巨大的滿足,于是順理成章,“有錢而沒資格”的她和“有資格而沒錢”的文博士結了婚。從兩者的對比描寫中,老舍對于兩位年輕女性的愛與憎、尊重與鄙夷,分明可見。文博士在兩相對比之中所進行的選擇,不是唐振華而是“有錢”的楊家六小姐,無疑加深了諷刺的力度,將人性的自甘腐化、自甘墮落刻畫得淋漓盡致。
除此之外,小說中同樣以較多筆墨刻畫的唐先生——唐孝誠,亦值得我們注意,文中對于唐先生的塑造處處在與文博士的對比中展開。同處濟南上流社會,唐先生實際上與文博士在心理上存在許多相似之處。初見文博士之時,他是受了焦委員的安排,因而惺惺作態,“顯出十二分虛假而親熱”“再三再四的伸手,拱手,彎腰”,擔當接過文博士的名片,看到上頭只有美國哲學博士一項,“他的臉馬上把笑紋都收回去”,與文博士同樣的勢力、同樣的媚俗。但當文博士“博士就是狀元”的說法稍稍打動他時,他又順理成章地開始謀劃如何給自己撈好處。他們都不大看得起對方,但又都妄圖利用對方來使自己得到好處。他們的差別之處,主要在于那一個“博士”頭銜,沒有這樣一個“敲門磚”的唐先生,雖辦事能力和手筆都不錯,但“有才而無資格”,所以只能靠與文博士合作來往上爬。他處心積慮了解文博士,摸清對方不過胃口大而學問不多時,就開始了自己的計劃,讓文博士教子女英語。之后為文博士到處奔走,打探委員會的事,則是希望文博士當上專員后,自己的兒子建華就能當個助手。雖然全靠自己奔走,但自己或兒子都沒有這個博士資格,只能為了兒子出路,借用文博士的這個名位。而他猶豫再三將文博士引薦到楊家,雖對楊家的金錢及勢力心有不甘,但想到楊家小姐的底細及對這事“必定得糟”的自信,他還是答應了。他心想的是“這是幫忙,也是報仇,一打兩用”。然而他沒有想到事情不僅成了,且成得如此順利,更沒有想到的是,文博士雖順利當上了委員會的專員,卻過河拆橋沒有履行讓自己兒子建華作助手的承諾。一個無學問而空有博士頭銜,一個手筆不錯、辦事也能干而無學位,兩者結局令人唏噓,一個順竿而上,一個竹籃打水一場空。在他們兩者的悲喜劇對比之下,“學位”“學問”失去了本來的意義,成為招搖撞騙者扶搖直上的憑借,成為空虛鄙陋者名利雙收的墊腳石。對于唐先生的悲劇,作者也并無惋惜之意,在女兒唐振華勸他休息休息,“從新用對新眼睛看看這些事”時,他還只想到他的委屈,只想到自己不該為他人作嫁衣,卻仍“根本不能承認這個社會的腐臭”,可見已經深受官本位錢本位的腐朽思想的荼毒。老舍以嘲謔諷刺的犀利文筆,在他們兩者互相利用的細節及不同結局中,鞭撻了這些舊中國“儒林”中的敗類。
三、敘事諷刺
從敘事學的角度來解讀《文博士》中的諷刺藝術,我們可以發現,不同于《貓城記》中隱含作者與敘述者“我”的諷刺態度基本一致——都是持批判否定態度,《文博士》中隱含作者的態度實際上與敘述者相對立,而敘述者及他所敘述的對象都是隱含作者所要諷刺的對象,敘述者“文博士”既是諷刺的主體,又是諷刺的對象。在隱含作者、敘述者及人物的復雜變化關系中,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立場、所持觀點及態度的錯落有致中,精彩絕倫的諷刺得以完成。
小說主人公文博士回到國內,處處看到中國的“沒希望”,甚至看到城墻就惡心,因為自己這樣一個博士,回國半年竟然找不到事做,錯處只能是在國家與社會,“一個瞎了眼的國家,一個不識好歹的社會”。找唐先生幫忙時,看不起唐先生那“一套落伍的衣裳禮貌與思想”,覺得“博士就是狀元”,自己有了博士頭銜,就有了做官謀事的一切資本。在這里,小說的敘述者走到臺前表演,諷刺社會及他人,而當敘述者在諷刺別人時,隱含作者實際上連敘述者也一起諷刺了。此外,還有隱含作者想批判的事物,敘述者反而贊揚;隱含作者贊賞的事物,敘述者卻橫加指責的情況,在敘述者與隱含作者之間形成對比,以此構建諷刺的張力。文博士在美五年,不專心讀書做學問,而是整天忙于結識朋友,投身于瑣碎空虛的交際與自我宣傳,希望借由這些人回國后順利地找事做。而因無聊世故的交際導致論文交不上延長了一年時間的留美經歷,在文博士看來卻是“不虛此行”。在這里敘述者文博士所樂于宣揚付諸行動的,恰恰是隱含作者所鄙夷的,老舍正是通過文博士的態度與行為,來諷刺這類不學無術、功利心重、毫無民族責任感的留學生群體。另一方面,唐先生的女兒唐振華不希望父親整天忙于籌劃算計,看不起文博士們和自己的兄長“對于學問都想用很小的勞力,而享極大的榮譽”的態度,認識到他們的空虛與糊涂,乃至整個社會的腐臭,因而在與文博士交談中真誠袒露心聲,試圖進行一番勸解。但唐振華的這一番正直言論,文博士卻不忍卒聽,不愿意再與她交談下去,反而覺得她“根本不明白博士的價值,用不著再和她講什么”,覺得她“到底不過是個小學教員,怎能有高明的見解”。在這里敘述者所嘲弄、持否定態度的,卻是隱含作者以為正確的、可貴的。從全文來看,敘述者文博士站在自我的角度講述自己的所思所想,但敘述者的諸多看法卻并非是隱含作者的,而是與隱含作者的想法嚴重對立。在隱含作者與敘述者態度的對立錯位中,諷刺的張力更加凸顯出現。
其次,文博士作為小說的敘述者,自詡是有見識有能力的留美博士,回國之后,以自己的“美國眼光”對國內的社會進行了一系列的諷刺:城墻是破舊的,飯菜里能吃出個蒼蠅來,院西大街只呈現出“雜亂而又呆死的氣象”,整個社會陳舊而破敗。至于中國人呢?文博士來到趵突泉剛感嘆完中國的地大物博,泉水的蕩漾美麗,轉頭就看到“張著嘴放蔥味的黃牙男子們,那些雞雞嘹嘹的左嗓子歌女們,那些紅著臉亂喊的小販們”,這些人是“多么蠢、多么臭”,只覺得“丟人”。對于中國的社會情形、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敘述者進行了百般諷刺,隱含作者即老舍在這里正是借文博士之口來鞭撻社會的混亂落后,中國人的死氣沉沉,但在敘述者文博士不斷痛斥“中國沒希望”“這就是你們中國人”“都是你們中國人”時,他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且從骨子里就浸透了腐臭的封建思想。他聽信道士“婚姻動,謀事有成”的卜卦,覺得道士也“可愛”,中國的老事兒也有許多合乎科學原理。自己的博士頭銜就是資本,博士就是中國古代的“狀元”,憑借“博士”自己就得娶有錢人家小姐,就能飛黃騰達,官財兩收。由此可以看出,隱含作者既借敘述者之口諷刺中國社會,同時敘述者也成為隱含作者的諷刺對象,敘述者既是諷刺的主體,又是諷刺的對象,這雙重諷刺不僅延伸了諷刺的對象,亦加深了諷刺的力度。
參考文獻:
[1]朱秀英.老舍與錢鐘書小說幽默諷刺藝術的比較研究[J].山東社會科學,2015(S2):471-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