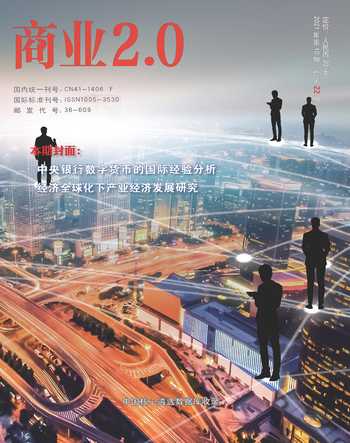淺談數字貨幣應用風險與監管對策
王鵬飛
隨著數字經濟不斷發展,數字貨幣應用場景和范圍亦將逐步擴大,對經濟、金融和社會影響也日益增強。數字貨幣產生于互聯網,發展也依賴于互聯網,這導致數字貨幣和金融體系中存在的各類風險危害更容易傳染和放大。同時,數字貨幣的技術復雜性和交易私密性也致使數字貨幣中各類風險更不易識別和評估,具有嚴重的不可預知性。數字貨幣發展關乎經濟、金融和社會各個方面,涉及其中的利益攸關方包括政府(國家)、數字貨幣持有者(投資者)、數字貨幣發行人(ICO融資者)以及數字貨幣交易商。他們在數字貨幣體系中角色定位不同,承擔的風險亦各有差異。亟待結合域內外數字貨幣應用風險監管的實踐經驗與問題,積極完善數字貨幣的監管方案,建立數字貨幣有序嵌入各行各業的最優監管模式,全面賦能數字經濟健康成長,促進社會健康發展。
一、數字貨幣應用風險
數字貨幣依賴于區塊鏈技術和一個系統,這就會使其遭受安全沖擊,比如計算機系統的黑客攻擊,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看到過很多實際問題。由于數字貨幣交易存在中間商,這些中間商不同于現實中的組織。現實中的組織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但數字貨幣的中間商是在網絡上的,風險更大。數字貨幣具有匿名性、快捷性和不可撤銷性,加上比特幣等數字貨幣在世界范圍內具有高流通性,因此很多不法分子將數字貨幣作為新型洗錢渠道。而且,通過數字貨幣洗錢有很多種不同的實現方式,總體而言,新型洗錢方式被發現、查處的幾率比以往更低,很多國家還沒有有效地打擊數字貨幣洗錢的手段和技術。這些因素導致不法分子更青睞這種洗錢方式。由于數字貨幣交易所更多的是由單個企業提供的交易平臺,更是一個中心化的產物,所以,在數字貨幣交易的環節中,屬于最容易受到攻擊的。比如,我們經常會看到某某交易所系統出現漏洞;或者,某某交易所被黑客攻擊等新聞,用戶在平臺上存管的數字貨幣被大量的盜取,以至于很多交易所無力承擔損失,而宣布破產。數字貨幣并非真實貨幣,沒有中央銀行在背后進行總量控制和宏觀調控,其是否值錢完全看其供應量。例如,根據中本聰的算法,最終BTC的供應量是2 100萬個,不會再增加。
二、數字貨幣應用的監管難題
(一)央行數字貨幣自身的安全問題
區塊鏈技術具有可編程拓展性,如果加載在區塊鏈的拓展應用存在后門或者安全漏洞,將會對交易安全構成較大的安全隱患。央行數字貨幣基于區塊鏈的分布式記賬技術建立,其對于互聯網的依賴較于傳統的移動金融支付更甚。與央行數字貨幣運行原理接近的比特幣就曾發生過嚴重的黑客攻擊事件,如 2017 年 5 月發生了惡劣的 WannaCry 勒索事件,這場事件造成 23000 臺電腦設備受到感染,范圍涉及 150 個國家、幾千家企業和公共組織,影響到金融、能源、醫療等行業。央行數字貨幣與比特幣類似,其能夠成功運行依靠的是全網的節點完成計算量,所以僅是一個小節點被黑客攻擊,便有可能誘發全網的癱瘓。
( 二) 匿名性產生的不法交易
央行數字貨幣匿名性的特點,固然滿足了使用者保護個人信息的需要,但也成為諸多不法交易的溫床。央行數字貨幣基于區塊鏈所具有的匿名性特點的運行原理與比特幣相類似。由于比特幣不依靠特定的機構發行,根據特定算法通過大規模的計算產生,并使用密碼學原理來確保各個環節的安全性,比特幣不僅具有了匿名性且不易溯源,使數字貨幣交易追蹤工作變得越發困難,容易滋生非法交易和洗錢活動,如 2013 年 10 月,美國多個執法部門查繳了一個使用匿名不法買賣的電子交易平臺,其創始人羅斯·烏布利希短短兩年就將該平臺變成網絡世界最大的 “黑市”,在該平臺上,通過比特幣支付可以得到以下非法服務,包括辦理假證件、買賣槍支毒品、器官交易、提供性服務等。若央行數字貨幣像比特幣一樣完全去媒介化,沒有被監管部門有效監管,其可能導致的后果不堪設想。
(三) 相關法律制度的不適用
我國以實物貨幣為標的,以憲法為依托,制定和實施了現行的與法定貨幣相關的法律法規。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法》在第四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中國人民銀行 “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明確授權中國人民銀行代表國家行使貨幣發行權。但是目前對貨幣的定義和發行制度僅停留在紙幣和硬幣層面。然而,數字貨幣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實物幣,有相應的面值和種類以及實物形態,并且與實物貨幣在發行、流通、存儲等環節上,有著本質的不同。現行的法律法規監管框架無法完全將央行數字貨幣囊括其中。另外,在貨幣法償性問題、貨幣所有權轉移以及反假幣等專項問題上均存在法律法規的不適用,亟待進一步的規制和完善。
三、風險監管對策建議
出臺數字貨幣法律法規。為數字貨幣的發展提供法 律支持,并為數字貨幣監管提供法律依據。我國可以充分參 考歐美、日本等國建立的金融監管貨幣,對其進行一定調整后與數字貨幣結合在一起,將其落實到我國數字貨幣監管體系中,確保其能夠發揮出應有作用。監管部門可以通過設置行業準入門檻、注冊審批的方式對數字貨幣設置較高的門檻,為滿足相關標準的企業、機構發放營業牌照。
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機制。數字貨幣服務平臺必須要定期將自身財務情況向外界披露,且平臺所有參與方都被納入央行征信體系內,確保消費者合法權益得到保障。根據學者們調查結果來看,我國目前還未將虛擬貨幣納入金融監管體系,且加強了虛擬貨幣的管控,但仍然有虛擬貨幣在民間流通。
建立數字貨幣交易監管平臺。監管機構可以將所有數字交易平臺納入自身監管范圍內,利用大數據技術對交易平臺各項交易信息進行分析,還可以利用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提升自身監管能力,使自身能夠對數字交易平臺發展情況保持密切關注,將相關風險控制在較低水平。還可以建立風險預警機制,當數字貨幣風險出現時,可以及時介入并管控風險,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根據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提供信息來看,我國已經加強了金融監管科研投入,這些可以為建立數字貨幣監管體系提 供技術支持與發展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