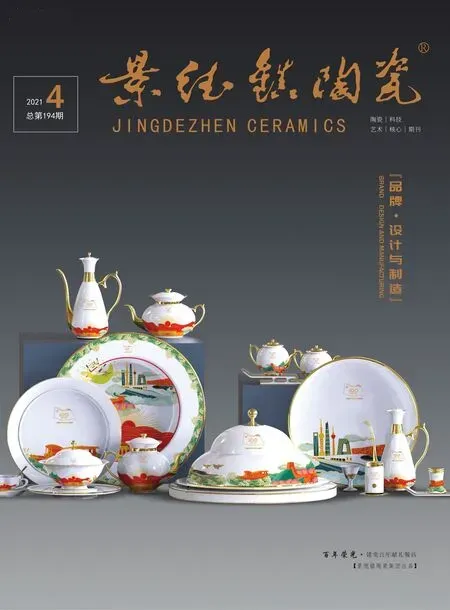淺談淺絳彩的由來與工藝特性的文化價值
于 杰
一、陶瓷“淺絳彩”一詞的由來
“淺絳”原指是黃公望在中國山水畫設(shè)色技法中所創(chuàng)的一種以墨色勾勒,以淡赭、淡花青等染色的一種表現(xiàn)手法。清末民初,尤其是程門畫派、皖南畫派為代表的藝人將這種設(shè)色技巧移植到陶瓷表面,后來還延伸到花鳥、人物等的創(chuàng)作中,逐漸發(fā)展成為一門獨特的陶瓷藝術(shù)語言,至此,“淺絳彩”便成為陶瓷裝飾的專用名詞,形成了大小寫意、工兼寫、詩書畫印相結(jié)合的一種文人畫氣息濃郁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這一陶瓷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在1912~1927年比較盛行,此后日趨衰落,雖是曇花一現(xiàn),卻風(fēng)靡一時,對當時及后期陶瓷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與發(fā)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影響。
如圖所示為清光緒十四年程門所創(chuàng)作的淺絳彩山水瓷板畫,題識為“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戊子年立春程門寫于珠山。”鈐印門。整個作品畫面色彩淡雅柔和,筆墨松弛有度,虛實層次有秩,整體氣韻暢通,采用了慣用的文人畫法,詩書畫印相結(jié)合,使整個作品既樸素自然,又曲折有致,還給人以強烈的情感帶入,是淺絳彩瓷的典型代表。
二、淺絳彩繪瓷藝術(shù)的發(fā)展
在瓷繪發(fā)展的歷程中,陶瓷繪畫對中國畫的臨摹、借鑒尤為明顯。明朝中后期,藝術(shù)領(lǐng)域倡導(dǎo)引書入畫,清中后期又將引書入畫逐漸衍變?yōu)閷懸夤P法畫,這種藝術(shù)風(fēng)格的衍變也同樣影響了陶瓷裝飾的發(fā)展。最為直接的要屬備受追捧的黃公望藝術(shù)形式,它在歷代畫壇都影響極大,這也是當時陶瓷繪畫借鑒這一藝術(shù)形式的主要原因;加之清朝末年,四百多年制瓷歷史的御窯廠被毀,大量工匠藝人流落民間,在社會動蕩不安和經(jīng)濟衰落的境況下,工匠開始尋求更加快速、便捷的制瓷方式;同治五年,李鴻章恢復(fù)御窯廠,甄選募集了一批徽州地方畫家入御窯廠從事繪瓷行業(yè)。這都在一定程度上為淺絳彩文人瓷畫的興起提供了契機和動力。
景德鎮(zhèn)的陶瓷制造業(yè),自漢代開始,制瓷歷史源遠流長,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來景德鎮(zhèn)定居和經(jīng)商。清朝末年,不少徽州幫來到景德鎮(zhèn)經(jīng)商、謀生,但受到景德鎮(zhèn)當?shù)亻T派、行規(guī)、傳藝等因素的種種限制,只能另起爐灶,便出現(xiàn)了程門、汪藩等在內(nèi)的一行人,嘗試將黃公望“淺絳”國畫技法運用到瓷器載體上作畫的開始,其效果令人稱奇,在當時景德鎮(zhèn)制瓷業(yè)引起一片嘩然,此后淺絳彩陶瓷藝術(shù)得到迅速的發(fā)展。
“淺絳”在中國畫上只適用于山水的描繪,但在淺絳彩瓷畫藝術(shù)上,除山水題材外,還出現(xiàn)了大量的花鳥、人物等題材,這源于宋代花鳥畫范本和部分海上畫派文人畫的影響。山水畫以寫意為主,意象地自由抒發(fā),花鳥畫沿用宋元及海上畫派畫本,人物以寫生、寫意手法為主,仍具有文人畫的風(fēng)格特點。多方面的藝術(shù)借鑒與融合使絳彩瓷畫中的花卉、飛禽、走獸等生機盎然、靈性十足,真正達到了傳神達意的藝術(shù)效果,而且瓷畫借鑒了紙絹畫一直以來題詩書印款的習(xí)慣,力求在瓷面上呈現(xiàn)出一副完整的文人畫藝術(shù)組成,無論從構(gòu)圖、技法、立意,還是效果上,都毫不遜色當時的紙、絹畫作。加上陶瓷材料的三維空間造物特性,最終表現(xiàn)出一種脫離實用器皿物質(zhì)外殼,以觀賞為目的的一種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
但是由于淺絳彩技法存在賦彩薄、觸感澀、易磨損和脫落的局限,而顏色鮮艷不易脫落的“洋彩”料的引入,以及新粉彩更加細膩的表現(xiàn)形式的沖擊,使淺絳彩這種藝術(shù)形式逐漸走向沒落。
三、淺絳彩的文人藝術(shù)與工藝特性

程門淺絳彩山水瓷板畫
在景德鎮(zhèn)制瓷行業(yè)內(nèi)流行一句行話,“共計一坯之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jié)目,尚不能盡也”。這是對景德鎮(zhèn)制瓷工序真實而準確的描述。以粉彩為例,長期以來,景德鎮(zhèn)工匠文化程度不高,分工細致,在長期的“重復(fù)性”實踐中,精益求精,練就且僅練就了單一的工藝技法或題材形式,可以說幾代陶瓷匠人不斷地將中國工筆畫的樣式搬到瓷器表面裝飾,樣式雖然精美,但卻匠氣十足。與之相比的淺絳藝人則大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養(yǎng),有著自主的審美觀念以及鑒賞美和創(chuàng)造美的能力,他們最大的優(yōu)勢是能夠從設(shè)計到描繪再到上色一系列工藝由自己完成,而且他們當中多數(shù)人兼善山水、人物、花鳥等各種題材,能自由地表達個性與情感,使淺絳彩瓷融入文人畫情趣,淡化了一直以來陶瓷的工藝與裝飾性,強化了文化與藝術(shù)的情感表現(xiàn),使瓷器裝飾脫離了傳統(tǒng)的匠人瓷畫特點,具備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主體性,所以人們常說粉彩板而淺絳活。
在原料方面,淺絳彩繼承了傳統(tǒng)粉彩工藝技法的同時又有所創(chuàng)新,在鈷料中經(jīng)過加入適當?shù)你U的成分進行一種“粉料”的調(diào)配,增強了粉料的固色性能,同時也由于粉料中摻入了鉛元素使原料中鈷的成分含量降低,其料的發(fā)色變淺變淡,再配以淡赭、水綠、淡藍等色渲染,燒制后呈現(xiàn)出一種淡雅、光澤感低、類似中國水墨畫效果的瓷畫作品。
在填色方面,淺絳彩摒棄了粉彩中所用的玻璃白打底方法,直接在胎體上用料進行描繪,這種施色特點對比柔和、色彩淡雅,猶如宣紙水墨畫上的藝術(shù)效果,但色階的過渡又有瓷畫的質(zhì)感,料色的濃淡、薄厚又比紙畫、絹畫更加強烈,既與文人山水畫、花鳥畫技法一脈相承,又帶有獨特的淺絳彩藝術(shù)效果。
縱觀大部分淺絳彩藝術(shù)作品,色彩對比柔和,空間布局講究,不僅具有文人畫把詩、書、畫、印融于一體的藝術(shù)視覺效果,更在畫意中結(jié)合了引書入畫的筆法,具有金石意味的筆意,同時給人以深遠曠達的藝術(shù)意境。淺絳彩瓷曾一度成為時尚,各種淺絳彩瓷藝術(shù)瓷、日用瓷,尤其是盤、碗、杯、瓶、罐以及文房用品迅速遍及全國各地,受到各方各界的喜愛。
四、結(jié)語
淺絳彩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成功地把文人畫藝術(shù)轉(zhuǎn)接到瓷繪藝術(shù)作品中,它的出現(xiàn)打破了以往彩繪千篇一律,只重工藝的不足的現(xiàn)象,讓瓷繪藝人們在思想和眼界上都有了新的認識與覺悟,迫使他們開始嘗試技法上的變通與改進,為瓷繪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形式尋求了新的突破口和方向標,使景德鎮(zhèn)繪瓷業(yè)呈現(xiàn)出了新的面貌與活力,也為瓷繪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新發(fā)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它雖存亡不足百年,但獨樹一幟的風(fēng)格表現(xiàn)和工藝的嘗試與探索都值得我們不斷思考和學(xué)習(x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