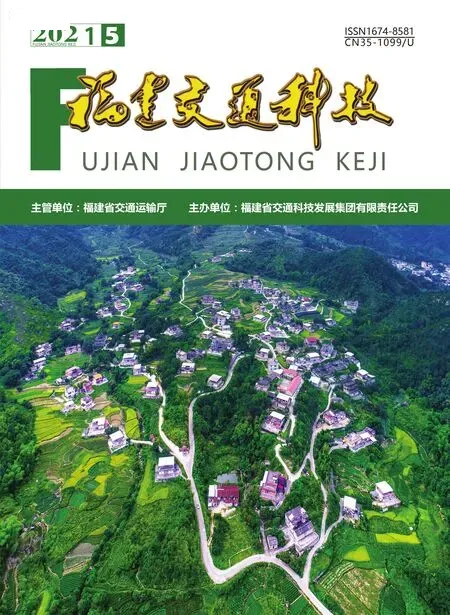某降雨型中-淺層滑坡成因分析
■余海強
(福建省交通規劃設計院有限公司,福州 350000)
1 引言
截水、 排水工程是滑坡治理工程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大多數情況下對于降雨型中-淺層滑坡應優先考慮排水工程, 并在滑坡防治總體方案基礎上,結合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條件設置地表截水、排水和地下排水方案[1-2]。本試驗采用了以地表截水、排水和地下排水方案為主要治理手段,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2 滑坡場區工程地質條件
滑坡場址區處于多座火山中心附近的空落相、碎屑流相、火山通道相、噴溢相區域。 4 座火山間歇性交互作用形成了該區域火山灰、碎屑流、熔巖流交互沉積的復雜地質環境, 最終形成了凝灰巖、含礫凝灰巖、 熔結凝灰巖等多種巖性組合的復雜場區。 熔結凝灰巖相對于凝灰巖堅硬,且不易于風化,由鉆孔揭示巖芯不難發現, 該場區凝灰巖均已風化成土狀, 而熔結凝灰巖多為大塊或整板狀孤石置于凝灰巖風化層中。 再經區域地質構造運動,致使場區內巖土層差異風化更加強烈,形成了多條風化凹槽[3]。
由場區微地形地貌特征可將其分為A、B、C 3 個區域,A、C 區為B 區兩側山脊,A 區覆蓋層厚度>B 區覆蓋層厚度>C 區覆蓋層厚度。 C 區覆蓋層最薄且在坡腳處發育反翹形式的基巖,好比天然的抗滑樁擋在C 區坡腳前緣, 也擋住了地下水的排泄,使其向B 區改道。全風化凝灰巖、砂土狀強風化凝灰巖多穿插發育于熔結凝灰巖及其風化層中。 場區水文地質情況為地表水、地下水排水條件A 區最好,C 區最差,B 區介于兩者之間[3]。
土工試驗成果顯示殘坡積層及全風化、砂土狀強風化層均屬高液限土。 由表1 可知,土層直接快剪的內摩擦角在18°~25°,與天然坡體坡角接近;進行飽和快剪時內摩擦角僅在11.3°~13.5°,土體的反復直剪殘余強度接近。

表1 土層室內試驗成果
3 治理后坡體再次變形破壞特征
滑坡現場觀測到的坡體變形特征如下:
(1)坡體后緣:A、B 區后緣未見明顯破壞特征,C 區后緣見拉張裂縫。
(2)坡面:A 區仰斜排水孔一直有地下水流出,坡面未見明顯破壞特征;B 區抗滑樁樁前土體被地表水沖刷垮塌,土體堆高2~4 m,土質較純地段坡面坡度9°~15°, 重力式擋土墻上未施仰斜排水孔,但坡面有地表水漫流痕跡。 由監測成果可判斷,樁前土坡沖毀較為嚴重的4、9、18 號抗滑樁穩定性尚可,天氣晴朗時抗滑樁前側擋土墻上重新施打仰斜排水孔,地下水自流一段時間后,監控量測成果顯示抗滑樁位移有較為明顯的回調收斂現象,23~27號抗滑樁水毀情況較輕;C 區坡面仰斜排水孔未施工,試驗場區開挖形成較大臨空面,采用框架錨索、錨釘墻結構加仰斜排水孔等措施綜合治理,坡面多處錨索、錨頭崩裂。
(3)坡腳前緣:A 區未見破壞現象;B 區1~22 號抗滑樁間坡體前緣未見明顯剪出破壞現象,24、25號抗滑樁前緣路面可見地表鼓脹裂縫推測該處滑動面向深層改造;C 區巖土接觸帶可見明顯剪出口,剪出口產狀與B 區早年發生的剪出口產狀基本一致:45°∠13°,C 區兩側剪出口高程與B 區早年發生的剪出口一致,但C 區滑動體主軸線上剪出口高程較兩側高10 m 左右,C 區經回填反壓加固措施處理后,坡體暫時穩定。
(4)滑動面:B 區1~22 號抗滑樁間的滑動面向下改造的可能性較小,23~27 號抗滑樁間的滑動面向深層改造可能性大, 且在樁底附近;C 區滑動面部分在全風化凝灰巖中,部分沿土石界面。
4 滑坡成因分析
滑坡一般發生在斷裂帶、堆積層、風化帶及巖土體的軟弱夾層所組成的斜坡地帶, 自下而上發展,規模不斷擴大。 從總體上看,影響該滑坡的成因有以下幾個因素。
4.1 人類活動因素
邊坡開挖施工前山體天然邊坡整體穩定。 施工開挖改變了山體的應力平衡, 坡體發生了位移,為保護邊坡的穩定,在B 區坡前二階平臺上設置了錨拉式抗滑樁, 坡前設置了重力式擋土墻,A、C 區設置了十字板錨索。 A 區設置了相對應的地表、地下截排水導流系統;B 區設置了地表截排水系統,但僅起到部分排水作用, 部分地表水被關在坡頂上方,直接下滲進入坡體,當雨量較大時呈漫流狀越過排水溝直接沖刷抗滑樁樁間土及樁前土體,且未設置地下水排水系統;C 區地表、 地下排水系統均未設置[3]。
4.2 水文地質條件
由地下水穩定水位等勢線圖(圖1)不難發現:A 區地下水位等勢線分布較均勻且相對疏松,即水力梯度相對較小; 在抗滑樁延長線上,A 區的地下水位埋深最深, 與地形地貌及地層條件相符,其排泄條件相對較好。

圖1 2016 年10 月強降雨后地下水水位等值線
B 區1~15 排抗滑樁間地下水位等勢線分布相對較均勻,水力梯度略大于A 區,地下水位隨著樁號增加而緩慢增加;B 區16~27 排抗滑樁地下水位等勢線分布有突變現象,且抗滑樁樁背處等勢線密集,即水力梯度大,地下水水位迅速提高;B 區地下水位態勢的主要原因有(1)抗滑樁阻擋地下水向坡下運移;(2)坡前擋土墻的阻擋;(3)B 區下游存在基巖面反翹突起現象, 再次阻擋了地下水向坡外運移,地下水水流方向改道大部分流向A 區下游。
C 區地下水同B 區16~27 排抗滑樁樁后地下水分布形態特征基本相似,水力梯度更大,地下水水位更高,C 區地下水位更高的主因與B 區第3 個因素相似,C 區坡前基巖面突起, 阻擋地下水順坡排出[3]。
場區地層發育比較混亂,A 區以土狀風化層為主,其間夾有碎塊狀強風熔結凝灰巖,巨塊狀孤石相對較少, 透水性相對最好;C 區開挖揭露坡面分布較多巨塊狀中風化熔結凝灰巖孤石,可視為隔水層;B 區介于兩者之間[4]。
4.3 大氣降水因素
根據當地氣象局提供的資料,2016 年初當地降雨天數較多,進入4 月后降雨更加頻繁。 2016 年7 月、9 月,場區遭遇最強臺風,7 月8-11 日受臺風“尼伯特” 影響, 局部地區24 h 最大雨量約222.5 mm, 超過百年一遇降雨量;9 月13-16 日受“莫蘭蒂” 超強臺風影響, 僅9 月15 日降雨量為70.1 mm;9 月17-18 日受“馬勒卡”臺風影響,9 月17 日單日降雨量為51.9 mm;9 月27-29 日受 “鲇魚” 超強臺風影響, 僅9 月28 日降雨量達157.6 mm。結合滑坡深部位移監測數據分析,2 次臺風后的一段時間內,坡體地下水位明顯上升,且無法及時排出,使土體迅速飽水軟化,土體自重增加,坡體下滑力增加,土體抗剪強度降低,抗滑能力減弱,坡體發生較明顯的變形活動;同時短時間持續暴雨造成抗滑樁樁間、樁前土體發生大面積的淺表層沖刷滑塌,樁前抗力喪失較多,導致部分抗滑樁出現向坡外傾斜現象。 持續強降雨是滑坡發生變形的主要外因[3,5](表2)。

表2 豐水期與枯水期坡體穩定性對比
由監控量測成果可以看出, 持續強降雨過后,坡體呈現向外傾覆的趨勢,但天晴后又會向坡體內收斂,如圖2、3 所示。

圖2 2016 年4 月-2018 年6 月地下水位埋深動態變化

圖3 抗滑樁位移量隨地下水位升降變化
由表3 可知,持續強降雨導致坡體地下水水位迅速提升,B、C 區地下水排泄條件較差, 坡體地下水較長時間處于高位,使得坡體土質軟化抗剪能力下降,是本次坡體變形的主控因子。

表3 場區地質條件對比
5 處治措施及效果分析
為防止降雨時地表水大量滲入坡體內,加劇坡體變形,建議在原有加固、支護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引排疏干地表水與地下水的措施; 在B 區24 號抗滑樁上邊坡約8 m 處,布設集水井與水平鉆孔進行深層排水;在A、B 區坡腳處重力式擋土墻上補充仰斜排水孔;在C 區基巖面較淺處增加7 根錨索抗滑樁進行強支護且在C 區抗滑樁上邊坡坡面上補充仰斜排水孔[3]。 在施工及完工后均對坡體進行變形觀測,及時了解施工及雨水對坡體的影響和變形的發展趨勢, 保證施工及高速公路運營安全,建立完善的監測安全預警機制,做到防患于未然。
集水井及仰斜排水孔施工后,場區所有監測孔內地下水水位均有下降且達到預期效果,原抗滑樁位移量也隨著地下水位的下降而回調, 呈收斂態勢,坡體穩定。 采用引排疏干地表、地下水的方案,不僅提升了坡體自身穩定性, 達到了治理的目的,同時還節省了大部分強支護的費用, 符合安全、科學、經濟、合理的設計原則[6]。
6 總結
(1)持續強降雨是引起本次坡體變形的主要原因,即異常、持續的集中降雨造成坡體地下水急劇抬高,且地下水堵在坡體內未及時排出,致使土體較長時間處于飽和狀態, 抗剪強度降低且自重增大;同時短時間持續暴雨造成抗滑樁樁前、樁間土體發生大面積的淺表層沖刷滑塌, 樁前抗力減小,造成坡體抗滑力不足,導致抗滑樁出現向坡外傾斜的現象[3,7]。
(2)對于降雨型中-淺層滑坡,一般情況下宜優先考慮排水工程,結合工程地質、水文地質條件,確定地表截、排水和地下排水方案。 計算滑坡的穩定性時應考慮截、排水工程的影響,而不只是作為滑坡穩定性計算的安全儲備,從而減少其他治理工程的經濟費用[8]。
(3)通過A、B、C 3 個場區地質條件的對比分析,表明地下水高水位持續時間決定了坡體的穩定性,地下水的排泄條件決定了地下水能否處于高位及其時間的長短,處治時應認真遵循“治坡先治水”這一治理原則[9]。
(4)對于降雨型中-淺層滑坡,地下水水位對坡體的穩定性影響大, 治理時不僅要考慮力學強支護,還應考慮強支護對水文地質條件的改變,以確定地表截、排水和地下排水綜合排水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