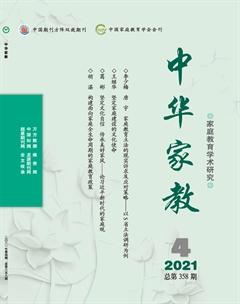家校社協同育人視角下的“拒學”概念、成因及應對策略
阮琳燕 史曉宇 何麗

從1996?年陳向明聚焦“王小剛為什么不上學了”的“輟學”議題,到2020?年我們關注“個別青少年為什么不上學”的“拒學”現象,一字之差,體現的不僅僅是25?年的時代變遷,更是時代所牽引的家庭在面對社會結構巨變過程中凸顯出的“力不從心”。表面看來,“拒學”(School?refusal)是指個別青少年在學齡期“不想去學校上學”的個體狀態,是學校出勤問題(School?attendance?problem)的一種類型[1]?;但其實,無論是主動拒學還是被動拒學,都是個體與社會之間,經由家庭所演變和呈現的社會現象。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拒學現象像是撥開湖面的水草一般滋生蔓延、浮出水面,一時之間讓越來越多的家長和教師手足無措。已有研究表明,我國廣州市中小學生的拒學行為檢出率為22.5%,且隨年齡增加呈上升趨勢。[2]?由此可見,學生拒學現象已經不再只是局限于極少數家庭的個體情況,而是全社會都需要引起重視的社會問題。
為了讓更多的家庭準確、理性地認識到身邊顯見或潛在的拒學現象,本文希望能夠從學術脈絡中厘清“拒學”概念并簡述其成因,進而提出“家校社協同育人”的干預機制與家長必須先行的“三步走”應對策略。
一、學術研究中的“拒學”:主動拒學與被動拒學
國外的拒學研究已有近百年的發展脈絡。Berg?就指出,有別于逃學、退學和學校排斥等情況,拒學是一種現象、行為,具有以下幾方面顯著特點:長期缺課、情緒困擾、父母知曉、不反社會。[3]?在最終發展為拒學表現時,青少年一般會歷經間歇性請假到長期缺勤的過程[4],并伴隨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不適特征[5],以及相應的中短期請假或長期休學行為。
由此可見,拒學既不同于厭學、逃學、輟學、退學或學校排斥,也不同于懼學、學校恐懼癥等現象,是一個目前我們正在逐漸辨清的現實情況和學術概念。
相對于拒學而言,厭學在《教育大辭典》中被界定為“一種消極對待學習的心理狀態,指厭倦、厭煩學習”[6],是一種比較負面的情緒,會直接引發消極結果。對于拒學來說,雖然也會出現負面情緒,但通過我們對14?組拒學家庭的質性研究發現,拒學既有被動現象,也有主動現象。因此,厭學從語言文化習慣的角度來說,與被動拒學相似,卻無法包含被動拒學中更復雜的狀況和主動拒學中的正面情況。
逃學、輟學和退學的概念,則是從教育管理學的視角,對學生的缺勤現象進行的界定,學校依據教育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等對學生的缺勤現象進行管理和應對。而學校排斥(School?exclusion)主要是指因為學校決策而導致學生不想去上學的缺勤情況?[7],強調學校決策層面而非學生主觀原因。懼學和學校恐懼癥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對學生不去上學的原因進行分析和判斷。懼學更加聚焦分離焦慮,學校恐懼癥則被認為與情緒障礙相關?[8],但均沒有確切的實證研究闡明其相關性。
通過上述概念的梳理,我們希望對目前社會輿論中的拒學進行“再定位”,盡可能減少公眾對拒學的污名化定義,拒絕給拒學現象簡單地“貼標簽”,從而為拒學“正名”——使拒學以一個中性詞的形象概念出現在大眾視野中。
筆者認為“拒學”是一個隨著時代發展所顯現的社會現象,包括主動拒學和被動拒學兩種情況,是一個中性概念。本研究通過深度訪談的初步分析發現,主動拒學是指雖然學生拒絕上學,但是并沒有拒絕學習,沒有明顯的社會功能損傷的拒學現象;學生依然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學習,社交興趣和能力也沒有太大變化;家庭會想方設法嘗試在家學習(Home?schooling)、出國留學或者創新教育形式。而被動拒學是指學生不適應或不認可學校教育,在一段時間內拒絕去學校上學并拒絕學習,且受到壓力進而出現心理情緒或軀體不適等問題,家庭(暫時)無法給予學生多種成長可能性的拒學現象。
二、“拒學”的成因:由家庭投射到個體,延伸至社會
關于拒學發生的影響因素,史曉宇將其概括為個人因素(心理障礙、個人特質)、家庭因素(教養方式、父母關系、家庭環境)、學校因素(學業壓力、同伴關系、教師行為)和文化因素。[9]
從個人因素來看,心理障礙是最為普遍的原因之一。臨床研究發現,兒童拒絕上學時常伴有軀體癥狀(54%)、情緒反應(77.3%);因拒絕上學而入院的兒童中有50%?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36.4%?被診斷為焦慮障礙(包括分離焦慮障礙、恐懼癥、強迫癥、癔癥),4.5%被診斷為心境障礙(抑郁癥、雙相情感障礙),9.1%?被診斷為品行障礙。[10]?此外,個人特質也是影響拒學發生的另一方面個人因素。一般而言,拒學兒童多表現為內傾、孤獨、情感封閉、情緒不穩、敏感多疑、焦慮、抑郁、敵意、是非感不強等神經質及精神質個性偏異。[11]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絕對不能將拒學的這兩方面因素與心理障礙和個人特質偏異直接畫上等號,這些因素只是分析拒學現象時可以考慮的可能性。
從家庭因素來說,高柏慧等的研究發現,相對而言,拒學兒童的父母給予子女的情感溫暖較少,在教養方式上表現出更多的控制、挑剔和忽視,且父母之間的關系較為緊張,家庭環境的學習氛圍較差。[12]?本團隊的研究通過關注北京地區14?個家庭,歸納出家庭引發學生拒學的主要原因為親子關系疏遠,甚至沖突。如父母無法理解學生的追星/?想當練習生或其他意愿,與學生在個人成長規劃方面難以達成共識。
從學校因素來講,國內目前鮮有對于拒學的直接研究。有關厭學的研究顯示,學生感受到過大的學業壓力、同學間的社交焦慮和教師對自己的控制等都會對厭學的發生造成影響。
最后,文化因素是從更宏觀的范疇去鏈接個體拒學行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目前國內也鮮有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我們之后系列研究的方向之一。
在這些因素分析綜述的基礎上,基于14?組拒學家庭的深度訪談,我們進一步確證:拒學現象不僅是學生行為發生的心理學議題,也不單是家長的家庭教育或教師的學校教育問題,更是學校和教育組織在管理/?干預制度,社會第三方機構(大學研究中心、心理咨詢機構、教育平臺等)在專業支持方面,共建共創的社會學話題。
以上這些研究的側重點往往聚焦于學生個體和家庭層面,雖然有對學校和文化因素的關注,但從應對路徑的角度來說,我國的拒學現象仍然被視為家庭需要獨自面對的困境,應對方案也單單指向個體和家庭,學校和社會等層面還未形成專門的干預機制。
三、“拒學”難題的應對策略:家校社協同育人
長期拒學,可能面臨一系列問題,所以需要研究動態過程及相應的綜合干預方案、長期陪伴方案、協同干預方案,從而對家庭實現精準幫扶,真正建構“家校社協同育人”的拒學干預機制。
我們通過對14?組拒學家庭的質性研究發現一個時間特征:近來學生拒學行為相對集中表現在疫情復學后,這樣的現象也散落于其他咨詢的家庭。可以說,疫情復學成為拒學現象顯現為社會問題的拐點。在這個從隱性家庭現象顯性化為社會現象的過程中,我們梳理了家庭尋求外部支持的七個重要階段。這些階段的發展并非線性單向,而是交叉或跳躍循環,并且充分體現了家校社協同育人的理念,如圖1?所示。

第一階段,手足無措,向內歸因。最開始遇到學生拒學,有些家長并不能夠及時識別,等到發展為較為明顯的被動拒學時,大部分家長都會表現出煩躁或暴躁的情緒和無措的狀態,很難理解學生為何不想上學。家長往往將學生拒學的原因歸結于學生個體,比如成績不好,與伙伴溝通不暢;也有歸因于學校的,認為教師教導不力等。也有部分家長頗為敏感,意識到學生出現了對學校的抗拒情緒,希望想辦法解決問題,但苦于抓不住問題癥結,沒有形成有效或系統的應對策略。
第二階段,孤立無援,向外尋助。當家庭無法承受向內歸因的重壓時,孤立無援的處境讓家長嘗試向外尋求幫助。
第三階段,網絡搜索,自主聯系。在向外尋求幫助的過程中,家長首先會在網絡中搜索相關案例和解決方案,或主動聯系身邊可能提供幫助的朋友。
第四階段,熟人介紹,專業咨詢。經由網絡和朋友的社會關系,拒學家庭會通過相熟之人聯絡專業人士,開始嘗試咨詢、了解相關知識,部分家庭逐漸走向我們所謂的“治療”階段。
第五階段,微信結盟,在線社群。專業咨詢或研究者介入拒學家庭之后,以微信為聯系工具,組建微信群,形成在線社群。“孤立無援的家庭”在微信群中遇到了來自天南海北的拒學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個體焦慮。
第六階段,公益活動,抱團取暖。國內已有拒學研究和服務中心正在籌建,且已開展了多次團隊和個體公益活動,來自不同家庭的學生和家長,能夠在線上和線下建構起“抱團取暖的社群”。
第七階段,結為伙伴,長期療愈。社群根據家長的參與討論和學習程度,可分為非正式社群和正式社群。非正式社群作為一種松散聯結的“網友”關系,家長在群里的發言以抱怨、討論和專業人士引導為主;正式社群則具有一定的封閉性,是一種緊密聯結的伙伴關系,由具有強烈改變意愿的家長和專業人士共同維護,討論和學習的內容更具系統性和專業性,家長的對話更具實踐性和方向性。
不難想象,真正走入社群并積極應對的家庭,能夠不斷營造“家校社共同體”的支持氛圍,呈現一種螺旋上升的趨勢,最終個別學生能夠成功復學或選擇其他適合的教育形式。但不可否認,也有學生及其家庭短期之內很難走出反復的惡性循環。
為此,本文為遇到拒學情況的家庭提出“三步走”應對策略。第一,理性認知,科學辨識;第二,尋求支持,抱團取暖;第三,調整家長,影響孩子。這三條應對策略環環相扣、缺一不可,而最為關鍵卻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第一步。所謂“因材”才能“施教”,只有相對科學、正確地判斷孩子處于哪種不想上學的狀態和原因時,家長才能做好短期或長期的應對方案。一方面,家長要多查閱相關資料,自主學習,并與教師積極溝通,比照孩子的拒學情況;另一方面,家長要盡早主動尋求第三方專業幫助,如心理咨詢/?門診、拒學研究中心或其他相關公益機構,從而得出相對準確的判斷。在不斷學習的過程中,家長會發現拒學并不是個別現象,可以找到“抱團取暖”的網絡或實體社群,這就為家長提供了共情交流的伙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家長的過度焦慮。最后,家長需要全力支持與配合,無論是家庭向內歸因和改進,還是向外歸因和溝通,都需要家長與孩子共同面對暫時的困難,以身陪伴,找到適合自己孩子的成長道路。
【參考文獻】
[1][7]Kearney,?C.?A.?Albano,?A.?M.?Children?Refusing?School?to?Avoid?Objects?or?Situations?That?Cause?General?Distress.?When?Children?Refuse?School.?New?York:?Oxford,2018,?pp.47-82.
[2]?陳玉霞?戴育紅?楊升平:《廣州市中小學生拒絕上學行為現狀分析與對策研究》,載《教育導刊》,2016?年第3?期。
[3]Berg,?I.?School?Refusal?and?Truancy.?Archives?of?Disease?in?Childhood,1997,?76,?pp.90-91.
[4]Kearney,?C.?A.?Introduction?to?School?Attendance?Problems?in?Youth.?Helping?Families?of?Youth?with?School?Attendance?Problem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9,?pp.1-18.
[5]?梅曉菁:《學生拒學的認知方式分析及學校和家庭的應對策略探索》,載《中小學心理健康教育》,2019?年第11?期。
[6]?顧明遠:《教育大辭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頁。
[8]Johnson,?A.?M.,?Falstein,?E.?I.,?Szurek,?S.?A.,?&Svendsen,?M.?School?Phobia.?American?Journal?of?Orthopsychiatry,?1941,?11,pp.702-711.
[9]?史曉宇:《他們為什么不上學?——北京市中學生拒學現象的案例研究》,北京聯合大學2021?年碩士學位論文,第14-17?頁。
[10][11]?王晨陽?林節?甘諾:《拒絕上學住院兒童的臨床分析及個性特征初探》,載《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2?年第6?期。
[12]?高柏慧?劉果?等:《青少年拒絕上學行為與氣質性格、父母氣質性格的關系研究》,載《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16年第1?期。
(?責任編輯:母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