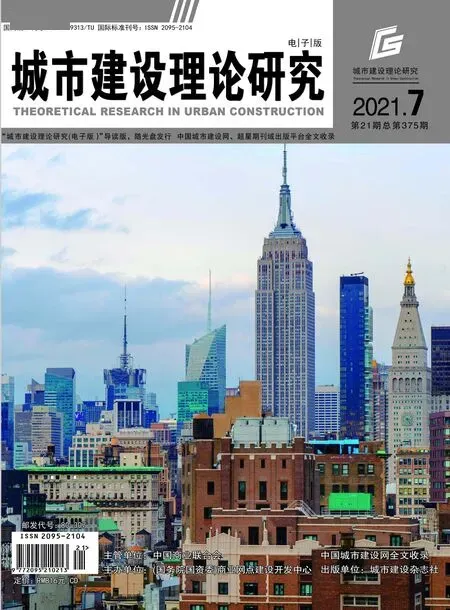數據技術支持歷史文化街區公共空間品質提升
——以上海衡復歷史風貌區為例
王澤夏
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 廣東 廣州 510060
1.引言
隨著城市發展逐漸進入緊湊化、精明化階段,歷史文化片區的保護更新問題一度成為大城市發展的重要課題。作為一個歷史悠久、文化街區數量眾多的國家,中國至今已確定了133個歷史文化名城,就上海而言,也制訂了44處歷史文化風貌區。
傳統的歷史文化片區更新方法是根據規劃者的經驗進行設計,經過多次調查和訪談后制定策略,但近幾年來,空間分析工具的進步和大數據的使用為公共空間規劃帶來了機遇。根據社會空間理論,空間規劃可以反映出社會結構和文化聯系,反之亦然[1]。也就是說,通過對一個區域形態結構和行為特征的分析,可以挖掘到該區域中具有良好區位條件的公共空間,也就更容易實現可持續的歷史文化保護區的更新規劃。這個區域形態結構的分析方法通常指的是空間句法,近幾年來,以SDNA為代表的空間句法的發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街道和道路網絡的空間配置,以及這種空間分配如何影響經濟活動和街道生活的方方面面[2]。本研究以空間分析方法和大數據為支撐,以上海衡復歷史文化街區為例,探討如何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進行歷史文化片區更新,提升社區品質。
2.上海衡復歷史文化街區
衡山路-復興路街區是上海市中心城區中規模最大、歷史要素最多文化風貌區,其中徐匯部分4.3平方公里。這里曾經十分繁榮,擁有許多代表性的海派建筑,但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加快,衡復街區原有的低密度、高綠化的特征逐步弱化,建筑老化、功能老化、人口老化的趨勢逐漸增強,私搭亂建的現象也時有發生。2016年,周珂、嚴澗等人共同完成了上海市風貌區保護規劃實施的評估工作,通過對實施效果的考察,認為衡復街區的整體反饋結果較好,但綠化種植和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還是沒有得到明顯改善[3]。
由于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護條例限制了建筑的拆除,許多老建筑中的居民動遷的愿望難以實現,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文化區的保護政策或多或少犧牲了當地居民的利益,因此研究希望通過規劃設計給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間,打造生活性道路的慢行系統,不僅保護了文化街區的風貌,也提升了當地居民的公共空間品質。
3.衡復街區道路中心性和基礎設施分布的關系驗證
研究采取街道中心性計算的方法,但因為街區尺度較大,將搜索距離變為500m、1000m、2000m、全局,分別對應著步行尺度和騎行尺度,方便同時規劃步行路徑和騎行路徑。結果顯示,不同搜索距離下的路網中心性呈現不一樣的結果,從舒適性來考慮,2000m和全局尺度可以規劃為慢性交通,可以跨街區布置連續的自行車道供市民和游客騎行。500m和1000m搜索半徑可以認為是居民日常散步步行路徑,由于步行距離遠小于騎車距離,只考慮在每個街區內部進行線路規劃,并將各個小的開發空間串聯在一起,形成散步和跑步的活動廊道。研究發現,搜索半徑為500的道路中間性高值點分布在各個地塊內部,因此在做步行路線規劃設計時,可以在每個地塊內部分別考慮設計步行路線。而搜索半徑為2000m和全局的中間性高值區分布則較為集中,貫通了整個地塊,可以考慮設計跨地塊的騎行路徑。

圖1 不同搜索半徑下的衡復街道中心性
另外,歷史文化街區內的公共資源主要包括優秀歷史建筑、公共服務設施、娛樂商業等三個方面,這些公共資源既有面向本地居民的生活性服務設施,也有面向游客的歷史建筑,因此公共資源的位置分布是選擇慢行路線和街區空間改造的重要判斷依據。利用百度地圖開放的興趣點,獲取到優秀歷史建筑、零售商業、飯店餐館、公交車站等公共設施的位置,并通對其做點密度分析以觀察其分布情況。可以發現,優秀歷史建筑主要集中于基地北部,因此在后續的規劃中可以將外來游客游覽路線偏向于地塊北側,以便起到更好的展示街區風貌的作用。
4.衡復歷史文化街區慢性系統規劃
研究使用公共空間網絡設計方式,采用因素疊加的方法進行線路選擇。衡復歷史文化街區的慢行系統網絡也包含兩種模式的路徑,一種是日常步行路徑,另一種是慢跑或騎行路徑,這兩種模式都是以街道中心性為導向的。由于日常步行線路主要服務于當地居民,因此方案以日常生活設施分布等條件為選擇依據,并結合街道中心性進行路徑選擇。另外,也考慮到人群活動強度的因素,一些中心性不強但商業活動較為活躍的地方也可被納入步行系統中。該線路的目標是使居民日常活動出行途經更多的服務設施,而對于現狀設施條件差的道路,也需要提出了改造意見,以使其空間品質得到提升。在騎行路徑選線時,利用搜索距離為2000m的中心性指標,除了基礎設施的分布外,還考慮了優秀歷史建筑的分布,這是由于騎行范圍遠大于步行,其路徑可以跨越街廓連接整片歷史街區。
慢性路徑規劃完成后,對選擇的步行、騎行路線進行實地考察,以便優化選線。通過現場調研,發現街道旁的小型公共空間被小汽車、共享單車占據,只剩下非常小的人行空間,因此這類道路需要在后續規劃中進行斷面改善。對于騎行線路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以肇嘉浜路和建國西路為例,這兩個路段被設計為自行車騎行路線,但就騎行體驗來看,建國西路交通量不大,自行車可以和摩托車混行,而肇嘉浜路為單向四車道,小汽車和摩托車的數量多,使騎行者體驗較差,不適合納入慢行系統中。可以把延慶路車行道取消,設計為人車混行,限制小汽車的涌入。另外,在地圖上顯示POI密集的商業區,在現實中多為沿街分布的小店和餐飲,這些低端商業雖然有助于提升街區活力度,但其無序擴散也會對風貌區的街道景觀產生不好的影響,因此后續規劃會對這些地段的商設施進行業態的整合與品質的提升。

周儉、梁潔等學者曾提出,衡復街區的街道空間較為均質,缺乏如“袖珍廣場”等節點設計,空間的辨識度不高。因此可以在每個庭院街區內設計一個節點空間,以提升地塊的識別性。對于歷史街區公共空間規劃,在保護傳統公共空間的同時,可以將部分傳統的非公共空間轉化為公共空間,或開辟連接傳統公共空間的新城市空間[4]。例如對于游客頗具吸引力的思南公館半開放的庭院就適合布置為節點空間。另外,文化風貌區內許多歷史街坊都存在圍墻,這種單調的街道景觀不僅使行人步行體驗趨于乏味,還影響了街區之間的連通性。因此在后續設計中,可以將此類圍墻打開,拓寬人行道路,一些稍大的開發空間也可以作為街頭廣場來設計,提升街區的環境品質和包容性。
5.總結
歷史街區的更新始終是城市規劃中需要考慮的問題,通常歷史保護區的生活環境質量差。歷史保護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當地居民的利益,因此需要為其提供更好的生活環境。以定量分析的方式設計街道網絡選線和公共空間布局是本文的重點,對于以往調研難以獲取的資源,如今可以通過多元數據分析得到,而對于環境復雜、基礎資料繁多的歷史街區來說,數據支持設計無疑是理想的選擇。空間分析(如空間句法、sDNA工具)和數據分析有其局限性,它們只是對空間的客觀描述,不能解釋人們的行為,人們真正的出行的原因是基于購物、工作等社會因素,并不是空間關系產生的結果。但不可否認的是,空間網絡分析工具以清晰的邏輯和科學的計算方法實現了設計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