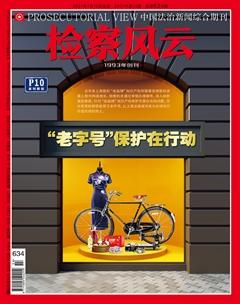楊曉鄔:三星堆還有很多未解之謎
楊曉鄔
“其實我也沒有數過,一共修復過多少青銅面具,大概三四十尊。”從1986年三星堆第一次考古發掘,大量前所未見的黃金和青銅物件出土,一醒驚天下;到時隔35年,三星堆祭祀區重啟發掘,6個祭祀坑出土象牙、青銅器、金器、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34件及殘破文物碎片近2000件,再醒驚天下;文物修復大師楊曉鄔始終與他心愛的三星堆文物在一起。
新出土:黃金面具最驚艷
記者:三星堆時隔35年,新發現了6座祭祀坑,500余件文物新出土,包括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的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這里面,哪件文物最能引起您的關注?
楊曉鄔(以下簡稱“楊”):我認為,最令人驚艷的當屬5號坑出土的黃金面具。上一次,在三星堆遺址中就發現了金面罩、金杖、金箔飾、金料塊及金箔殘片等多種金器,不僅種類豐富,且量多體大。作為權力之象征被運用于祭祀典禮,體現了古蜀人的金器崇拜。這與國內同一時期主要以玉器、青銅器為祭祀品的其他遺址相比,顯得非常特殊。此次發現的黃金面具,為古蜀文明中對于金器的崇拜,又增添了一大實證;同時其本身也攜帶著許多神秘信息等待揭開。
記者:那么,它較之前發現的黃金面具,神奇在哪里呢?
楊:以前1號祭祀坑出土過一件金面罩,大小、造型與同坑出土的人頭像面部可相匹配,可能是從某件人頭像上脫落下來的。但是這次5號坑出土的黃金面具,半張寬度就有(約)23厘米,高度(約)28厘米,重量(約)280克。雖然只是殘件,但從面具的尺寸和重量來看,可以肯定它不是覆在人頭像上的,可能是覆蓋在寬40厘米左右的青銅面具上的。據我了解,在全國,乃至全世界,如此巨大且厚重的商代金面具,還沒有出土過。
記者:這件黃金面具只有一半,會不會影響它的文物價值?
楊:不會,這才是最讓人興奮的所在。可能是祭祀活動完了,把它撕碎了,撕開成兩瓣,甚至幾瓣。從面具的背后看,已經燒得半熔化狀了,在它下面有一些金的珠子,我們猜測是金被燒熔后掉下來的,那就可能是另一半面具燒的。比起修復完成的滿足感和成就感,我更享受“考古”真正的樂趣,搞清楚文物背后的故事,搞清楚每一件器物為什么是這般模樣,才是最快樂的事情。
說修復:辦法總比困難多
記者:1986年三星堆第一次考古發掘完成后,你面對這么多前所未見的文物,更多是興奮還是著急?
楊:都有。喜的是,那么多珍貴文物一下子出土了;急的是,不少青銅碎片看起來只是混雜著泥土的“破爛”,經驗不多,人手更缺。其實當時干修復的,只有我一個人,后來才把郭漢中調來成都跟我學。
記者:是現在每天忙碌于祭祀坑挖掘現場的“四川工匠”郭漢中老師嗎?
楊:對,他是我徒弟。如今也足足修了35年三星堆文物,但當年他只是一個特別調皮的孩子。那時,我們在坑里挖文物,借他們家房子住。住久了,他就做一個假的陶器,放在坑里,看我們是不是看得出。那時候他才13歲,機靈、聰敏、勤奮,上手又快。最初就讓他跟著學點陶器(修復),后來三星堆有青銅和玉器陸續出土,就把他調來成都了。
記者:你們師徒倆守著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那間二三十平方米的小辦公室,是如何修復完成了那么多頭像、面具、銅尊和罍的?
楊:辦法總比困難多。一開始,是挺著急的。蜀人制作這些青銅器不是為了展示和欣賞。青銅器鑄造好后,很快就會被大力砸碎,然后堆進祭祀坑用火焚燒,用作祭祀。所以,三星堆數量龐大的青銅器發掘出來后,沒有一件是完整的。不光破碎,而且還因為埋土時候用力夯緊,導致器型扭曲變形,也有一些碎片被火給熔化了。比如,青銅大立人被發掘時,斷成了兩截,是被人為敲碎的,上下兩截。大立人的下半部分,在坑里氧化得比較厲害,它已經禁不起這個青銅大立人的重量了。我們在修復的時候,就得在下面進行加固。經過很多次努力,才把這個青銅大立人給修復了。
修神樹,七年彈指一揮間
記者:很難想象,那么小一間辦公室,要放下那么多大尺寸的文物。
楊:是的。修復縱目面具,最初以為修出來跟單人藤椅差不多大小,結果越修越完整,越修越大。修了兩三年,最后幾乎要把小辦公室撐滿了。每天看著它凸出16厘米的縱目,真是感到精絕雄奇。后來,單位挪出一間稍大的會議室給我和郭漢中用。不過,神樹的修復只能在室外,在高高的腳手架上進行。
記者:我們注意到,所有文物修復前后您都會拍一組照片存檔。神樹修復前的照片,看上去就是滿地的碎片吧?
楊:是的。當時,成堆的碎片滿滿鋪了一地,除了變形嚴重的底座,看不出任何樹的形態,甚至找不出一根完整的枝丫。文物毀損嚴重,這根本難不倒我。最棘手的是,這些東西我連見都沒見過,也沒有任何資料和線索。最開始我們都不知道它到底長什么樣子,就想著要把文物恢復到幾千年前的原貌,還不能有絲毫的差錯,簡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記者:面對“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你們最終完成了這株高達396厘米(中國古代青銅文物中體形最高大)的青銅神樹的修復,是如何做到的?
楊:只好用最“老實”的方法來修復。我們把東西分好類,先找出結構最簡單的碎片,而后根據碎片和碎片之間斷裂的縫隙結構,像玩拼圖游戲一樣把它們拼起來。就像愈合恐龍骨架一樣,一節一節地把它愈合好。慢慢地,才理清其中套鑄、鉚鑄、嵌鑄等工藝。從1990年到1997年,爬上蹲下,七年彈指一揮間。
三星堆,未解之謎還有很多
記者:1997年,三星堆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恢宏詭譎的神樹,以及縱目闊嘴的面具、高鼻大耳的立人、流光溢彩的黃金,這些您和徒弟一起修復的文物,令人嘆為觀止、流連忘返。對您來說,已經修復完成了那么多珍貴的文物,還有什么遺憾嗎?
楊:確切地說,不是遺憾。三星堆的挖掘在繼續,修復和考古也在繼續。比如說,在廣漢的三星堆博物館和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庫房里,其實還存著一些“零碎”的青銅殘片(暫時很難再作復原和進一步研究),沒有足夠的依據,不敢隨便亂動、亂拼接。
其實,哪怕面對我們修好的文物,我們也會時常問——為什么會出土這么多人面青銅器?為什么它們長得如此獨特?它們是如何被鑄造的?那些碩大的青銅器從何而來?這些小而精美的青銅物件又是做什么的?存在于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人是怎樣的一群人?他們從哪兒來?他們是如何生活的?跟出現時期有所重合的中商王朝有什么關聯?三星堆文化到底存在了多久?
記者:隨著新一輪的考古發掘,這些遺留的問題,有望迎來新的突破嗎?
楊:從2019年12月開始,在1號、2號祭祀坑的周圍,現任三星堆考古工作者站站長雷雨和同事們又陸續發現了六個相似的器物坑,四大兩小。發掘工作目前還在進行中,3—8號祭祀坑目前所出土的文物數量和質量,甚至已經超過了之前的。這很讓人欣喜,我也特別期待能在修復領域幫上一點忙。
不過,打開“盲盒”容易,要完整呈現出它的原貌,卻非想象得那般簡單。當年古蜀先民把這些祭祀物品放進坑里后,不僅是回填泥土,而且還層層夯實,這導致文物變形和破碎,至少需要三五年時間才能夠清理完畢,之后又需要很長時間去修復。這個活,我還想一直干下去。因為三星堆值得。
采寫:孫佳音? ?編輯: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