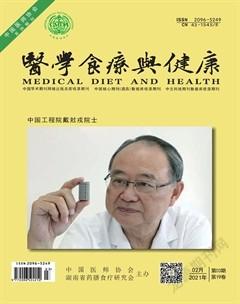即刻種植與常規種植治療牙齒缺失修復中的療效觀察
王輝
【摘要】目的:觀察牙齒缺失修復治療中采用常規種植與即刻種植的效果差異。方法:納入本單位2018年01月至2020年01月間確診牙齒缺失的50例患者作研究樣本,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組,取其中25例為對照組,施行常規種植;另25例為實驗組,施行即刻種植。比較兩組療效、種植體穩定系數(ISQ)、滿意度及不良反應差異。結果:兩組治療成功率(96.00%、92.00%)、術后1~3個月的ISQ評分、不良反應發生率(12.00%、8.00%)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實驗組治療滿意度(100.00%)高于對照組(8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結論:即刻種植治療牙齒缺失,在療效、種植體穩定性、不良反應方面表現與常規種植具有一致性,但即刻種植治療時間更短,患者治療體驗更好,滿意度更高,值得關注。
【關鍵詞】即刻種植;常規種植;牙齒缺失;種植體穩定性;疼痛;不良反應
[中圖分類號]R78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5249(2021)03-0075-03
對于牙齒缺失患者的治療,臨床常采取人工牙種植技術干預,以幫助患者重新修復咀嚼功能,并滿足患者對人體美學的追求。牙齒種植還能夠降低牙槽骨吸收,改善周圍健康牙的工作負擔,清潔方便,穩固性好,受臨床廣泛關注[1]。牙體種植技術經歷數十年的發展,成熟度較高。現階段,臨床對于牙齒種植方面的主流研究方向之一,在于對種植時間的探討。目前較常采用的兩種種植方式有常規種植與即刻種植,臨床報道顯示[2],即刻種植在改善患者治療體驗方面更好,分析這是由于該治療方式耗時相較于常規種植更短所致。為進一步探討兩種種植方式的效果差異,筆者納本單位50例患者作研究樣本,整理數據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納入本單位2018年01月至2020年01月間確診牙齒缺失的50例患者作研究樣本,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組,取其中25例為對照組,男女比例12:13,年齡18~63歲,平均年齡(48.75±6.48)歲,病因:外傷15例、牙周炎7例、其他3例;另25例為實驗組,男女比例13:12,年齡19~65歲,平均年齡(48.99±7.04)歲,病因:外傷16例、牙周炎6例、其他3例。研究報備本院倫理委員會且獲得批準,基線資料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納入標準:牙齒缺失且需要接受種植治療;患牙根尖區未見肉芽腫及炎癥反應;知曉本次研究內容并自愿被納入組,簽署(家屬代簽)同意書;可耐受相應治療者。
排除標準:病灶周圍出現膿性分泌物;骨缺損情況嚴重,無法接受種植;認知障礙或精神類疾病;嚴重全身性感染;妊娠、哺乳期女性。
1.2方法 實驗組實行即刻種植,術前影像學觀察病灶部位情況,評估牙槽骨骨量,局麻常規消毒鋪巾,拔牙注意避免對牙槽骨造成醫源性損傷,成功拔牙后清除牙碎屑及周圍軟組織,牙槽窩經向導鉆進行加深處理,再以擴大鉆由小至大擴大牙床,再次清除周圍碎屑及軟組織后,即刻植入種植體,根據情況合理選用覆蓋螺絲或覆蓋鈦網膜,術畢軟組織縫合處理。給藥羅紅霉素(生產企業:哈藥集團制藥六廠;國藥準字: H19980087)0.15g/d,連續用藥7d;指導患者洗必泰漱口液(生產企業:深圳南粵藥業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20104)規范漱口,15mL/d,連續用藥21d。
對照組實行常規種植,拔牙方法同上,待創口愈合,一般90~180d,于牙槽嵴進行牙體種植,骨融合良好下,一般90~180d,開始后期修復,其他操作同上組。
1.3觀察指標 ①療效:成功:經影像學觀察,種植部位未見透射區,查體確定患者種植牙未見松動異常,隨訪期間患者未主訴神經疾患、感覺異常、疼痛難消、感染等情況發生;失敗:經影像學觀察,種植部位存在透射區,查體確定患者種植牙有一定松動跡象,隨訪期間患者主訴存在神經疾患、感覺異常、疼痛難消、感染等情況發生。成功率=成功例數/總例數×100%[3]。②種植體穩定系數(ISQ):經瑞典哥德堡公司生產的OSSTELL分析儀檢測種植體的穩定性情況,數值越大提示穩定性越好。③滿意度:采用本單位自制的滿意度問卷,統計患者滿意度情況:優:80~100分;可:60~79分;差:0~59分。滿意度=(優+可)/總例數×100%。④不良反應:種植體松動;牙齦紅腫;牙周膿腫。
2 結果
2.1兩組療效比較 實驗組種植成功者24例,成功率96.00%(24/25);對照組種植成功者23例,成功率92.00%(23/25);兩組成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418,P=0.234>0.05)。
2.2兩組ISQ比較 兩組術后1~3個月的ISQ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1。
2.3兩組治療滿意度比較 實驗組治療滿意度(100.00%)高于對照組(8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2。
2.4兩組不良反應比較 實驗組不良反應發生率達12.00%,對照組為8.00%,兩組該指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詳見表3。
3 討論
對于牙齒缺失患者,臨床常采取的治療方式有人工牙體種植技術。根據治療時間的不同,又將人工牙體種植又分為常規種植與即刻種植。前者在臨床應用率較高,但其不足之處同樣存在,即治療周期長,患者多次治療下舒適性欠佳,因此治療有其局限性。而隨著牙齒種植技術的不斷發展,臨床研究發現[4],即刻種植能夠有效改善上述常規種植所暴露出的不足,同時能夠保留常規種植療效,可行性更佳。患者無需經歷牙創愈合、骨融合的時間等待,極大程度縮短了整體治療周期,不僅有效改善患者的治療體驗,同時在經濟性方面亦具備優勢。如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兩組治療成功率、術后1~3個月的ISQ評分、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差異不顯著;但實驗組治療滿意度高于對照組,差異顯著,提示二者整體療效表現相近。
何貴州[5]在其研究中統計得:兩組患者接受種植的第1、3、6個月,ISQ得分均值在61~66分之間,這與本文的統計結果基本一致。與此同時,何還就兩組患者的遠期療效進行了觀察,接受即刻種植的一組,術后1年僅存1例牙齒松動者、0例牙周膿腫;接受常規種植的一組,術后1年出現3例牙齒松動、2例牙周膿腫,統計學分析預后差異,提示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組數據的得出與本文觀點并不一致。思考造成上述差異的原因,或許與患者自護水平有關。
張旭等[6]研究中,接受即刻修復的一組并發癥發生率占比6.25%,較之常規修復(4.17%)略高,但不具備統計學意義,與本文結果相較一致。張旭等在文中總結前人觀點,認為導致即刻修復遠期預后略差于常規修復的原因在于即刻修復無法滿足形成骨整合的條件(術后3~6個月,軟組織需完全覆蓋于植體之上,植體需要徹底埋植于骨內,同時保障植體在愈合期內免受其他外力的干擾)。而即刻種植技術因治療特性,無法滿足上述要求,即刻種植導致植體纖維性愈合,故患者的遠期預后結局略差于傳統種植技術。但從部分臨床文獻[7-9],以及本文的研究結果來看,即刻種植技術的遠期預后并不會與常規種植技術拉開過大差距,往往兩項技術該指標對比,并不具備統計學意義。
相較于常規種植,即刻種植的優勢有以下幾點:①即刻種植,整體療程較短,能夠縮減患者咀嚼功能恢復的時間,降低手術頻次,提升患者治療舒適度;②常規拔牙后即刻采取種植干預,能夠進一步避免牙槽脊吸收,降低骨損失;③拔牙后即刻植牙,更利于植入床的成形;④利于術者手術過程中更好地參照原有牙根,幫助術者更好地決策種植牙位置,使得種植療效更佳,牙齒協調性更好,進一步追求人體美學,有效保持牙槽骨的高度與寬度[10]。
綜上所述,即刻種植治療牙齒缺失,在療效、種植體穩定性、不良反應方面表現與常規種植具有一致性,但即刻種植治療時間更短,患者治療體驗更好,滿意度更高,值得關注。本次研究亦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在于研究時間短,樣本納入量不高,可能導致數據采集客觀性有所欠缺;未來條件允許下,可以適當擴充樣本量,延長研究時間,以更好地統計數據,確保研究客觀性,更好地指導臨床。
參考文獻
[1] 張宏偉, 李春茹. 即刻種植和常規種植在牙齒缺失修復中的臨床價值對比[J]. 黑龍江醫藥科學, 2017, 40(1): 115-116.
[2] 杜進輝, 劉亦涵, 許立, 等. 即刻種植與延遲種植在牙齒缺失修復中的臨床療效觀察[J]. 臨床口腔醫學雜志, 2017, 33(5): 297-300.
[3] 潘勇. 即刻種植和常規種植在牙齒缺失修復中的應用效果對比分析[J]. 當代臨床醫刊, 2017, 30(4): 3267-3268.
[4] 華一峰, 張瑞智, 余波, 等. 牙齒缺失患者行即刻種植牙法與常規種植牙法治療的臨床療效比較研究[J]. 貴州醫藥, 2019, 43(11): 1773-1775.
[5] 何貴州. 即刻種植法和常規種植法對牙齒缺失進行修復的療效對比分析[J]. 中國現代藥物應用, 2015, 9(16): 89-90.
[6] 張旭, 陶庭亮, 張磊, 等. 牙缺失修復不同骨質患者行即刻種植與常規種植臨床比較研究[J]. 北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2017, 18(3): 371-374.
[7] 蔡劍, 唐偉成, 孫麗君, 等. 牙齒缺失患者常規種植和即刻種植修復后療效比較[J]. 中國美容醫學, 2020, 29(5): 127-130.
[8] 謝義璞, 王令軍. 牙齒缺失患者行即刻種植牙法與常規種植牙法治療的臨床效果觀察[J]. 國際醫藥衛生導報, 2020, 26(3): 396-399.
[9] 丁姍姍. 即刻種植與早期種植對前牙種植體周邊軟組織美學效果比較分析[J]. 中國美容醫學, 2019, 28(12): 132-135.
[10] 趙麗娜, 劉鑫, 唐旭炎. 上頜前牙單牙即刻種植術后即刻修復和延期修復的臨床效果比較[J]. 口腔醫學, 2019, 39(9): 799-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