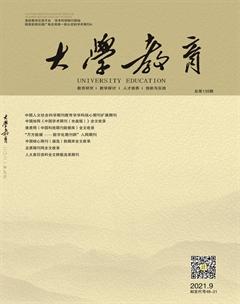“發達資本主義孕育出無階級的幻象”
韓璐
[摘 要]文章從“工人階級消亡論”產生的緣由入手,著重梳理了特里·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對這一觀點的批駁。其批駁是基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新的變化與發展,因此是在現實語境下針對西方學界長期存在的對馬克思主義的誤解的有力批駁與正名,其批駁所切入的方式、論證的路徑以及語言風格都極具特點。文章也對特氏論證中的問題與瑕疵進行了總結與探討。
[關鍵詞]工人階級;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 B0-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21)09-0129-04
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鼓吹“工人階級消亡論”的聲音一直不絕于耳,意圖通過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這一重要范疇來達到否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的目的。“工人階級消亡論”的產生源于當代資本主義的一系列新變化,尤其是由產業結構和生產模式調整帶來的勞動者結構的變化,使很多西方學者得出“各階級的流動性越來越大”“社會的包容性在持續增大”的結論,進而批判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已經不合時宜,不能用于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問題。
一、“工人階級消亡論”產生的主要根源
其一,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的數量在不斷減少。隨著科技革命的不斷深入,西方發達國家正在從自動化的工業3.0時代邁入到智能化的工業4.0時代。產業結構與生產組織方式的變化帶來了工人群體結構的變化,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工人數量正在不斷減少,而服務、管理、信息等崗位的從業人員數量不斷攀升。這就使得某些西方學者單純從表象出發,得出“馬克思主義所定義的為資本主義機器化大生產過程而服務的工人階級的概念在現代化語境下已然失效”的結論。
其二,舊式的企業等級結構讓位于相對松散的組織形式。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以“泰勒制”和“福特制”為代表的勞動組織形式,極大地提高了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保證了資本家的收益,但也激化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伴隨著工人運動的不斷高漲,資本家被迫作出讓步以緩和勞資關系。過去等級森嚴的“完全掌控式”管理模式,逐步讓位于更為松散的、形式上更為平等的、以團隊為導向的組織形式。企業的員工與管理者之間的關系似乎更為友好,諸如可以直呼其名、表達建議等。因此很多西方學者據此得出結論,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以及階級對立已然成為歷史,用階級概念來繼續分析資本主義的現實問題就像“談論在火刑柱上燒死異教徒那樣不合時宜”。
其三,“消除偏見”的努力帶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包容度在表象上的加大。消除差異和偏見、追求權利平等是西方政界、學界與社會公眾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中經常就文化、種族、性別等方面的權利平等問題展開激烈討論,并不斷采取措施來消除差異與偏見。因而很多西方學者認為,這種差異化的削弱和對于弱勢群體的關注,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包容度在不斷加大,繼而必然會消解馬克思主義曾指出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而實際上這種避重就輕的論調完全無視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最本質的不公正與差異化,即剝削現象的長期存在。因而所謂的社會包容度加大,只是資本家用于緩和社會矛盾、掩蓋社會不公正現象的偽飾而已。
針對“工人階級消亡論”,國內外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從邏輯、現實等多種角度進行了批駁,其中就包括英國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馬克思主義者特里·伊格爾頓。他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針對西方世界存在的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誤讀與偏見一一進行了批駁,在構思和寫作方式上致敬了同樣非常喜歡論戰的馬克思。特里·伊格爾頓在這部著作中用不少篇幅專門批駁了“工人階級消亡論”,其著眼于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現實,用生動的案例與幽默的筆觸論證了“工人階級消亡論”的荒謬與淺薄。
二、特里·伊格爾頓對“工人階級消亡論”的批駁
在《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特里·伊格爾頓對“工人階級消亡論”的批判主要從概念、現實和歷史角色三個維度展開。
首先,從概念層面上,特里·伊格爾頓將階級明確界定為“一個關于你在某一特定生產模式中所處位置的問題”,以此與“消亡論者”認為階級主要是態度和感覺問題的論調區別開來。某些差異的削弱,會使人“感覺”到不同階級間溝壑的彌合,但并不能改變特定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中的角色和位置,而后者無疑才是界定階級的基本依據。同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所出現的勞動者結構以及企業組織形式的變化,只能說明階級的構成發生了改變,但并不能說明階級已經消失。把“改變”混淆成“消亡”,無疑是一種別有用心的障眼法。
特里·伊格爾頓還以反諷的筆法指出“消亡論者”所鼓吹的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中正在發生的“公正化”和“階級調和”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即資本主義制度在對所有無產階級都進行了公正、無差別的剝削的角度體現出了無可挑剔的“平均主義”。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決定了其實現資本增值、財富擴張的方式必須建立在少部分人對大多數人實行剝削的基礎上,這一內在的發展邏輯不會因社會發展而改變,不會因“消除差異”的努力而削減。而恰恰是因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其真實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被層層掩蓋,才使得很多人產生階級已經消亡的錯覺。
其次,從現實層面上,特里·伊格爾頓犀利地指出無產階級這一群體不僅不會消亡,其實際規模遠超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不可否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無產階級隊伍的構成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工人的數量明顯下降,與此同時,從事技術、行政及管理工作的受雇傭者的人數急劇增長。如前所述,特里·伊格爾頓已闡明“階級”不是一個抽象的、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一個現實的“利用自己控制他人的權力為自己謀利的能力問題”。產業工人數量的下降是信息技術革命被廣泛應用于生產領域、產業結構調整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即從更少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更多的財富,使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因此,這一變化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論斷的準確性。同時,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使大量傳統意義上的專業人士、中產階級等群體受到失業、破產等問題的困擾,成為“無產階級化”的潛在人群。比如2018年全球失業人口為1億7200萬人,失業率為5%,而在受雇傭的人群中,仍有7億勞動者陷于貧困困境當中。2020年,在疫情影響下,美國的失業人口已達到了創紀錄的2200萬人,這個數字還在持續增長中。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雖然不能絕對化地將所有受雇于他人、領取薪水的個體都歸于無產階級之列,但在這一群體中無法控制自身勞動、飽受失業威脅、收入與勞動投入不成比例的均應被納入到無產階級這一階層中。以此為標準進行考量,無產階級的數量將是非常龐大的。
同時,特里·伊格爾頓還特別指出,在探討無產階級這一群體時,不應忽略目前世界中存在的龐大的貧民窟人口。這一群體也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或雇傭勞動者,但現實中他們并未被排斥在生產過程之外,而是“在生產過程的內外之間來回漂移”。由于這一群體往往處于赤貧狀態,因此他們通常只能從事一些工資最低、無須培訓、工作環境最差的臨時性工作,他們所受到的盤剝程度也是極高的。據聯合國下屬的國際勞工組織統計,截至2018年全球有20億就業人口屬于非正式雇用,占全球勞工比例高達61%。從貧民窟勞工群體在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在生產模式中所處的地位,特里·伊格爾頓認為將其歸于工人階級群體是完全合理的,并且他在書中對于這一群體的處境表達了格外的關切與悲憫。他將貧民窟勞工群體的生存現狀與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所描述的現象相類比,指出實則二者的處境沒有本質上的差異。而正因為如此,貧民窟中受到盤剝、飽受貧困之苦的人們理應被視為無產階級的一員,他們將為改變自身的悲慘處境以及爭取平等與解放而組織和行動起來。
再次,從歷史角色的層面上,特里·伊格爾頓斷言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賦予這個世界的“強大禮物”。他將工人階級稱為“不是階級的階級”,原因在于工人階級這一群體的存在對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而言是必要條件之一,但當談及權利、成果的分配與共享等問題時,工人階級又被排斥在外,“既發揮了作用又一無所有”,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存在狀態的精準描述。
這一自相矛盾的生存狀態,恰恰說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內在問題,這種不公正、不協調的生產模式和社會階級關系也預示著資本主義社會走向衰落和滅亡的必然命運。而推動這一歷史進程的主導力量,正是被資本主義社會極力排斥在外的工人階級。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言,工人階級想要被正常納入社會秩序中,使其人性化的一面得以被承認,而不是僅被當作進行生產的工具,就必須對現有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重建,即成為舊的制度的“掘墓人”。工人階級的這一歷史角色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語境下并未發生改變。
同時,特里·伊格爾頓糾正了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僅是專注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激烈批判而無視資本主義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的常見誤解。他首先指出馬克思本人在著作中曾多次高度評價了資產階級所取得的成就,這些成就正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而馬克思對于資本主義的種種批判,實際上是一種審慎而理性的描述,畢竟熱情地贊揚或是尖銳地譴責都不是理性的態度。而資本主義社會賦予這個世界最強大的禮物之一就是孕育出了工人階級,其代表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趨勢。
關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觀的另一常見誤解是,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將資本主義社會“臉譜化”地劃分為工人階級和“邪惡的資本家陰謀集團”,而隨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資本家在社會生產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因而很多人借此來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觀的正確性。特里·伊格爾頓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層劃分中居于最高層的雖然不盡然都是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家,但卻都可以歸類于“資本的代理人”;馬克思主義者并不排斥和反對這個群體投身于無產階級運動的陣營,但由于這群人所擁有的社會地位與財富,他們會更傾向于認同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并且很有可能采取各種措施來鞏固既得利益。可見,并非是由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劃分而使資本主義社會呈現出兩大階級對立的狀況,也并非是由于無產階級對于資產階級的主觀敵意而產生階級矛盾。工人階級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孕育出來的,并因被排斥于社會之外而必須走上推翻舊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之路。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的那樣,歷史選擇了工人階級并非是由于“勞動者身上具有某種燦爛的美德”,而是由工人階級所處的社會地位所決定的。
特里·伊格爾頓通過針鋒相對的駁斥,闡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與資本家這兩大階級的地位、角色并未發生本質改變,而要改變這種“異化”的狀態,憑借單純地否定階級的存在是無效的,恰恰要通過階級來戰勝階級,通過階級來消亡階級。
三、特里·伊格爾頓對“工人階級消亡論”的批駁的理論與現實價值
首先,這是在當代資本主義語境下對階級問題的有益探討。特里·伊格爾頓基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階級構成、企業組織機制等方面的變化,對工人階級這一特定群體的現實存在狀態和社會地位進行了深入探討,架空了“無產階級消亡論”者建立觀點的基礎,即當代資本主義已區別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所描述的時代,因而打破了消亡論者試圖證偽馬克思主義階級范疇的幻想,從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與開放性,是在當代資本主義語境下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積極嘗試。
其次,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長期存在的誤解的有力批駁與正名。在西方學界及公眾中長期存在一些假馬克思主義之名的錯誤觀點與論調,試圖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污名化,引發了對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的嚴重誤解乃至敵意。特里·伊格爾頓以論戰的形式,針鋒相對地逐一駁斥了這些觀點,為馬克思主義正名,還大眾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原貌,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當代價值。這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在西方世界的廣泛傳播并持續擴大影響力無疑是很有助益的。
再次,這體現了對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底層人民生存狀況的憂慮。資本主義社會“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內在邏輯使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貧富差距不斷增大,造成了當前最為嚴重的世界性問題——貧困問題。在特里·伊格爾頓關于工人階級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感到他對貧困人群的深切同情與憂慮。尤其是他對不斷擴張中的貧民窟人口的關注,打破了資產階級所編織的階級鴻溝逐漸消失的謊言,讓我們看到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剝削與壓迫的丑陋真相。同時,特里·伊格爾頓的論述也使對貧困問題的關注從現象層面深入到制度層面,由感性的同情與悲憫發展為理性的分析與批判,為資本主義世界中財富分配的不公正找到根源,并給出解決方案,即必須依靠工人階級組織和行動起來,在自我拯救的同時解放全人類。這種對于底層人民的關切與憂慮,體現出了作為一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特里·伊格爾頓的情懷,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即人民立場的體現。
最后,這是對資本主義世界當前階級調和、美化等做法本質的揭露。為了避免階級矛盾的激化,資產階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和矛盾、掩蓋剝削,并試圖通過轉移公眾的關注點,模糊階級矛盾與非階級矛盾的界限。通過偷換概念,使大眾轉而討論文化、身份認同、種族、性別等問題,試圖用這種手段來消解對階級問題的探討。特里·伊格爾頓的批駁打碎了這些偽飾,使我們看到文化、種族等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必然與階級問題交織在一起,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而階級現象是資本主義社會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前提,無法將階級分化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剝離開來。而資產階級不斷否定工人階級這一群體的現實存在、對階級問題諱莫如深,恰恰說明這一問題是其不能回避的,也是解答其財富來源的關鍵問題。特里·伊格爾頓的駁斥使資產階級調和階級矛盾、縮小階級差異的“作秀”的虛偽性表露無遺,也使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邏輯從未發生改變。
四、特里·伊格爾頓關于“工人階級消亡論”的論述值得商榷的兩個問題
首先,重在反駁,欠缺更為深入的實踐思考。特里·伊格爾頓集中力量對“工人階級消亡論”的常見論調進行了一一駁斥,重在“破”,而“立”的方面則略顯不足。雖然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進行了界定,也講明了為何必須由無產階級承擔起推翻舊的社會制度的任務,但其論述還主要停留在現象枚舉和描述的層面,回答了“是什么”和“為什么”兩個層面的問題,但缺乏對于“怎么做”即實踐層面的關照與深入。如能針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工人運動的趨勢與策略進行梳理與展開,則會使對本問題的談論更加完整,增強其觀點的實際效用。
其次,欠缺基于哲學史縱向發展維度的視角。特里·伊格爾頓關于“階級”概念的探討在語言風格上是較為生動的,因此也較為通俗易懂,這對于面向大眾廣泛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無疑是非常有助益的。但由于沒有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的視角對“階級”概念的內涵進行系統化的梳理,其闡述略顯零亂,不能讓人窺得馬克思主義中階級范疇的全貌,也容易引起對階級概念的一些新的誤解,這不得不說是這部著作的遺憾之處。
在特里·伊格爾頓的《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是對的》一書中仍存在一些瑕疵,有的人將其歸因于作者文學評論家的身份,意指其慣用的話語方式與哲學探討存在差異,但我們換個角度看,這種差異也可稱為特色。特里·伊格爾頓以其生動、犀利的語言風格,有力批駁了當代西方世界中盛行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歪曲性認知,并因其著作的淺顯易懂,起到了在更廣大的群體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現實影響力與說服力的效果。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主義為什么是對的》一書的現實意義較之其理論意義更大、影響更深遠。我們有理由相信,在這部風格獨特、內容精煉的著作的影響下,有更多的當代西方學者乃至普通讀者開始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走近馬克思主義,最終樹立和堅定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走上無產階級革命之路,因為,馬克思是對的。
[ 參 考 文 獻 ]
[1] 特里·伊格爾頓. 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M]. 重慶: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17:110-195.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1-498.
[3] 邁克·戴維斯. 布滿貧民窟的星球[M].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7:91-250.
[4] 楊柳夏,許斗斗. 工人階級消亡了嗎?[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6):103-110.
[責任編輯:龐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