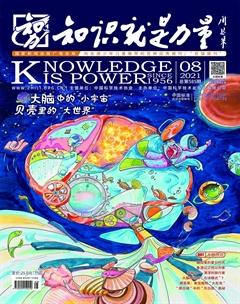讓死去的動物“活”過來
非遺中的科學
從渺小的螞蟻到巨大的鯨,想留住動物世界的千姿百態,就需要標本制作師通過不同類型的標本,盡量留住每一種動物生前的樣貌。可以說,每一類動物標本的制作,都是工藝與科學的完美結合。中國標本制作傳統技藝素有“南唐北劉”之譽,為了探尋標本制背后的科學內涵,知力記者走進清黎閣北劉動物標本制作處,和非遺傳承人聊聊標本制作技藝的故事。
北劉動物標本制作技藝創始人劉樹芳為清代宮廷所做的動物標本(供圖/劉嘉暉)
北劉動物標本制作技藝第二代傳承人劉汝淮、劉汝英為國家領導人制作的小青馬標本,現為國家一級文物,保存于延安革命紀念館(供圖/劉嘉暉)
動物標本制作的“花花世界”
大家每每去到博物館,總是被博物館里大大小小的標本所吸引。其實,標本可分為五大類:泡在“水”里的浸制標本(如魚類、蛙類、烏賊、海參等);“巧奪天工”的干制標本;制作哺乳類、鳥類、爬行類和大型魚類標本常用的剝制標本;沒有“肉”的骨骼標本和玻片標本。這便組成了豐富多樣的標本“花花世界”。
浸制標本:讓動物“活”在瓶中
對于水生動物來說,由于它們的柔軟身軀在干燥狀態下不易保存,因此只能泡在“水”中。但是,此水不是真的飲用水,而是由防腐殺菌的酒精或甲醛的水溶液(即“福爾馬林”)制成浸制標本。
浸制標本的歷史悠久,古代就曾利用烈酒中的高濃度酒精充當臨時防腐劑。而酒精的防腐原理和后來問世的福爾馬林類似,都是破壞肌體中的蛋白質,殺死細菌。盡管裝在玻璃瓶里的福爾馬林容易讓標本褪色,還會發出刺鼻的氣味,但是如果想要完整地保存柔軟的動物遺體、內臟器官,浸制標本仍然是不二之選。
泡在高濃度防腐劑里的浸制標本,不會受到細菌的破壞,可以長久保存
昆蟲標本屬于干制標本,又叫針插標本
由動物標本制作技師劉樹芳制作的亞洲象標本,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巨型剝制標本,現存于北京自然博物館(供圖/劉嘉暉)
慢工出細活的干制標本
對于昆蟲來說,最適合它們的標本制作方式莫過于干制標本了。昆蟲標本屬于干制標本,又叫針插標本。先用化學藥劑快速殺死昆蟲,然后用細針慢慢地穿透昆蟲身體,再釘在底板上固定,之后烘干或者風干即可。由于昆蟲體型小,少量體液在干燥過程中就蒸發掉了,只剩下那些不易腐爛的組織。對于有著細小翅膀及觸角的昆蟲來說,在制作中就需要用細針來固定,從而保持相對自然的狀態。
“脫胎換骨”的剝制標本
對于最有沖擊力的剝制標本,制作技藝就要相對復雜,既需要了解動物的解剖學特征和生活習性,還需要有高超的手工技巧和藝術修養。剝制標本的實質就是要將動物尸體內的肌肉、骨骼、內臟和皮下脂肪等完全掏空,只留下體表的皮毛、鱗片和犄角,再整形成生前的樣子,可謂是除了留有表皮外徹底地“脫胎換骨”。
在現代的剝制標本工藝中,動物遺體毛皮經過鞣制(使生皮變成革的物理化學過程),轉化為柔韌有彈性的熟皮,能長久保持鮮活。內部則用樹脂、石膏或玻璃鋼等材料,制成尺寸貼合動物身形的整塊“假體”,再套上皮毛,便呈現出了逼真的肌體層次,而且不易走形。標本的眼睛,也從玻璃球換成根據標本形態專門定制的假眼,使之更加炯炯有神。
動物標本與化石標本
和化石標本相比,動物標本更具有直觀性和沖擊力,因為它不需要后期借助科技還原其原貌,它本來就是一個真實存在的實體,保留了它生前的所有特征。制作標本主要是為保存動物的生物學基本數據,包括外形輪廓、解剖學結構、分類標志、自然生活狀態等各種要素和信息。這些信息為動物學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最為直接的實物依據。
動物標本是一件藝術品,只有通過展示才能喚起更多人對自然的珍惜。死去的動物不會說話,但動物“復活”后,卻能告訴人類,要好好保護其他活著的動物。這是一種微弱又巨大的聲音。
(責任編輯/陳天昊 美術編輯/周游)
北劉動物標本制作第四代傳承人劉嘉暉在制作雪豹標本,北劉動物標本制作技藝入選為北京市第四批市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供圖/劉嘉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