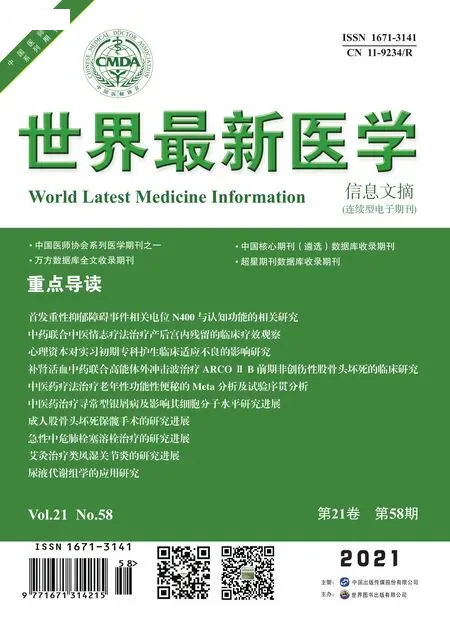自發性孤立性腸系膜上動脈夾層診療進展
王垚柯,趙渝,李鳳賀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血管外科,重慶 400000)
0 引言
自發性孤立性腸系膜上動脈夾層(Spontaneous isolated 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issection,SISMAD)是一種罕見的血管疾病,在一項對6666具尸體進行的尸檢報告中該病發生率為0.06%[1]。自Bauersfeld在1947年首次報導SISMAD病例以來[2],過去幾十年僅有少量的病例報告。近年來,隨著計算機斷層掃描(Computed tomography,CT)在腹痛患者中的廣泛應用,尤其是高質量CTA的普及,SISMAD病例數較前大大增加,相關文獻報道也越來越多,其中大多數來源于中國、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3],但發病率是否與人種、環境、氣候及生活習慣等有關尚無研究證據支持。由于SMAD可因夾層動脈瘤破裂出血或SMA堵塞引起腸缺血、腸壞死等致患者死亡,在臨床上受到醫生的關注與重視。然而,SISMAD的病因及自然病程尚不清楚,最佳治療方案的選擇也未達成共識。
1 病因
SISMAD的病因目前尚不明確,部分研究者認為與動脈壁病理變化有關,包括動脈中層囊性壞死、血管平滑肌細胞發育不良、外膜炎癥、中膜彈性層破裂、穿透性動脈潰瘍、假性動脈瘤和動脈瘤等[4,5]。也有研究者認為結締組織病(如馬凡綜合征、Ehlers-Danlos綜合征等)是SISMAD發生的可能原因[6,7],但在大多數報告中沒有確定SISMAD的具體潛在原因,此外,不容易將這些結締組織病與夾層發生后的繼發性變化區分開來。
有研究者[5]提出SISMAD的發生可能與腸系膜上動脈的解剖學特點及血流動力學有關。腸系膜上動脈是腹主動脈第二個主要分支,自腹主動脈發出后在胰腺后方下行,位置相對固定,之后跨過胰腺鉤突的前方進入小腸系膜根部,此段位相對活動,在移行區存在異常剪切力,可能是導致腸系膜上動脈夾層的原因。Park等[8]測量了SISMAD患者胰腺下緣和SMAD入口之間的距離,平均距離是11.2mm±9.61mm,發現SMAD總是從SMA的彎曲段周圍開始。Park等[8]還建立了SMA不同彎曲度的模型(60°、90°、120°),應用計算機流體力學對SMA開口及彎曲段的血流流場及動脈壁剪切應力進行分析,認為在SMA的特定部位發生的異常血流動力學變化是SISMAD發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腸系膜上動脈與腹主動脈存在一定的角度,KIM等[9]測量了三組研究人群(韓國SISMAD患者、韓國人和白種人患者的體檢數據庫)的腹主動脈腸系膜上動脈夾角(aortomesenteric angle,AMA),發現SISMAD患者的AMA比正常韓國人、白種人的AMA更大(75.7°±17.5°vs.56.0°±19.6°vs.62.6°±19.2°,P<0.001),認為較大的AMA是SISMAD的一個重要病因。吳等[10]人的一項研究也發現SISMAD患者具有比正常人更大的AMA(73°±19.8°vs.50°±18.81°,P<0.001),并且進一步進行力學研究證實,較大的夾角與SMA彎曲段動脈壁較高的應力和血管腔內較高的振蕩剪切指數有關,彎曲段也正是夾層通常發生的地方。
2 臨床表現
SISMAD好發于50多歲的中老年男性,其臨床表現多種多樣,臨床上以癥狀性SISMAD多見,但缺乏特異性,亦有隱匿發病的無癥狀患者,在影像學檢查中偶然發現。在幾篇系統性回顧報道[3,11-14]中,男性SISMAD患者占80.6%-88.5%,癥狀性SISMAD占83.4%-93.3%,其中腹痛是最常見的癥狀,多為持續性腹痛伴陣發性加重,部分患者可能伴有腰背部放射痛或表現為隱痛。Cho等[15]認為腸系膜上動脈狹窄與SISMAD患者的臨床癥狀有關,提示腹痛可能是由于內臟缺血引起,而Park等[16]認為腹痛原因來源于腸系膜上動脈夾層及血腫本身,動脈夾層周圍的炎癥刺激內臟神經叢而導致疼痛。除腹痛外,其他癥狀包括惡心嘔吐、腹脹、腹瀉、血便、厭食、便秘、體重下降、發熱、多汗、胸骨后疼痛等[13]。部分患者可出現持續超過一個月的慢性癥狀,包括惡心、嘔吐、腹瀉、黑便、餐后疼痛和體重減輕,提示SMAD可能有亞急性或慢性病程[14]。在體征方面,發病早期可能無明顯腹部體征或腹部體征較輕,表現為“癥狀體征分離”,嚴重者可能因不同程度的腸壞死表現出腹部壓痛、反跳痛及肌緊張等腹膜刺激征。
3 診斷
SISMAD患者常因突發腹痛于急診或基層醫院就診,且其臨床表現和體征缺乏特異性,容易漏診或誤診。有學者建議,在適當的臨床環境中應考慮對每個有2-3h以上不明原因腹痛病史的患者進行急性腸系膜缺血的診斷性檢查[14];對于頑固性上腹痛和血壓升高、且腹痛與查體和實驗室檢查相對不符的患者應懷疑SMAD[17]。
目前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被認為是診斷SMAD的金標準,可以清楚的顯示夾層的位置、累及范圍、血管管腔通暢情況及分支血供等,但因為其屬于有創操作,并未作為首選的診斷方法,而在血管腔內介入治療方面更有價值[5,14,18-20]。臨床上約95%的ISMAD患者依靠CT診斷[13],尤其是增強CT,可以見到特征性的“雙腔征”,可以顯示夾層的破口、真假腔直徑、真假腔有無血栓、遠端血供及是否合并其他動脈夾層等,也有助于判斷有無腸道缺血/壞死。彩色多普勒超聲(Color Doppler Sonography,CDS)可根據SMA內真假腔及撕裂的內膜片等征象診斷SMAD。BAO等[21]發現CDS和CT血管造影(CTA)在測量最小內徑、橫截面積、直徑和狹窄面積率以及真腔流速等方面無顯著性差異,CDS可能是診斷SISMAD的一種有效手段,并且具有更高效、更無創、更經濟等優點。但是腸道蠕動、腸道積氣、檢查者經驗等會影響CDS成像效果,故其在診斷SISMAD方面存在局限性。實驗室檢查和腹部X線在本病的診斷中尚無明確作用。
4 分型
目前尚無針對SISMAD的病程發展進行分期的文獻報道,臨床上根據增強CT或者DSA進行影像學分型。2007年Sakamoto等[22]根據假腔的影像學表現首次對SISMAD進行影像學分型,將其分為4型(圖1):Ⅰ型,假腔血流通暢,既有入口又有出口;Ⅱ型,“死胡同”形假腔,有入口無出口;Ⅲ型,假腔內血栓形成,伴潰瘍樣突起(真腔突出到血栓形成的假腔中形成的局部充血囊);Ⅳ型,假腔內完全血栓形成,不伴潰瘍樣突起。但是此方法未考慮真腔血栓形成或狹窄等情況,2009年YUN等[18]提出新的分型(圖2):Ⅰ型,真假腔均通暢,有入口和出口;Ⅱa型,真腔通暢,假腔有入口無出口,呈囊袋狀;Ⅱb型,真腔通暢,假腔內血栓形成;Ⅲ型,真假腔均閉塞。2010年,Zerbib等[23]在Sakamoto分型的基礎上補充了另外兩種分型:Ⅴ型,假腔內部分血栓形成,腸系膜上動脈近端動脈瘤樣擴張、遠端狹窄;Ⅳ型,腸系膜上動脈部分或完全血栓形成。以上分型均是以SMAD真假腔情況作為依據,未考慮夾層長度,但是SISMAD患者的臨床癥狀與夾層長度和真腔狹窄程度有關[18,24]。2013年Luan等[20]根據夾層的位置及長度提出一種新的分型方式:A型,夾層位于SMA彎曲部分并向近端延伸;B型,夾層僅限于SMA彎曲部分;C型,夾層位于SMA彎曲部分并向遠端延伸,但未累及回結腸動脈或遠端回腸動脈;D型,夾層位于SMA彎曲部分并向遠端延伸,累及回結腸動脈或遠端回腸動脈。目前,YUN分型因其簡單、全面,在臨床上應用較廣泛。然而,盡管很多分型方法被提出,但是分型的目的并不是為了更全面的囊括所有SMAD類型,而是協助臨床醫療決策,臨床上何種分型方式更適用尚未確定。

圖1 Sakamoto分型[22]

圖2 YUN分型[18]
5 治療
SISMAD的治療目的是緩解癥狀,預防腸缺血或腸系膜上動脈破裂,目前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包括保守治療、血管腔內介入治療和開放手術治療。歐洲血管外科學會臨床實踐指南[25]推薦:無癥狀患者不需要立即干預,可以通過抗血小板治療和控制高血壓進行保守治療;有癥狀患者最初可以進行保守治療,應該考慮給予抗血小板藥物或肝素以預防受累動脈血栓形成;當保守治療無效且懷疑腸缺血時,應行血管腔內治療或開放手術。然而,最佳治療策略仍未達成共識。
5.1 保守治療
保守治療是最常見的初始治療方案,治療方式主要包括抗血栓治療、控制血壓、腸道休息、抑制胃酸分泌、鎮痛及營養支持等。Park等[16]分析了46例接受保守治療的患者6.5-74.2個月的隨訪結果,CTA顯示41.3%的患者假腔縮小,23.9%的患者夾層長度變短,43.5%的患者無變化;15.2%的患者夾層完全重塑,沒有患者出現夾層進展;隨訪期間26%的患者出現輕度腹部不適,但無復發性腹痛,無SISMAD相關死亡率。Heo等[26]對83名有癥狀的SISMAD患者予以保守治療,96%的患者腹痛緩解,4%的患者出現長時間的腹痛,包括一名患者腸道壞死;在長期(1-173)個月隨訪中,CTA顯示34%的患者無變化,63%的患者有部分或完全重塑,2%的患者有動脈瘤樣改變,1%的患者夾層進展。多項研究[7,12,27-30]顯示SISMAD具有相對良好的病程,保守治療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說是安全有效的,但仍需密切的監測及隨訪。
抗血栓治療的目的是預防SMA血栓形成以及潛在的遠端栓塞[12],盡管臨床上30%和57%的患者分別接受了抗血小板治療及抗凝治療[3],然而其有效性及必要性仍存在爭議。Kim等[31]對29名SISMAD患者予以不使用抗血栓藥物的保守治療,26名患者保守治療成功,在(13-129)個月的隨訪中,27名患者CT掃描顯示夾層改善或完全消失,無癥狀復發。在初次CT掃描中沒有腸缺血或梗死證據的患者中,不使用抗血栓治療的保守治療可能就足夠了[31]。此外,在一些大樣本研究及系統性回顧[26,32,33]中,抗血栓治療與單純的保守治療在癥狀緩解率、動脈重塑率等方面未發現明顯差異。考慮到夾層動脈瘤破裂可能引起致死性出血以及抗血栓形成藥物相關出血風險,抗血栓治療的使用需充分權衡利弊。
5.2 腔內介入治療
2000年Leung等[34]首次報道了對SISMAD患者予以腔內治療,此后,腔內治療SISMAD的報道日漸增多。腔內治療最常見的措施是支架置入,亦有溶栓、彈簧圈栓塞、球囊血管成形等方式[14]。腔內治療SISMAD的優勢在于可以早期、有效的恢復腸系膜上動脈血運,快速緩解臨床癥狀,并且創傷小、術后恢復快,這使得腔內治療已成為除保守治療外的首選治療策略。有研究顯示[35],相對于保守治療,腔內治療的患者癥狀復發率更低,完全重塑率更高,腔內治療具有更好的長期預后,可能是癥狀性SISMAD患者合適的一線治療方案。一些學者[5,36-38]提出了SISMAD腔內治療的適應證,包括:腹痛持續時間超過7天;有急性腸缺血跡象;腸系膜上動脈真腔受壓>80%或腸系膜上動脈夾層動脈瘤直徑>2.0cm;保守治療失敗。
腔內治療的爭論點主要是植入支架的選擇。由于SMA細長,且夾層常發生于彎曲段,因此臨床上使用較多的是柔順性好的自膨式裸支架,可以使內膜貼壁,封閉夾層破口或減少假腔血流灌注使假腔內形成血栓,同時維持真腔通暢并且不影響分支的血供。Wen等[39]對12名接受覆膜支架植入的SISMAD患者進行了16-36個月的隨訪,顯示了較好的短期療效;覆膜支架可以更好的封閉夾層破口,可能是一種安全有效的選擇,但是覆膜支架相對較硬,且有可能封堵SMA的分支血管引起腸缺血,因此臨床上未作為首選。近年來,多層支架被用于動脈瘤的治療,它通過降低瘤腔內的平均流速和湍流,導致動脈瘤囊內血栓形成,而被覆蓋的側枝和分支仍是開放的[40,41]。然而在中國,多層支架尚未推出,有研究者[40]運用多層重疊裸支架來替代并取得了類似的效果。目前許多研究[39,42-45]顯示腔內治療具有良好的療效及中期通暢率,然而支架狹窄、支架內血栓形成等并發癥時有發生,因此支架植入的患者需長期或終生服用抗血栓形成藥物并且規律隨訪。Hang等[46]對支架遠端狹窄的原因進行了分析,發現支架與血管直徑比和遠端邊緣的角度是支架置入術后支架遠端邊緣狹窄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他們認為錐形支架更適合放置在腸系膜動脈中,支架尺寸約等于近端正常參考直徑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而不是超過參考直徑的10%。
5.3 手術治療
開放手術治療SISMAD的術式較多,如肝右動脈轉流術、腹腔干轉流術、主動脈-腸系膜上動脈搭橋等旁路手術,以及補片血管成形術、內膜切除術、血栓切除術等,部分患者因腸壞死行腸切除術、空腸造口術、小腸移植術等[7,29,47-49]。近年來,隨著腔內介入技術的發展,開放手術治療創傷大、技術要求高、風險高、并發癥多等缺點逐漸明顯,臨床上開放手術的應用逐漸減少。但是開放手術療效確切,仍是一種不可忽略的治療策略,目前主要用于出現腹膜炎體征考慮腸壞死的患者、夾層動脈瘤破裂出血的患者以及保守治療和腔內治療失敗的患者。
6 小結
SISMAD是一種罕見的血管疾病,也是腹痛的罕見原因。本病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腸系膜上動脈的解剖學特點和血流動力學改變可能是本病發展的重要原因。本病缺乏特異性的臨床表現,診斷主要依靠CT等影像學手段。大多數SISMAD患者表現出良性臨床病程,但仍可能因腸壞死或動脈破裂等導致患者死亡,臨床醫生應予以重視。保守治療和腔內治療的有效性、安全性得到研究證實,但是最佳初始治療方案的選擇仍存在爭議。對于腸壞死或動脈破裂等患者,應選擇開放手術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