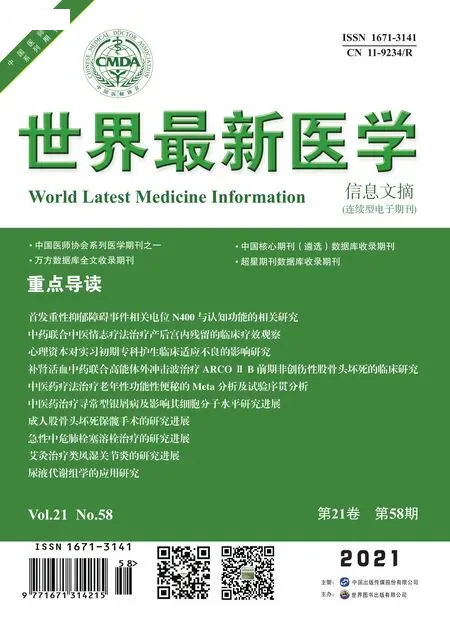淺談卒中相關性肺炎
王媛,徐士欣
(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天津 300193)
0 引言
卒中后急性期感染是常見的并發癥,占總發病率的30%,肺炎和尿路感染最常見,分別占約10%[1]。卒中后的感染會使疾病復雜化,從而延誤疾病的恢復,導致不良的功能預后甚至死亡[2-4]。腦卒中后的并發癥SAP不是簡單的癥狀疊加,其高度復雜的發展過程與腦卒中密切相關。SAP的概念最早在2003年由德國Hilker等人提出,為臨床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5];2010年我國專家制定了《卒中相關性肺炎診治中國專家共識》,規范了國內SAP臨床診療等相關事項[6];2015年Smith等歐洲專家共識進一步闡述了SAP的定義和診斷[7];2019年中國專家更新了國內的共識,增加SAP預測模型及中醫治療等內容[8];同年,Smith等專家關于卒中并發肺炎的抗生素治療提供了新的認識[9]。SAP被定義為非機械通氣的卒中患者在發病7d內新出現的肺炎[7]。SAP在卒中單元的發生率為3.9%-44%,在混合和卒中單元的短期死亡率增加10.1%~37.3%[10]。及時準確地評估卒中患者的病情程度對指導臨床治療尤為重要。
1 卒中相關性肺炎的危險因素
肺炎是由細菌,真菌和病毒引起的肺組織感染。患病的肺泡中有液體,微生物和炎性細胞[11,12]。SAP的機制很復雜。除感染外,其他與SAP相關的危險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吸煙,中風嚴重程度,中風類型,病變部位,意識水平,吞咽障礙,心房顫動,高血壓,慢性呼吸道疾病,糖尿病,中風誘發的免疫抑制等[13-16]。
1.1 吞咽困難
中風后吞咽困難被認為是SAP中必不可少的危險因素[17]。患有吞咽困難的中風患者容易誤將胃內容物和口咽分泌物吸入肺部,從而誘發肺炎[18]。這些患者出現SAP的風險約增加了3倍,并且危重卒中患者發生SAP的風險約放大到了11倍[19]。一些報告證明早期有效的吞咽困難評估有助于降低中風患者罹患SAP的可能性[20,21]。但是,有些研究得出卒中嚴重程度而非吞咽困難或吞咽困難篩查有助于卒中后肺炎的預測[22]。出現這種情況可能的原因是,除吞咽困難外,中風嚴重程度、中風后免疫抑制和其他疾病等也會影響中風后肺炎的發生和結局[13,23]。因此,為了改善急性中風的預后,除了進行吞咽困難篩查及選擇最合適的護理方法和飲食措施外,我們還應進一步關注SAP的其他危險因素。
1.2 免疫抑制
SAP的發生和發展與卒中后免疫抑制密切相關[13]。在急性中風期間,腦細胞的死亡會誘導中樞神經系統中炎性介質的產生和釋放,誘發腦的局部免疫反應[24]。血腦屏障的功能破壞導致周圍免疫細胞可以通過破裂的屏障募集到患處[25]。然而,抗炎反應并不是總對腦損傷部位有益[26]。過度的免疫反應會加劇腦損傷程度并增大梗死面積[27]。為了防止中樞神經系統的局部免疫反應引起腦細胞的進一步凋亡或壞死,自主神經系統通過過度激活來誘導人體全身性免疫抑制的出現[28,29]。外周免疫抑制影響了機體殺菌的正常功能,使宿主更容易發生感染[30]。交感神經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SNS)和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過度激活后,通過調節適應性免疫來抑制大腦的免疫反應[31]。HAP識別急性卒中后釋放的促炎因子-α,白介素-1β和白介素-6后分泌過量的糖皮質激素,導致T細胞凋亡[32,33]。過度激活的SNS釋放過量的兒茶酚胺到血液中,導致免疫細胞的數量減少和功能減退,從而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感染風險[34,35]。直接激活的膽堿能抗炎途徑對卒中后肺部感染的發展至關重要。在炎癥浸潤的狀態下,乙酰膽堿通過抑制促炎物質的產生,防止免疫系統潛在的有害的過度反應。肺泡巨噬細胞和肺泡上皮細胞表達α7煙堿能乙酰膽堿受體,膽堿能途徑可抑制肺固有免疫力,促使中風后肺炎的發生[36]。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缺血性腦卒中直接改變了肺中免疫細胞的生態位:淋巴細胞數量和各種促炎趨化因子明顯減少;未觀察到單核細胞浸潤,但是單核細胞趨化因子C-C基序配體2的表達增加。總之,這些發現證明了缺血性卒中后肺部免疫力受到直接影響[37](見圖1)。

圖1 中風后全身免疫抑制的神經調節,過度激活SNS和HPA通過調節適應性免疫來抑制大腦的免疫反應
1.3 細菌來源的多種途徑
引發卒中后肺炎的病原體可能來自體內或外部。例如,定植在口腔和呼吸道中或在社區和醫院中持續存在的細菌[38-40]。急性卒中患者的口腔生態系統破壞使病原菌過度生長,可能引發全身感染[41,42]。有研究表明,急性卒中發展過程中吸入原本無害的細菌會引起嚴重的肺炎和菌血癥[43]。此外,腸道菌群的遷移也是急性卒中早期階段內源性細菌的起源之一。卒中后腸道微環境的平衡被打破,影響到腸道屏障的功能并增大其通透性。宿主腸道菌群中的細菌通過血流或淋巴液選擇性轉移到周圍組織中。這經常會在相關的組織部位(例如肺部)引發中風后感染[44,45]。有研究發現,大鼠腦中動脈缺血模型發作24h后,與短暫大鼠腦中動脈缺血模型誘導相比,回腸和結腸中細菌生物量顯著減少,并且粘膜微生物群的組成發生了顯著變化;與假手術組相比,缺血后大鼠的脾臟,肝臟,肺臟和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檢測到培養細菌。這些結果有力地揭示了腸道細菌是系統性傳播的[46]。卒中后小鼠肺中的某些病原體最有可能直接從小腸傳播或間接通過肝臟傳播的腸道菌群[47]。引起SAP的細菌包括好氧革蘭氏陰性桿菌(如肺炎克雷伯菌,大腸桿菌和銅綠假單胞菌)和革蘭氏陽性球菌(如金黃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鏈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腸埃希菌普遍存在于腸道菌群中[48]。在卒中患者中觀察到超過70%的細菌來自正常大腸桿菌,其中包含腸球菌,大腸桿菌和摩根氏菌;大鼠腦中動脈缺血模型24h后,預計60%以上的肺部微生物來源于小腸;與口服途徑將接種細菌傳播到周圍組織相比,中風引起的腸屏障障礙和通透性增大優先發生[47,49]。(見圖2)

圖2 中風后腸道菌群向肺部遷移的途徑,腦卒中打破腸道微環境的平衡并增加腸道通透性,宿主腸道菌群中的細菌選擇性轉移到周圍組織
總之,誘發SAP的病原體來源是多渠道的,包括原本存在于呼吸道的和從腸道遷移的細菌。更糟的是,中風后免疫抑制會增加細菌感染的可能性。因此,似乎闡明了SAP發生在較早時期——急性卒中后7天之內的原因。
2 卒中相關性肺炎的預防及治療
對于SAP的預防及治療,我們須先積極治療原發性疾病,并為急性卒中患者提供最佳的護理方式,高質量的臨床護理可以改善結局并降低醫院的死亡率[50]。關于SAP的臨床治療,Smith等專家們就使用抗生素達成了共識:他們建議在SAP患者中立即進行抗生素治療,然而抗生素給予的時機以及特定抗生素類別的選擇仍然不確定[9]。基于對卒中后肺炎機制的最新了解,一些研究者支持采用預防性抗生素[51],但目前尚無足夠的證據支持抗生素在防止SAP發展進程中的普遍使用[52,53]。因此,迄今為止,各國的臨床指南中均不建議使用抗生素預防SAP。
2.1 抗生素的應用
一些早期臨床試驗報告了預防性使用抗生素治療卒中后感染的效果:在卒中單元,左氧氟沙星預防性給藥的作用并不優于對急性卒中患者進行高質量的護理[54];米諾環素與莫西沙星的預防性給藥對AIS患者有更好的預后[55,56]。綜上所述,預防性治療卒中后感染的結論是有爭議的。基于這種矛盾現象,研究人員進行了前瞻性,多中心,隨機對照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三項研究揭示了預防性抗生素治療不能降低卒中后肺炎的發病率和死亡率,也不能改善3個月的功能結局,并且可能會增加住院時間和費用[57-59]。卒中后預防性抗生素治療似乎可以降低感染的風險,但主要原因是它可以預防尿路感染而不是肺炎[60,61]。卒中后肺部感染具有復雜的發病機理,并且由于細菌來源途徑的不同,抗生素只能殺死部分細菌,不能充分覆蓋所有的病原體。預防性抗生素的使用也不能從根本上提高宿主消滅細菌的免疫力,從而不能達到預防SAP的良好效果。
2.2 免疫調節劑
隨著對卒中后免疫抑制機理的了解,一些學者提出了免疫調節療法來預防卒中后肺部感染。激動劑JWH-133激活大麻素2受體可以抑制嗜中性粒細胞向大腦的募集,并且可能不會影響機體抵抗細菌感染的防御能力,對大腦和全身的免疫調節是有益的[62,63]。在有關SNS激活免疫方面,普萘洛爾通過阻斷去甲腎上腺素神經遞質調節不變的自然殺傷T細胞以預防卒中后肺部感染[64]。然而,一些臨床研究表明β受體阻滯劑的使用并不能減少卒中后肺部感染的發生,甚至可能會提高30天的死亡率[65,66]。通過分化簇147的抗體阻斷可改善異常的肺部免疫應答(包括肺部對白細胞浸潤和細菌感染的敏感性)來降低SAP的發生率[67]。目前對中風后免疫抑制促使SAP的發生達成了共識,但其病理過程的發展仍不清楚。由于機體自身復雜免疫調節的存在,有必要找到最佳的免疫調節方案,該方案應在不加重腦損傷的情況下將SAP的發生率降至最低。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免疫調節研究仍在動物實驗中,結論尚存爭議。因此,我們仍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來闡明免疫調節的機理,并設計可行的臨床試驗以驗證調節免疫的功效。
3 結論
目前的證據表明SAP與多種危險因素有關。卒中后吞咽困難增加了SAP發生的可能性;卒中后免疫抑制使得機體降低了對病原微生物的防御能力;細菌來源的多途徑使SAP的發病機理更加復雜。這些病因給SAP的防治帶來一定的困難。希望能對SAP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從而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為臨床醫生在診療SAP患者時提供有效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