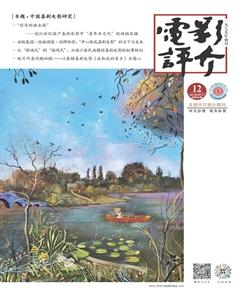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現(xiàn)代性思考: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的電影理論開(kāi)拓
在寫(xiě)實(shí)主義批評(píng)家陣營(yíng)中,德國(guó)批評(píng)家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是公認(rèn)的西方寫(xiě)實(shí)主義最具代表性的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在一系列著作中大膽立論、旁征博引,利用大量影片案例和理論建立起一個(gè)完整而嚴(yán)密的電影理論體系,提出了之前從未有過(guò)的紀(jì)實(shí)主義美學(xué)規(guī)范。這些看法條理清晰,自成體系,對(duì)貝拉·巴拉茲、艾因漢姆和雨果·明斯特伯格等電影理論家的觀點(diǎn)都提出了挑戰(zhàn),其博大精深的理論格局體現(xiàn)了西方20世紀(jì)現(xiàn)代性思維下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發(fā)展。
一、作為被攝物的世界與作為客觀世界素材的影像
在克拉考爾之前,關(guān)于“趨向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以記錄自然為最高目標(biāo)的傾向”與“造型的、以藝術(shù)創(chuàng)造為目標(biāo)的傾向”[1]即電影形式主義美學(xué)與紀(jì)實(shí)主義美學(xué)的爭(zhēng)論已持續(xù)了半個(gè)世紀(jì)。如果在這一沖突的視角下審視克拉考爾的理論,會(huì)發(fā)現(xiàn)克拉考爾在堅(jiān)持了紀(jì)實(shí)美學(xué)基本原則的基礎(chǔ)上大膽立論,從自身的電影化價(jià)值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出發(fā),對(duì)電影進(jìn)行了等級(jí)的劃分。克拉考爾對(duì)電影進(jìn)行劃分的方式與既往所有方式都不相同,他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是素材的美學(xué),重點(diǎn)在于電影的內(nèi)容而非形式。克拉考爾首先對(duì)電影這一媒介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理論描述,對(duì)電影的拍攝素材和基本方法做了內(nèi)容方面的闡述,其次依據(jù)建立的標(biāo)準(zhǔn),對(duì)各種電影形式進(jìn)行了通透的批評(píng),最后將電影放入現(xiàn)代性思考的理論背景中,論述了電影的目的與可能性。與此相關(guān)展開(kāi)的種種論述建立在三個(gè)預(yù)設(shè)上:首先,電影的主要功能是攝影,而非剪輯或其他形式技巧;其次,攝影的主要功能是忠實(shí)記錄事物而非對(duì)事物形態(tài)進(jìn)行轉(zhuǎn)換;第三,電影需要忠實(shí)記錄它所捕捉的事物。換言之,電影應(yīng)該在形式上或構(gòu)成上寫(xiě)實(shí)地對(duì)其意象進(jìn)行描繪。這三條預(yù)設(shè)是絕對(duì)意義上的,克拉考爾試圖沿著紀(jì)實(shí)主義的基本方向通過(guò)對(duì)各種類(lèi)型電影的考察,為電影找到最適合其媒介形式發(fā)展的路線,從而為三條預(yù)設(shè)找到了合理性。在對(duì)具體影片素材與內(nèi)容的考察中,克拉考爾提出了許多全新的論點(diǎn),如電影不一定首先非要是藝術(shù),效法傳統(tǒng)藝術(shù)會(huì)使電影失去它的特色;只要?jiǎng)訖C(jī)純正,創(chuàng)作者就可以將自己對(duì)物質(zhì)存在的感受用記錄片的方式反映出來(lái);電影不應(yīng)該在完滿的封閉狀態(tài)中表達(dá)人類(lèi)的意義,而應(yīng)該利用想象力超越素材本身,表現(xiàn)世界的意義等。
對(duì)于克拉考爾而言,電影這一媒介是題材/電影素材和處理方法/電影技巧的綜合產(chǎn)物。這種理解方式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他對(duì)紀(jì)實(shí)美學(xué)與形式美學(xué)長(zhǎng)期爭(zhēng)論的一種回應(yīng)。電影的目的只是“駐足于真實(shí)的物理世界”展現(xiàn)自己的素材,而并“不意在創(chuàng)造一個(gè)新的藝術(shù)世界”。[2]即使銀幕中充滿抽象效果或充滿想象力的奇觀,觀眾的認(rèn)識(shí)也不應(yīng)該超越對(duì)象,而應(yīng)該借助電影回到對(duì)象本身——這也是克拉考爾為何始終對(duì)“電影藝術(shù)論”有所保留的原因。在他看來(lái),電影和傳統(tǒng)藝術(shù)的差別在于其素材本身直接來(lái)源于現(xiàn)實(shí),電影應(yīng)該在現(xiàn)實(shí)與技術(shù)性能兩方面發(fā)展素材本身的美學(xué)。而電影工作者的任務(wù)是要正確地了解需要被表現(xiàn)的現(xiàn)實(shí),與適合表現(xiàn)現(xiàn)實(shí)的媒介(攝影術(shù)與電影),然后采用合適的技巧表現(xiàn)合適的題材。從現(xiàn)實(shí)方面來(lái)說(shuō),電影繼承了攝影發(fā)展的形式,以及攝影術(shù)和現(xiàn)實(shí)之間的天然聯(lián)系。其結(jié)果一方面在于,電影繼承了攝影術(shù)的服務(wù)對(duì)象——充滿“偶然事件”和“無(wú)限細(xì)微反應(yīng)”的“無(wú)盡的、自發(fā)的世界”[3],保存了復(fù)制的特點(diǎn)作為自身的主要特性;另一方面,電影也擴(kuò)充了攝影術(shù)能表現(xiàn)的對(duì)象與題材,以剪輯變焦特寫(xiě),光學(xué)效果等次要技術(shù)部分的形式對(duì)攝影術(shù)的靜態(tài)畫(huà)面進(jìn)行了補(bǔ)充。總而言之,克拉考爾認(rèn)為整個(gè)世界都是有待被攝影的,而電影的媒介形式適合拍攝一切現(xiàn)實(shí)世界中的事物。在電影以其基本技術(shù)手段記錄和揭示客觀世界的過(guò)程中,電影作者可以通過(guò)對(duì)現(xiàn)實(shí)和運(yùn)動(dòng)的記錄呈現(xiàn)世界原有的面貌,也可以通過(guò)一些附加技巧來(lái)改變世界被呈現(xiàn)的面貌,從而令我們對(duì)世界產(chǎn)生更為深刻的認(rèn)識(shí)。在對(duì)素材的處理中,克拉考爾雖然贊成部分形式主義技巧,認(rèn)為這些技巧可以使我們對(duì)世界產(chǎn)生更為深刻的認(rèn)識(shí),但對(duì)電影技巧吸引觀眾參與電影而不是現(xiàn)實(shí)世界、令觀眾沉溺于電影本身的做法持批判態(tài)度。克拉考爾借鑒德國(guó)學(xué)者埃里希·奧爾巴赫在《模仿論:西方文學(xué)》中的觀點(diǎn),認(rèn)為電影應(yīng)該如同嚴(yán)肅的寫(xiě)實(shí)主義文學(xué)一樣,以一種溝通性媒介的形式根植于現(xiàn)實(shí)中澄清和放大生活經(jīng)驗(yàn)中的模式,從人類(lèi)講話動(dòng)作的簡(jiǎn)單日常開(kāi)始獲得藝術(shù)感染力與共鳴,而非通過(guò)藝術(shù)家的主觀創(chuàng)造與加工展現(xiàn)所謂的“藝術(shù)感染力”或新的經(jīng)驗(yàn)。只有這樣,電影才能避免意識(shí)形態(tài)并摹寫(xiě)人類(lèi)生活經(jīng)驗(yàn)的復(fù)雜性和多樣性,引導(dǎo)我們走向永久的和諧之路——這也是20世紀(jì)現(xiàn)代自然科學(xué)發(fā)展的背景下克拉考爾作為電影理論家與思想家的自然觀點(diǎn)。19世紀(jì)的唯物主義信條在相對(duì)論與量子物理學(xué)被發(fā)現(xiàn)之后早已崩潰,許多技術(shù)方法將看起來(lái)非現(xiàn)實(shí)、無(wú)法用常理判斷,但真實(shí)存在的世界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真實(shí)”已經(jīng)不再與“實(shí)在”“存在”“可見(jiàn)”等概念產(chǎn)生直接的聯(lián)系。這樣對(duì)“真實(shí)”的懷疑觀點(diǎn)下,模糊卻實(shí)際存在著的理論傾向取代了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絕對(duì)認(rèn)同。在電影素材與技術(shù)無(wú)法再對(duì)現(xiàn)實(shí)做出精準(zhǔn)的確定之后,尋求自然與人類(lèi)在攝影中的統(tǒng)一,成為達(dá)到新的和諧的方式。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電影扮演了人與自然溝通媒介的角色,克拉考爾認(rèn)為自然中有適合電影和攝影表現(xiàn)的“外部的連續(xù)”層面,并列舉了五條相關(guān)的道路:極其廣闊的現(xiàn)實(shí)面、某些事件的因果聯(lián)系、對(duì)一個(gè)物象“摩弄”良久直到它在我們心目中造成無(wú)邊無(wú)際的印象、生活中某一重要時(shí)刻內(nèi)的再現(xiàn)、再現(xiàn)大量的物質(zhì)現(xiàn)象構(gòu)成的可理解節(jié)奏形式……[4]人類(lèi)無(wú)法通過(guò)其他形式來(lái)接觸這些層面上的自然,而自然也以電影的形式來(lái)表現(xiàn)自己。這種影片里的鏡頭或鏡頭組合具有多種的含義,電影化的影片所喚起的現(xiàn)實(shí),要比它實(shí)際上所描繪的現(xiàn)實(shí)內(nèi)容更為豐富。
二、電影形式結(jié)構(gòu)中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原則
克拉考爾在對(duì)電影基本性質(zhì)思考的基礎(chǔ)上將電影素材加以形式化,并在電影的形式結(jié)構(gòu)中對(duì)不同電影類(lèi)型進(jìn)行了歷史性的考察。最終,克拉考爾在對(duì)德國(guó)表現(xiàn)主義、電影好萊塢類(lèi)型片與美國(guó)藝術(shù)片的分析與比較中,再次證明了自己寫(xiě)實(shí)性的美學(xué)原則。克拉考爾將電影結(jié)構(gòu)自由選擇影像呈現(xiàn)順序的時(shí)間稱(chēng)為“構(gòu)成”,依據(jù)電影的主題將電影分為“敘事”與“非敘事”兩種類(lèi)型,其中以敘事電影為主要類(lèi)型,并進(jìn)一步將非敘事電影分為“真實(shí)電影”和“實(shí)驗(yàn)電影”。在對(duì)敘事電影的論述中,克拉考爾企圖為這種被普遍認(rèn)為是娛樂(lè)觀眾的、商業(yè)的、不是純粹的電影正名。克拉考爾不僅認(rèn)為劇情片使電影有了全面發(fā)展的機(jī)會(huì),避免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追求走向形式主義的極端立場(chǎng),還主張劇情片應(yīng)該成為電影的主流,因?yàn)楣适卤旧頌殡娪坝跋竦默F(xiàn)實(shí)帶來(lái)的深度。“基于事實(shí)的電影,只能表現(xiàn)世界的某一部分,新聞片和紀(jì)錄片表現(xiàn)的都是人的外在環(huán)境,而不是個(gè)人的內(nèi)在沖突,所以故事的懸疑性既有助于紀(jì)錄片又使其相形見(jiàn)絀。”[5]故事不僅是電影的經(jīng)濟(jì)與市場(chǎng)基礎(chǔ),也是美學(xué)原則的基礎(chǔ),只有故事與情節(jié)能使抽象的主題具體,使觀眾在觀影過(guò)程中投入到劇情中,從而形成富有深度的體驗(yàn)。即使是紀(jì)錄片,其中的優(yōu)秀者也會(huì)努力使觀眾完全投入到劇情中。
基于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原則,克拉考爾并不全然肯定故事在電影中的作用,而是再次提出了故事的分類(lèi)與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試圖在紀(jì)實(shí)原則和形式原則,或者說(shuō)在記錄的寫(xiě)實(shí)和揭露的形式之間取得平衡。在克拉考爾看來(lái),最好的劇情片源于偶然中被發(fā)現(xiàn)的故事或運(yùn)動(dòng)的組合,其次是改編自文學(xué)的作品,再次是舞臺(tái)化敘事。舞臺(tái)化的敘事是默片時(shí)代藝術(shù)電影的殘留,其中以人工背景、風(fēng)格化表演、沖突矛盾密集的劇本等元素襯托的舞臺(tái)化形式違背了紀(jì)實(shí)的電影原則,例如大量好萊塢影片就屬于這一類(lèi)型。這些好萊塢影片以一種傳統(tǒng)的舞臺(tái)藝術(shù)形式帶給大眾快樂(lè),但從電影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掩蓋了生活的真實(shí)與真實(shí)的生活。改編于自然主義小說(shuō)或其他適合改編的寫(xiě)實(shí)文學(xué)作品的電影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真實(shí)原則,但同樣注定失敗,因?yàn)閯?chuàng)作者只能在主人公所處的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其具有限制性的簡(jiǎn)單情感與思想,對(duì)內(nèi)心復(fù)雜的糾結(jié)矛盾無(wú)能為力。最后,由多種多樣的運(yùn)動(dòng)組成故事則是真正“電影的”,只有電影攝影機(jī)才能記錄的現(xiàn)象與故事才被認(rèn)為是最上乘的電影題材。偶然發(fā)現(xiàn)的故事和攝影機(jī)對(duì)真實(shí)的展現(xiàn)之間存在千絲萬(wàn)縷的關(guān)系,這些偶然性的故事建立在混亂的不可預(yù)測(cè)的生活之流上,使各種外在活動(dòng)自然地變?yōu)閮?nèi)在活動(dòng),是開(kāi)放與帶著強(qiáng)烈情感沖擊力的。克拉考爾以帶有敘事性的紀(jì)錄片《北方的納努克》(羅伯特·弗拉哈迪,1922)與《亞蘭島人》(羅伯特·弗拉哈迪,1934),以及意大利新現(xiàn)實(shí)主義影片《大地在波動(dòng)》(盧奇諾·維斯康蒂,1948)、《游擊隊(duì)》(羅伯托·羅西里尼,1946)、《偷自行車(chē)的人》(維托里奧·德西卡,1948)等影片為例說(shuō)明這一觀點(diǎn)。他認(rèn)為這些電影中的故事來(lái)自影片中表現(xiàn)出的地域與文化,普遍而客觀地通過(guò)典型場(chǎng)景中的典型人物表現(xiàn)戰(zhàn)后意大利普遍存在的社會(huì)問(wèn)題,所有的情節(jié)都可能直接存在于現(xiàn)實(shí)本身之中,而不是帶有想象意味的個(gè)人創(chuàng)作。
克拉考爾同時(shí)批判了非敘事的電影,尤其是其中的部分實(shí)驗(yàn)電影,他針對(duì)這些影片根據(jù)自己的節(jié)奏感組織素材,創(chuàng)造形式而不記錄模仿形式的問(wèn)題提出了批判。在紀(jì)實(shí)主義美學(xué)的基本原則中,現(xiàn)實(shí)是電影力量的來(lái)源;而以遠(yuǎn)離現(xiàn)實(shí)觀念制作的實(shí)驗(yàn)電影扼殺了創(chuàng)作者對(duì)于現(xiàn)實(shí)的好奇,只是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的又一種延伸。相比之下,克拉考爾更加推崇包括布努埃爾在內(nèi)的許多先鋒藝術(shù)家傾向于寫(xiě)實(shí)理念與表現(xiàn)形式的做法,對(duì)許多展示藝術(shù)家創(chuàng)作過(guò)程的影片也較為推崇。例如紀(jì)錄了畢加索創(chuàng)作20余幅繪畫(huà)作品詳細(xì)過(guò)程的《畢加索的秘密》(克魯佐,1956)。克拉考爾認(rèn)為影片中的畫(huà)作在被錄入影片時(shí)依然作為獨(dú)立存在的物質(zhì)實(shí)體,而非創(chuàng)作者的心理或精神存在,這點(diǎn)難能可貴:作為電影忠實(shí)于被記錄的藝術(shù)作品本身同時(shí)創(chuàng)造出了與之相關(guān)的新作品。
三、現(xiàn)代性思考與影像的結(jié)合
克拉考爾在遭遇納粹迫害流亡國(guó)外之后,開(kāi)始將對(duì)現(xiàn)代性的思考與對(duì)藝術(shù)史的研究結(jié)合起來(lái),在1941年定居美國(guó)后逐漸寫(xiě)作完成了《電影的本性: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復(fù)原》《從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等著作。在對(duì)素材與內(nèi)容的美學(xué)及形式結(jié)構(gòu)進(jìn)行闡述之后,克拉考爾在一篇長(zhǎng)達(dá)十幾頁(yè)的分析大綱中闡明了自己理論的正當(dāng)性與現(xiàn)代人生活的批判態(tài)度。在“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還原”這一基本命題之后滲透的是克拉考爾對(duì)于人與自然關(guān)系、西方文明走向、資本主義制度內(nèi)在矛盾等問(wèn)題的深刻思考。在克拉考爾看來(lái),信仰與宗教在19世紀(jì)的失效造成了意識(shí)形態(tài)的瓦解與消失,科學(xué)無(wú)法在失去支撐的文明中給予人們新的信仰,現(xiàn)代人過(guò)著普遍空虛且凡俗的生活。盡管科學(xué)宣稱(chēng)自身誕生于自然的真理,但20世紀(jì)以來(lái)人類(lèi)生活的破碎與非自然狀態(tài)卻證明了理性希望的破滅。在意識(shí)形態(tài)的空洞中,人們犧牲了對(duì)自然的直覺(jué)認(rèn)識(shí),轉(zhuǎn)而不斷追求抽象化方向發(fā)展的科學(xué),其結(jié)果是為了找到控制萬(wàn)物的法則而背棄了自然本身。這種情境中,藝術(shù)應(yīng)當(dāng)完成的目標(biāo)就是讓人類(lèi)重新找回對(duì)自然的直覺(jué)認(rèn)識(shí),將世界從抽象的公式中解放出來(lái),以感性與審美的邏輯去體驗(yàn)宇宙的存在,并重新組合支離破碎的思想世界。基于這一蘊(yùn)含著對(duì)西方世界現(xiàn)代性批判的審視目光,克拉考爾失望地提出西方傳統(tǒng)藝術(shù)的目的是用特殊方法轉(zhuǎn)換世界的存在形態(tài)。在這樣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中,原本真實(shí)而富有力量的素材被削減了。此時(shí)“應(yīng)運(yùn)而生”的電影這一新媒介則與之前的傳統(tǒng)藝術(shù)不同,可以如實(shí)地展示它的素材,并通過(guò)素材的紀(jì)實(shí)展示生活的本身——這也是克拉考爾不認(rèn)同“電影藝術(shù)論”的根本原因所在。在他的理想中,電影觀眾可以通過(guò)電影等媒介與世間萬(wàn)物直接對(duì)話,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種與物質(zhì)緊密聯(lián)系的、新的信仰,繼而擺脫自我中心的危險(xiǎn),建立一種普遍而超然的、與自然萬(wàn)物密不可分的新文化與新文明;也正是對(duì)電影通過(guò)直接呈現(xiàn)真實(shí)的預(yù)期,克拉考爾建立了他的紀(jì)實(shí)美學(xué)理論。在他看來(lái),《黨同伐異》(大衛(wèi)·格里菲斯,1916)和《十月》(愛(ài)森斯坦,1928)兩位導(dǎo)演都過(guò)高估計(jì)了畫(huà)面的象征力量,把自己認(rèn)為合適的東西都硬加在畫(huà)面本身的固有含義之上,而這些象征性的鏡頭和場(chǎng)面是經(jīng)不起時(shí)間考驗(yàn)的。[6]對(duì)于直接攫取現(xiàn)實(shí)進(jìn)行表現(xiàn)的電影而言,越是避免直接呈現(xiàn)內(nèi)心生活、意識(shí)形態(tài)和心靈問(wèn)題的影像越富于電影性,也越接近真實(shí)的世界與人的內(nèi)心。
盡管克拉考爾一再?gòu)?qiáng)調(diào)紀(jì)實(shí)美學(xué)的原則與電影適合或不適合表現(xiàn)的對(duì)象,但無(wú)數(shù)創(chuàng)作者對(duì)表現(xiàn)抽象世界的巨大興趣的確是不可否認(rèn)的。如同愛(ài)森斯坦曾經(jīng)幻想將《資本論》翻拍為電影一樣,至今無(wú)數(shù)導(dǎo)演仍在探索視聽(tīng)語(yǔ)言的表現(xiàn)范圍上進(jìn)行摸索。試圖觸摸現(xiàn)實(shí),深入現(xiàn)實(shí),就必將導(dǎo)致將人與自然重新調(diào)和,以視聽(tīng)語(yǔ)言表現(xiàn)抽象世界的想法。對(duì)此,克拉考爾提出了相對(duì)折中的解決方案,即通過(guò)電影或其他適合的媒介在保持這一抽象思維興趣的同時(shí),提升我們對(duì)生活的體驗(yàn)。如果說(shuō)傳統(tǒng)藝術(shù)往往是一種吸引人的模型,它自上而下地將形而上的思考表述出來(lái),顯現(xiàn)為融洽自足的作品;那么電影就是到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記錄、拍攝和發(fā)現(xiàn)具有偶然性的真實(shí)世界,并將其自下而上地“升華”為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完整呈現(xiàn)。為了使傳統(tǒng)藝術(shù)作品在內(nèi)部達(dá)到自洽,傳統(tǒng)藝術(shù)家需要壓抑真實(shí)的本性使現(xiàn)實(shí)符合他對(duì)世界表現(xiàn)的需要。當(dāng)觀眾深信自己通過(guò)傳統(tǒng)藝術(shù)作品體驗(yàn)到“自然”時(shí),不過(guò)是以一種新的方式再次體驗(yàn)到了日常生活中被型塑好的刻板意識(shí),永遠(yuǎn)無(wú)法感受到自然真正發(fā)出的氣息。此時(shí),電影作為一種“非藝術(shù)”或者新的藝術(shù),能在“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復(fù)原”中從自然入手,將我們從狹隘的隔絕中拯救出來(lái)。
結(jié)語(yǔ)
克拉考爾從紀(jì)實(shí)性原則出發(fā),闡明電影的本性在于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復(fù)原而非講述虛構(gòu)的故事。他提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實(shí)際存在的物質(zhì)作為電影的素材,調(diào)動(dòng)電影的多種表現(xiàn)手段,能使觀眾的思想與自然相融合,擁抱無(wú)邊無(wú)際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從而使我們暫時(shí)從被虛假理性占領(lǐng)的、荒蕪空缺的意識(shí)空缺中解脫出來(lái)。
參考文獻(xiàn):
[1][2][3][4][5][6][德]齊格弗里德·克拉考爾.電影的本性:物質(zhì)現(xiàn)實(shí)的復(fù)原[M].邵牧君,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15,31,57,31,197,279.
【作者簡(jiǎn)介】 李晉媛,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師范大學(xué)戲劇與影視學(xué)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影視傳播、影視教育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 本文系山西省省籌資金資助回國(guó)留學(xué)人員科研項(xiàng)目“中、美、韓高校電影專(zhuān)業(yè)教育供給側(cè)人才培養(yǎng)模式比較研究”(編號(hào):2020-148)階段性研究成果。